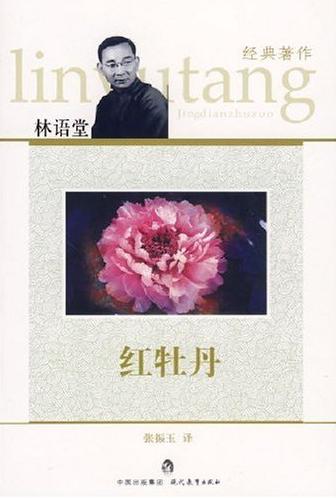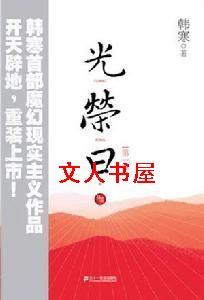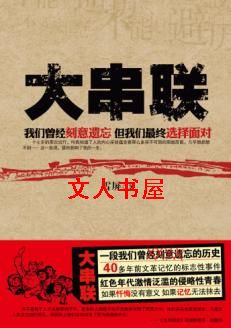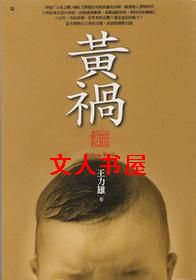作者:张爱玲祖父不肯出来做官,就肯也未见得有的做。大小十来口子人,全靠祖母拿出钱来维持着,祖母万分不情愿,然而已是维持了这些年了。……潆珠家里的穷,是有背景,有根底的,提起来话长,就像是“奴有一段情呀,唱拨拉诸公听”。可是潆珠走在路上,她身上只是一点解释也没有的寒酸。只是寒酸。她两手插在塌肩膀小袖子的黑大衣的口袋里,低头看着蓝布罩袍底下,太深的肉色线裤,尖口布鞋,左脚右脚,一探一探。从自己身上看到街上,冷得很。三轮车夫披着方格子绒毯,缩着颈子唏溜溜唏溜溜在行人道上乱转,像是忍着一泡尿。红棕色的洋梧桐,有两棵还有叶子,清晰异常的焦红小点,一点一点,整个的树显得玲珑轻巧起来。冬天的马路,干净之极的样子,淡黄灰的地,淡得发白,头上的天却是白中发黑,黑沉沉的,虽然不过下午两三点钟时分。...
作者:林语堂译者序本书纯属杜撰,人物情节全系虚拟。其中人物如与古今人物相似,纯系偶合。花儿半开半闭小停轻颤犹疑唇间微笑如梦里芳心谁属难知译者序黄肇珩女士在《林语堂先生的写作生活》一文中,曾有下面一段文字:(见《无所不谈集》,页七八一)但是,我翻译时,却将那若干段都忠实译出,丝毫未曾删减。一则表示尊重原作,二则尊重原著作者林先生,三则仰体孔夫子删诗不删《关雎》之意,四则……欲语还休吧。倘若中国的清教徒那些卫“道”之士想欣赏林先生的创作艺术,只须将门儿关上把此数段艳文偷偷儿看几遍,也就与道心无大碍了。张振玉记民国六十六年十一月于台北燕庐寓所上卷第一章费庭炎,生前任高邮盐务司的主任秘书。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三,那天他的丧礼举行开吊,生前的友好前来吊祭;每个人都在乌黑的灵柩前深深的三鞠躬,然后脚尖点着地,轻轻走开——男人到一边去,女人到另一边去。这个丧事先潦草办,也是家里...
作者:韩寒【由文】第一章三年以前,再以前。当时改革的春风吹满地,腐败分子撒一地。大麦在的是一个小地方,两省的交界,在管理上经常出问题。通常两个省的事,都不省事。小地方叫孔雀。本来那里叫凤凰,但是隔三差五的,经常有背着巨大旅行包,操着鸟语的老外到镇政府值班办公室要求看一看沈从文的老家。那时候那拨人还在上学,一次看见一个插着一面美国国旗的老外,大包上写了一个英文,是WALK,还有一句中文。到了中国,入乡随俗,老外觉得一定要有中文的翻译才显得亲切。但很明显,这个老外的第一站是北京,而且找的街头翻译也不是善类,因为包上的中文标着:去你的。老外去过很多地方,因为他的衣服上写了不少字,有“天津欢迎你”,“你到河北了”和“打倒美帝国主义”,“你的毛真黄”。...
作者:陆天明一事后,丁洁记得非常清楚,12月18何下午,她亲自驾驶那辆大奥迪车,送父亲去来凤山庄参加那个高级别的聚会,应该说,当时一切正常,无论怎么回想,也找不到任何迹象表明那天会出事。丁洁的父亲刚从大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退下来,决定定居省城。是日晚,热情而又懂事的省市主要领导为尽地主之谊,特地20在著名而又非常幽静的来凤山庄组织了一个小型聚会,为这位劳苦功高的大军区离休司令员接风。虽说是小型聚会,但省市几大班子的主要领导都要出席,安全保卫工作自然是做得严密到位,滴水不漏。头一天的白天,奉命筹办这次聚会的市政府秘书长周密就带着他那一班秘书处的得力干将进驻了山庄,并会同市公安局政保处的人对山庄的方方面面都做了无可挑剔的部署。到晚间,一支精干的警卫小分队便严密封锁了进出山庄的各路径道口,并把警戒哨放到了五六百米以外。18日下午,只有两件事让她稍感意外。一件事是气象台预报没有大...
作者:钟墨第一章 谁比谁多情见到林雨馨,孟皓知道了自己究竟想要的是什么样的女人。大连市赫赫有名的鲲鹏公司总经理孟皓用食指玩弄着水晶杯的口沿,目送着林雨馨和男友郝良登上S形的楼梯,上二楼孟伟的房间。林雨馨长长的裙摆随着脚步的上移而露出精致的脚踝,孟皓有一种想握住它们的冲动。直到看不见她的影子,孟皓才缓过神来,他轻舒了一口气,看看身边的母亲叶海琳。海琳在那里有些发愣,眼神也望着楼梯的方向。孟皓用右手掌在母亲面前挥了挥,“妈,你还在生我的气吗?我说不去你不干,我就知道又得惹你生气,好了,妈,好事不怕晚。”海琳一扬手打落了儿子的手,对着楼上努了努嘴:“那个女孩,就你弟同学的女友,怎么样,够漂亮的吧?照这样的找,你还会有意见吗?”孟皓微微一笑,不答。海琳真的急了,竟从沙发上站起身来,说:“这样的也不行?你说,到底想找什么样的?今天可是第二十九次相亲,你挑不出人家长相上的毛...
作者:关小常【由文】这是一部亦编亦著的作品,但我特别喜欢;这也是一部中国现代文学与生命快乐哲学的作品,希望读者喜欢。人生的意义就是人存在的理由,人生的意义就是快乐。不管你是工人、农民、医生、学者、法官、政治家、哲学家、道德家、自由者、正义者、善、恶、美、丑、真、假……所有的人,所有具有生命感知能力的人,如果生命是痛苦的,那么人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无意义的生命中,人成为“一沟绝望的死水”,没有快乐的生命,人就没有了“情热”和“智光”。这个世界上,每年有多少人自杀?文学界有诗人之死,娱乐圈有明星之死,企业界有富翁之死,校园里有学生之死。不管这些人为何而死,有一相同的,生命的存在失去了意义,生命成了痛苦的理由,那么存在就多此一举了,只好自然以摆脱生命的痛苦和虚无。与其生命痛苦,不如一死百了。...
作者:雪屏【】引子我以为是的还他一个是,我以为非的还他一个非,我以为应该这样办的,或以为应该那样办的,便自己打定一个主意或态度。——邹韬奋1倘若不是为她,我绝对不会登上这辆列车。我知道上了车就下不来了,我也知道不上车,恐怕这辈子我再也见不到她了。月台上的人太多了,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感觉,反正我感觉似乎毛主席昨天接见过的五十万名红卫兵都聚集在这里了。等我挤上这一趟去西北的车,我的裤腰带都断了,只好拿背包带临时扎上。我的伙伴们在十二号车厢,见了他们,我才后悔,我只背了个军挎包,装了毛巾、裤衩和袜子,外加上五块钱、六斤全国粮票,而他们人人都扛着个铺盖卷。看我来,他们都盯着我的蓝裤子,偷偷笑。他们都很纳闷,见我单枪匹马,脸上都露出疑问的表情:家辉呢?家辉是我们这次大串联的组织者,偏偏就他迟迟不见踪迹。我告诉他们,家辉不能来了,他家昨天夜里被抄了,他爸他妈也被押走了,他得照...
作者:王力雄【】一March 20, 1998地球人在努力营造一个大千世界。它很小,一半向着光闪闪的太阳,一半向着遥远的恒星。它像一个橙子,橙皮上起伏着山川河流,在没边没沿黑呼呼的宇宙中没着没落地旋转。在这颗橙子亮面与暗面相交的边缘上,太平洋中一头灰鲸玻璃般的眼球射进清晨第一束阳光。它仰浮的躯体被石油和有毒物质所腐烂,最后一丝知觉正沿着阳光去追溯往昔的海洋。琥珀色赤潮汹涌地覆盖着无际的洋面。与鲸鱼相对,橙子的另一侧明暗相交处,落日余光正把尼罗河干涸河床上蠕动的饥民照得如同鬼影。大风卷起干燥热土。爬行的沙漠早已掩埋古老光荣。人的脸上只剩盐碱﹑沙粒和一层层剥落的皮肤。美洲在太阳照亮的一面,倾斜地躺在大洋上。美国被高温和衰退折磨,百业萧条,艾滋病医院却肥皂泡般咕噜噜地越涌越多。...
作者:许开祯【由文,】第一章 娘子军1那道沉重的铁门“哐当”一声,滟秋算是被“救赎”出看守所。看守所罗所长并没送她到铁门外,只是把她叫到办公室,对她做了短暂的“教育”。罗所长说:“想不到啊,棉球这浑球,还有点能耐,要不然啊,要不然啊……”罗所长呵呵干笑着,不往下说。其实罗所长是一时找不到准确的表达语言,积攒在他脑子里的词汇量真是太少了。滟秋面无表情地盯着姓罗的。罗所长这天穿着警服,他是很少穿警服的,这个夏天,滟秋看到最多的,是他穿两件颜色和风格迥然不同的“老人头”T恤,裤子么,有时穿宽松的牛仔休闲裤,有时穿那条米色的飘逸西裤。穿米色飘逸西裤的时候,多半会跟看守所那个留短发的姓米的女警员在一起。那个姓米的女警20来岁,长得像根嫩葱,外加棱棱的鼻子,一对漂亮的小眼睛,笑起来分外甜,可她对滟秋一点不甜,训滟秋就跟训土匪流氓一样刻薄无情,滟秋恨这个女人。...
作者:孙惠芬岸边的蜻蜓吕作平蓬乱着头发的脑袋在椅子上越低越深。看到吕作平那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泪水在我的眼眶里漫起大雾。岸边的蜻蜓一吕作平来了,就在我的楼下,可是我还以为他是从庄河打来的电话。他说,我出事了。我说,什么?他说,你下来,我就在你楼下。吕作平站在我的对面,头发蓬乱,脸色乌青,仿佛刚刚遭到一顿拳击。在邻街酒吧坐下的时候,他撸着头,跟我说,梅花背叛了我。我端坐着,静静地看着他。我说,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吕作平闷闷地看着我,痛苦在他脸上抽动,仿佛我是梅花的帮凶。他说,你猜那个人是谁?我哼了一声,我听见我鼻孔里的声音裹着笑意。我说,是谁都很正常。这时,只见吕作平脖子和下颏逐渐胀起来,一瞬间,就涨红了眼睛。他瞪着我,好像要把别人打他的拳头挥向我。他努力压低声音,说,春天你太恶毒,那个人是老姨夫,老姨夫你听见了吗!...
作者:都梁【】《百年往事》内容简介笔墨纸砚 指间百年沧桑流变鼓笳笙萧 腮边往事风雨废兴回看百年中国抚摸“宅门”旧事首部以荣宝斋为题材的长篇巨制都梁第四部力作。《百年往事》弘扬中国文化,展现中国百年近代史演变历程。通过琉璃厂百年文品老店松鹤斋(荣宝斋)的成长发展,逐渐形成全国官吏、学者心目之中的文化朝圣地。读者和观众可以通过《百年往事》这个窗口向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进行回溯。咸丰年间,由张仰山经营的松竹斋,因其承办官卷、官折而成为当时京城琉璃厂里最有名气的一家南纸店。松竹斋由于名声好商品质素佳,又安逸的做着官家生意,多年来平稳发展,张家一家与店里伙计也和睦共处相安无事。1860 年,英法联军向布防在张家湾的清军开战。直隶绿营总兵郑元培出征抗敌,血战之后身负重伤。张仰山和店里伙计林满江意外发现了奄奄一息的郑元培,在生死关头,张仰山化开一块比金子还贵的古墨为郑元培止血疗伤,保...
作者:陈昌平一在王喜贵王师傅眼里,小儿子王爱娇就是一个废物。王师傅祖籍山东,世代务农。至少可以追溯到爷爷的爷爷,老王家便人丁兴旺,而且全部是兄妹六个——五个男的一个女的,老幺是个女的——小棉袄。至少从那时候开始,王家的男人和媳妇就像一台性能优异的机器,五男一女的生育传统和性别格局便一直延续下来。即便是在兵荒马乱颠沛流离的年代,王家的祖先依然顽强而又幸运地保持着这一匪夷所思的传统。到了王师傅这一代,自然还是兄妹六个,五男一女,老幺依然是个女的——小棉袄。这当然是一个奇迹,而且王师傅没有理由和借口破坏这一传统。王师傅排行老大,是兄弟里第一个成家立业的,而且赶上了突飞猛进蒸蒸日上的新社会,所以王师傅结婚时就铆足了劲儿,把机器调理得齿轮飞转马达轰鸣——他要给兄弟们做个榜样。...
作者:温金海第一章 神秘的死亡1手机响的时候,陶永和姚小琪正依偎在床上,准备做爱。最近陶永为了落实几个广告项目,在外接连跑了十多天,下午刚回到枫城。他惦念着姚小琪,早就盼着跟她约会,回来的路上他就给她打电话,告诉她预计几点几分到,要她到他家等他。陶永在枫城日报工作已近十年,算得上是年轻的老编辑,尽管还是单身,但不久前搭上福利分房末班车,分了套两居,九十多平方米。姚小琪刚工作三年,按规定没有分房资格,一直住在报社的单身宿舍,与另一名年轻女记者挤在一间小屋,诸多不便,陶永家便成了他们约会的主要场所。回到家,姚小琪果真在屋子里等他。这让陶永分外高兴,同时也让他感到欣慰、满足。俩人一见面就拥抱在一起,没过多久便躺到床上。但想做的事没还没做成,姚小琪的手机响了,嘀嘀两声,很短促。这是信息提示音。姚小琪想去看手机,陶永一把拦住了她。过了一分钟,嘀嘀声又响了两下。不太响亮,却搅...
作者:张爱玲好;那些不用多加解释的人物,他们的悲欢离合。现代的电影院本是最廉价的王宫,全部是玻璃,丝绒,仿云石的伟大结构。这一家,一进门地下是淡乳黄的;这地方整个的像一支黄色玻璃杯放大了千万倍,特别有那样一种光闪闪的幻丽洁净。电影已经开映多时,穿堂里空荡荡的,冷落了下来,便成了宫怨的场面,遥遥听见别殿的箫鼓。迎面高高竖起了下期预告的五彩广告牌,下面簇拥掩映着一些棕榈盆栽,立体式的圆座子,张灯结彩,堆得像个菊花山。上面涌现出一个剪出的巨大的女像,女人含着眼泪。另有一个较小的悲剧人物,渺小得多的,在那广告底下徘徊着,是虞家茵,穿着黑大衣,乱纷纷的青丝发两边分披下来,脸色如同红灯映雪。她那种美看着仿佛就是年轻的缘故,然而实在是因为她那圆柔的脸上,眉目五官不知怎么的合在一起,正如一切年轻人的愿望,而一个心愿永远是年轻的,一个心愿也总有一点可怜。她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小而秀...
作者:刘德濒【由文,】上 部第一章 小活佛的三个预言扎西被庄园里的景象惊呆了。满眼望去,院子里的人横七竖八倒毙在地,都已经断了气。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他们的尸体有的叠压在一起,挤在井台边上;有的抱成一团,蜷缩在碉楼的石墙下;还有的暴晒于院子中央,在灼热的阳光下,开始腐烂。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腥臭味儿,一阵阵地往扎西的鼻孔里钻。“又被那个小活佛说中了!太不可思议了!”扎西头皮一阵发紧,那个还不到十岁、说话奶声奶气的孩子,他的第二个预言也应验了。扎西顿珠是多吉林寺的喇嘛。这座寺院离拉萨有半天的脚程,深藏于彭波格拉群峰之间的一个山坳里。从七岁起,有二十多年的时间扎西都是在这里度过的。他是曲水宗一个差巴的儿子,藏历火羊年,他阿爸把收获的青稞都交了领主的高利贷,还没过冬,全家人就断了口粮。扎西差点儿饿死,幸好遇见了多吉林活佛。那天,活佛在羊措雍湖畔做法事,他带领一群喇嘛神...
作者:贾立峰【,】第一章 宝石蓝 雪花白 麦子黄 01 好炕夏末秋初,史无前例这个词几乎被孔家屋子的人用烂了。村里人原本不知道这个词,这个词是在一个清亮亮的日子里,一不小心从小学教员高原的嘴里冒出来的。高原每天读书看报,看到这个词,认为是一个难得的好词,就特意记住了。看来知道的事情多了没坏处,说不定哪一天就能用到。令高原始料不及的是,第一次使用,居然会让全村人都记住,并且风靡一时;他更没有料到,在未来的一个年代,这个词会成为了一个炙热鲜红的烙印,灼痛了许多人的心,也包括他自己的。如果不是因为那条铁路,平原本是一览无余的。许多年前,德国鬼子修了一条铁路,路基五六米高,像一条僵死的蛇横在村子东边,使那个方向的视野突然局促起来。一条灰白的大道先爬长长的大坡,横跨铁路,又下长长的大坡,然后一溜歪斜进村子,自东而西穿村而过。...
作者:阎真引子多少年来,我总忍不住想象自己将在某一个遥远的晴朗早晨告别这个世界,这种想象那一年在多伦多一个冬日的黎明出其不意地袭击了我以后,就再也无法摆脱。这想象这些年来折磨得我好苦。在那个晴朗早晨我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模糊多日的意识突然清醒,清醒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回光返照是这个生命的最后挣扎。周围站有人,神色凝重地注视着我注视着这个无法逆转的事变。我似乎听见有人说“醒过来了”就再也听不见什么。隔着人的肩膀我从眼缝中看见倒吊着的输液瓶在微微晃动,瓶中的药液在阳光中幻现出一个亮晶晶的斑点。我仿佛记起护士穿着白衣带着白帽给我打过吊针。冬日的阳光照到我的脸上,我感到了温和的灼热。我知道这是生命的最后感受。我想对周围的人说,太阳在明天、明年、一万年以后仍然是这样灿然照耀,能够行走在这阳光下是多么巨大的幸福多么领当不起的命运恩泽,可嘴唇蠕动着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有人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