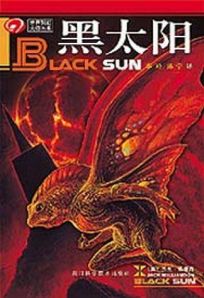太阳之塔-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因为太过安静,以至于远藤马上就听见我的脚步声。他一脸惊讶地抬头,立刻把手上的笔记本合上。
“你在这里做什么?”远藤说。
“那是我的台词吧。”我说。
“居然连这里都找得到。”
“那也是我的台词。”
我抬起头,看着晴朗到让眼睛刺痛的天空。
“你在这里做什么?”
“跟你没关系。”
一个黑色皮包靠着椅脚摆在地上,里头应该都是摄影器材,看起来,他还没学乖,还在玩偷拍。只要可以接近她,就是万死也值得,所以远藤才会跑到这么有深度的地方来,继续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拍摄。针对这件事,我差点就不假思索地把他用龟甲缚的手法绑起来,再丢在这个中庭里。只不过,我不知道龟甲缚的具体绑法。
“你也注意到那个车站了?”
他垮下肩膀,就像是放弃了。
“偶然而已。”我在桌子旁边的另外一张椅子上落座。
“她在哪里?”我开始找人。
“不晓得。不过,应该在某个地方吧。”
远藤好像真的不知道的样子。
“你都跟到这里来了,还是什么都没跟她说?你在干什么啊?真是个胆小鬼。”
“我有我的方法,你少管我。”
他说,多少带了一些忧愁的味道。
“难听的话我就不说了,你住手吧。老像只小老鼠跟在她后头转来转去,这是不行的,你的路会越走越偏。”
“我不想听被甩掉的男人说教。”
“唔,的确,我是没有什么立场说话。”
远藤粗鲁地拉过皮包,取出小小的保温瓶,然后他把之前那种美味的咖啡倒进杯子里,推到我眼前。我刚好喉咙很干,就满怀感激地收下了。
“这里为什么到处都是招财猫?”远藤说。
“我也不晓得,那是谜中之谜。”
我一边喝咖啡,一边瞎扯。
我们时不时地抬头望着天空发呆。这应该是春季的天空吧。
在远藤的公寓谈话时,我就已经对我们两个人面对面时会有什么状况感到些许好奇。这点我之前已经写过。现在的状况,却比之前更诡异许多。眼前,我们就在她的梦里,但是最重要的她却不在,只留下我和他在这里干瞪眼,简直毫无意义可言,性价比实在是差得可以。
我已经意识到再待在这里,恐怕连她的背影都看不到。出现在我眼前的就只有远藤而已,一想到这个我就觉得火大。不过我也注意到,在我发火以前,已经能够享受这种特殊的趣味了。
“那么,你甚至一路闯到她的梦里来,有什么非到手不可的东西吗?”我说。
“不。”远藤摇了摇头,“我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我们两人便相视而笑。
“你也真是不得已哪。”
“我到底是怎么了,好怪。”
远藤看着天空,皱着脸,嘴里发着牢骚。
“你现在就跟个变态没什么两样哪。”我说。
“我可不想被你说成变态。”
“嗯。”
“话虽然这么说,不过,我真的不是这样的人啊!就在我绕着她团团转时,事情就变成这样了。我迷惘了许久,回头才注意到居然迷失在这奇特的森林里,就这么回事。”
“就在你讲什么情情爱爱的时候,你已经腐朽啦。”我说。
“果然还是这么回事吧。”
“现在能怎么办?”
“怎么办呢?”
远藤脸上浮起干笑,他把咖啡从保温瓶里倒出来。
“还是有办法。总是得做点什么才行吧。”我说。
我们两个人喝完了咖啡,看着天空发呆。她还是没有出现。
我们两人的叹息声在中庭回响。
“哪,也不能老是待在这里。”
我站起身,伸了个懒腰。远藤也下定决心,站起身。
“没错,就是这么回事。”
◎
一样是搭乘睿山电车,我们把她的梦幻境地抛诸脑后。
当电车出了田中春菜町的小路,距离天亮还有一段距离。气温还是很低,就跟下雪时差不多。我的太阳穴开始抽痛,皮肤不太够地绷紧。
“你虽然蛮变态的,但人还不错。”远藤说。
“真是失敬啊。”
“哈哈哈。那,再见啦。”他笑着举起手,接着步行离去。
我则往住处走去。
走在夜晚的街道上,万物沉眠。她应该也是一个很好睡的人吧,我想。
她跟我交往的时候,在小钢珠店打工,生活极其忙碌。也因为如此,她在哪里都能睡着。当我看着她就像猫咪缩成一团睡得香甜时,总是一个人发起呆。我曾经很认真地想过,到底我在这里做什么?我也曾经在被恋爱冲昏头的时候想过,她能够这样毫无挂碍地在我身边熟睡,是因为跟我在一起能够很安心的关系吧。这点让我感到非常骄傲。
在我的想像——现在的想像当中,在房里沉眠的她,是不是正在摇摇晃晃的睿山电车里穿过夜晚的街道,前往那遥远的、我不知道的所在?那里的原野森林广阔、阳光明朗,伟大的太阳之塔,是不是正等待着她?
我并不是现在还对那伤心苦恼念念不忘,不过,多少有些难过吧,我想。我踩在冰冷的柏油路上,脚步声响起。
当我抵达白川通的时候,雪花开始飘落。我决定要弄点我最喜欢的肉桂吐司来吃,所以去超市买了一袋吐司,然后走向御荫通的坡道。
在我缓缓爬上坡道时,想起了不久之前我跟远藤的对话。我突然停下脚步,吐出一口白烟。
仔细想想,为什么我要安慰远藤、让他恢复精神啊?那家伙,对自己脱离常轨的行为视而不见,反而对我一阵痛骂,用胶布把我的房间封锁起来,甚至还让我的房间变成昆虫王国。为什么我要安慰他啊?为什么我非得要跟青春连续剧里那种会劝学弟“你要正正当当地跟她交往才行啊”的学长一样,我干吗一定要演这种跟我差了十万八千里远、热血到不行的角色啊?
我注意到自己正多愁善感。“笨蛋!那种不合理的冲动就要赶快排除啊!”我痛骂自己。在这样的状况下,我要怎么去面对饰磨?我可是要跟他一起向圣诞法西斯主义宣战的人啊!
我满怀愤怒地甩着吐司,重重地踏着脚步往我的住处走去。
我才不理她还是远藤会怎么样,我在心里发誓,绝对、绝对不让自己再被卷入那种无法抑制的感伤当中。
◎
高中时代,每年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学园祭。
学生把课业放在一旁,来回奔走准备筹划。他们热衷于胆大的妄想当中,有时,他们会认为自己是在讴歌青春。到了后夜祭(注:后夜祭是学园祭的最后一天。)他们会围着烧得旺盛的火堆,在那时,轻浮的氛围可说到达了一个顶点。就连钢筋水泥材质的校舍,都像是在这样发烧模糊的空气中飘浮起来,浮游于离地三十公分之处。
在这样的忙碌纷乱中,来来往往、成双入对黏在一起的年轻人可说是比比皆是。学园祭,是高中生情侣的大量生产工程。在这样低烧不退的情况下,大部分的学生都会失去理性,甚至深思自己的人生是否活得浪漫,进而轻易地越过那道门槛,哎呀哎呀几声,周围就充满了感情好到放学时会一起回家的幸福情侣。身为一个理性的人,我看着周边来来去去的年轻人,只觉得十分厌烦,那种发情的样子,简直就像在抢夺残存无几的食物一般。我不禁苦笑,我想,我绝对不能变成那个样子。
而圣诞节就是把学园祭的集体错乱现象扩大到全国性规模的日子。若只是学园祭,走出校外就没事了,但如果是圣诞节,便无处可逃。就算躲在自己的住处,圣诞节的阴影也会透过手机的待机画面、大学里的熟人,或者是电视、新闻等各种媒体,执拗地追过来。
“哪,睁开眼睛吧,不要再把自己关在房里了。圣诞节快到啰。”
他说。
◎
随着圣诞节日渐逼近,饰磨的两颊逐渐消瘦,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颇有新撰组那种“近身者斩”的气魄。这绝不是因为他接连不断地向路过的女性发情的关系。每当我去御荫通的小店“Kenya”吃晚餐,总能看到他一天比一天更像释迦佛陀艰苦修行的干瘦模样。像他这样的身体,真的能够撑到圣诞夜吗?我不得不这么质疑。
然而,愈是接近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这个魔鬼的节日就愈是逼近到我们的周围,他会非常紧绷,用他全身的力气去抵抗,到最后,圣诞节当天就会发高烧,每年都会睡上这么一天。这是真的。他的战斗,是如此激烈啊。
“那么,远藤那里怎么样了?”一边吃着汉堡包,饰磨一边问我。
“这个嘛……”
“诶诶,你放着那家伙不管,不会有问题吗?”
“我懒得管他。他怎样跟我无关。”
“这样啊。也好。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可得集中精神对付圣诞节才是。”饰磨说。接着,他露出了非常奇异的微笑。
即便如此,我只要稍微想像一下,在他那消瘦衰弱的体内,那个“‘不好吗?’骚动”妄想是多么高浓度团团转着,我就几乎连鼻血都要喷出来了,肚子也饱了。不过,打打嘴炮、卖弄自己的妄想,也是饰磨的拿手好戏。或许他出乎意料之外地并没有对圣诞夜有任何计划也说不定。“‘不好吗?’骚动”,我实在没办法从这个愚蠢的名字想到什么“凄绝的战斗”,不过这样微妙的判断,也很难用普通的会话表达出来。
如果要对这个折磨了我们五年的圣诞法西斯主义进行最后的报复,就只剩今年了。最起码,不能重蹈那个冬天的覆辙。为了他,也为了我们自身的尊严,我如此祈祷着。
那是我大二的时候发生的事。
那年的十二月中旬,我们四个人前往四条河原町,计划去拜访位于寺町通、每年都对我们多有照顾的铃木唱片行。我们每年会去那里买偶像月历,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素材。那天,我们一边说着“圣诞节是什么东西啊”,一边打算要无忧无虑地在街上晃荡时,被一阵意料之外的强风给掀得乱七八糟,连同我在内的四个男人,为了要做什么而陷入争论的泥淖中。最后则是在莫名其妙的状况下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