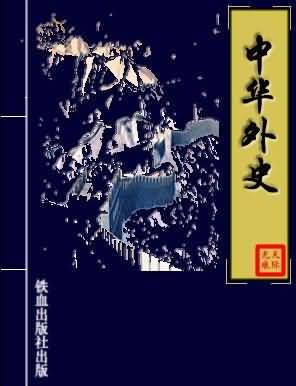春明外史-第6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们又没同在一个学校读过书,怎么算是同学?”徐二先生道:“不然,从前同
拜一个老师的,都称为师兄弟。现在我的教员,当过他的教员,和同门拜老师一样,
怎么算不得同学?你还不知道呢,他兄弟两个,和气得很,一见就要我换帖。我想
他们都是简任职,我连一个荐任职还没有巴结上,怎样可以和人家换帖?所以我极
力推辞,不肯奉命。不过他两个人给我的名片,很算得我一种交际上的纪念品,我
就留下来了。”
杨杏园听他说话,一面将书翻着。只见书的总序后面,有半页白纸,上面行书
带草,写了十几行小字。字虽写得极小,但是笔法秀丽,看得很是清楚的。把那段
文字,从头至尾一看,却是一段小跋,写的是:
孟夏日永,端坐多暇,作茧余热,捣麝成尘,顾影自怜,徘徊几榻。因检点旧
笈,收拾残篇,闲取一卷,自遣愁闷。忽得是书,重睹先人手泽。犹忆十三四岁时,
先严赐果案前,抚鬟灯下。常为指点四声,口授诵咏。时窗外月落梧桐,风传蟋蟀,
娇笑憨问,秋漏每尽,一展斯篇,依稀如梦,释卷怃然,不期双袖之湿也。浴佛前
一日,就槐荫窗下,磨陈松烟墨随笔。
杨杏园念了一遍,不觉失声道:“竟是一篇六朝小品,好清丽的文字!”再一
看那段文字下面,印了一颗小图章,是两个篆字。看了半天认出那篆文,是“冬清”
两字。心想看这文和这个印章,一定是个女士了。照我看来,一定还是几十年前的
大家闺秀哩。便问徐二先生道:“你这书从哪里来的?”徐二先生道:“花三十个
子儿,在琉璃厂书摊子上收来的。”杨杏园道:“世上的东西,真是没有一定的价
值。有人爱它,就当着珍宝,没有人爱它,就只值三十个子儿了。”涂二先生不懂
他的意思何在,还想问呢。有人在院子里喊道:“徐二先生在这里吗?”徐二先生
道:“你别忙,我就来,反正和你打起两块头子钱得了。”那人道:“那末,我就
去催他们了。”杨杏园问道:“什么人邀头?”徐二先生道:“说起来好笑,就是
住在隔壁屋子里,刘议员的兄弟刘子善,这一些时逛起来了。昨天晚上,有两个学
生,又带了他去逛二等,怂恿着他快活一夜。他正和哥哥要了几块钱,身上带着六
块,一时高兴,就答应了。那两个就拉他在一边,教他放下三块钱,又教他回去换
一身小衣服再来,刘子善都照办了。回到会馆,他一声不响,自在屋里换小衣。忽
然听到我屋子里的钟,已经敲了十二下。心想往日这时候都睡了,今天还要出去呢。
换衣服的时候,打开皮夹子一看,只剩三块钱。又心想要买好多东西都没买,这样
的花去三块,岂不冤枉?今日若是早睡一刻,就省下来了。越想越心痛,越心痛越
舍不得。就和那两个学生吵着,要去退钱。两个学生被他吵不过,只得和他去了。
那窑姐儿当然不肯,刘子善哭丧着脸,说要告诉他哥哥。两个学生,又怕刘议员知
道了,说好说歹,退回来了两块钱。还差一块钱,两个学生就替他邀一场小麻雀牌,
给他抽头抽出来。我就是四角之一。”杨杏园笑道:“胡说!没有这样的怪事。”
徐二先生道:“你不信,回头我们打牌的时候,你去看一看就明白了。”杨杏园笑
道:“他哥哥刘续,本来是个新补的议员,来自田间,为日无多。他这兄弟,当然
是个老土了。老土花钱,没有舍得的,你说的话,也许可以打对折相信。”徐二先
生道:“说了半天,你还是疑信参半,我不和你辩论了。那里还等着我呢。”说着
自去了。
杨杏园一人坐在屋里,将那本《花间集》打开,见是哀感的句子上,或是用红
笔,或是用黑笔,都圈两个圈。看了这本,再看那本,都是一样。心想这冬青女士,
一定是个伤心人,所以遇到哀感的句子,都表示同情。由此类推,她一定也是个女
词章家了。翻着书,随手打开一页,只见书页里面,夹着一张纸条。条子上写着两
首七绝:
净水瓶儿绿玉瓷,秋花斜插两三枝,
移来意态萧疏甚,相对凄然读楚辞。
霜后黄花不忍看,铜屏纸帐润秋寒,
晚来几点梧桐雨,愁煞灯前李易安。
杨杏园念了两遍,看看那个笔迹,正和那位题跋的冬青女士一样无二。心想道:
“这位女士何怨之深?看她后面一首诗,却是崇拜李清照的,词一定填得好,我来
翻翻看,书里面可还有她的大作。”想着把书乱抖了一阵,却是没有。在睡椅上,
拿着那纸又念两遍,心想“清丽得很,我却做不上来。这样的女子著作,我还不多
见呢。”
他一人在这里想得出神,无如隔壁院子里,哗啦哗啦,那打牌的声音却闹不休。
杨杏园被麻雀牌的声音吵不过,心里很是烦躁。便放下书慢慢的走出来,到隔壁院
子里去。走到刘子善的屋子边,由窗懦朝屋里一看,徐二先生等四个人,正在那里
打牌。那刘子善却背着手站在一边看,杨杏园情不自禁的,也就走了进去。徐二先
生一回头说道:“你是最不愿意走进别人屋子的。怎么来了?”杨杏园笑道:“你
们能打牌,我看一看还不行吗?”说时,这刘子善早客客气气的递过一支烟卷来,
杨杏园接着烟卷道:“我们同住一个会馆,不必客气。’划子善又擦了一支火柴,
递给杨杏园。他只得接过来,燃着烟卷吸了一口。这一吸,不打紧,几乎把嗓子都
呛断了,不由得咳嗽了一阵。这烟味又辣又燥,也不知道是什么烟,拿在手里却不
敢吸。刘子善却毫不为意,自取了一支在手上,在抽屉里翻出一把剪刀来,将一根
烟卷,剪成三截,把两截放在窗台上。另外在窗台边水烟袋上,取下一支纸煤筒来,
衔在嘴里当烟嘴子,却把一截烟卷塞在筒子里燃着吸了。他吸了一口,由鼻子里喷
出两道青烟,然后问杨杏园道:“这两天,和家兄谈过吗?”杨杏园道:“我这几
日身体不好,不很出来,没有会到令兄。”刘子善道:“本来也不容易会到,他就
很忙,昨日晚上,他一点多钟才回来。今天上午就在什么堂吃饭,听说是内务总长
请的。两点钟还有一餐,晚上八点钟,是他们党里请客,吃的地方就更奇了。说是
在前门火车上,吃外国菜。当议员的虽没有品级,照我看和总长都是并肩一样大。
不谈别的,这口福就不小了。”杨杏园一边听刘子善说话,一面看牌,顺手就把手
上的烟卷,扔在地下。刘子善看见还有一大截烟,杨杏园就扔了,心里怪难受的,
想捡起来吧?又有些不好意思。眼瞧着那半截烟,只是转个不住。这时,桌子上已
经成下来了一个三翻,却只抽四个子儿头钱。刘子善嫌太少,便不依道:“像你们
这样抽头,什么时候,才可以抽到一块钱?”桌子上有一个人笑着说道:“没吃没
喝的场面,就只有这个样子。”刘子善不知人家是玩话,说道:“我家已在党部里
打牌,吃喝都是自己的,为什么一回头钱,就好几十块呢?”那人又笑道:“人家
是抽头给听差的,你呢,不是议员的本家老爷吗?”徐二先生最是要联络议员的人,
就不肯得罪议员的兄弟,觉得那人的话太重了,便道:“刘先生原不是邀头,不过
我们凑一个茶围钱,闹着好玩罢了。”那人将牌一推道:“我不要议员写介绍信,
我不联络这样一个具本家老爷。”说着气愤愤地走了。大家面面相觑,一场没趣。
杨杏园也就忍着笑走出来。刚走到院子里,只见那刘续议员,匆匆的在外面进来,
手上拿着一根司的克,一摇一摆的走。看见杨杏园,便对他招手道:“来来!我有
一段好新闻告诉你。今日下午,陈总长在忠信堂请议员,杨先生知道吗?”杨杏园
道:“不知道。”刘续走到他身边低着声说道:“陈子徐的总长,都在我们手板心
里,他不能不联络我们。在候补议员里面,大半都是不很熟悉政局的,惟有我一人
能在党里拉拢几十个人,却有几分怕我。此外我还有一条消息告诉你,也是很重要
的,昨天我们党部里开会,我被举为十二干事之一。这两条务必请在贵报登一登。”
杨杏园随口答应道:“可以的。不过我的记性不好,恐怕忘了。最好请你做一篇稿
子送来。”刘续道:“好,回头我就编一篇送来。我还有许多建议案,还没有修改
好,等修改好了,也可以送到贵报,尽先发表。我这个提案,和中国前途,都大有
关系,不可藐视。其一:是中国无宗教不足以正人心,端国本。请立大同教,以孔
子为大同教主。其二:请咨达政府令全国各学校,不得作白话文。以中文为主,洋
文为宾,庶几合乎圣人用夏变夷之旨。其三;今之代议士,皆为全国之俊彦,今在
立法机关,为人民代表,固位置极优。一朝任期终了,仍为平民,颇非国家爱惜贤
才之至意,应一律给予简任职。其有继任议员或转为官吏者,固不必论。否则应逐
年给予养老金。以上三件,是我提案里面最重要的,足下看看好不好?”杨杏园道:
“很好,都是应该提出的。”刘续道:“老实告诉你,我们党里这一百多人,我都
可以指挥。原因就是因为我既能做文章,发言又有道理。”杨杏园道:“贵党有许
多人,那在国会里面,实在有一部分势力。贵党部现设在什么地方?”刘续道:
“在土地庙九十九号,昨天还在那里开全体大会呢。”杨杏园道:“不是吧?那个
地方,是我一个朋友家里,我很熟悉。他虽是一个议员,屋子不过两进,除了自己
家眷在后一进外,另外一进,只有六间整屋子,常常有几个议员在那里打小麻雀牌
玩,似乎不像一个党部。一百多人,怎样好在那里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