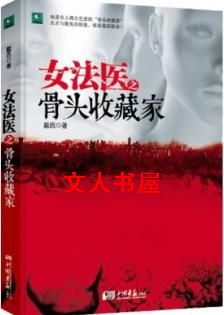骨头在说话-第3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拍立得照的,另一种是五乘七的彩色照片。接线生回来了,她说到处都找不到莱恩。好吧,她叹口气,再去咖啡室替我找人。
我翻动这些拍立得照片。一张猴子尸体送进陈尸室时的相片。一张紫黑色运动袋的相片,拉链拉上和拉开的都有,后者可看出袋里有一捆东西。接下来那张照片是那捆东西放在解剖台上拍的,还没有解开捆绑。
剩下的六张相片拍的是猴尸各部位。由放在解剖台上的小刀,可以看出尸体的确很小,比胎儿或新生婴儿还小。腐烂的情况很严重。肌肉已开始发黑,上面好像还爬有小虫。摄影者站的位置太远,尸体表面又太脏了,我只能概略分辨出头部、躯干和四肢,无法看得更清楚。
接线生回来了,她肯定莱恩不在那里。我只好再留个话,便挂断电话,等明天再和他联络。
这些五乘七彩色相片的摄影位置较近一些,而且尸体也清理过了,一些拍立得相片看不出的细节,现在都清晰可见。这个小动物被剥了皮、切成数块。拍照片的人也许是但尼斯,他已经把尸块按原来的位置排列好,才开始拍摄。
我翻开这些照片,不由得想到肉商宰好待炖的兔子。只有一个部分例外,第15张相片展示出一只细小手臂的末端,有四根完整的指头和一根向手掌内卷曲的拇指。
最后两张照片拍的是猴子的头部。去掉毛皮,猴子的头部看起来真的很像初生胎儿,赤裸而脆弱,只有桠柑大小。不过,尽管它脸看起来很平,五官酷似人类,但不需要请教珍·古德(Jane Goodall),就能知道它不是人类小孩。它的嘴里长满牙齿,连臼齿也长出来了。我计算了一下,上下左右各有三颗小臼齿。这只“终站猿猴”是从南美来的。
这只是另一个动物尸体的案子,我对自己说,一边把照片放回信封。我们经常会处理这种案件,被猎人遗弃剥了皮的熊爪、被宰杀猪羊的废弃器官、被丢人河中的狗或猫。总是会有人误把它们的尸体当成是人。不过,人类的残忍总是让我震惊不已。我永远也没办法适应。
为什么这个案子会引我注意?我又看了一次五乘七照片。我知道,是因为猴子也是被人分尸的。很好。我们经常看到动物尸体,有些混蛋会以虐杀动物为乐。就这件案子而言,也许是一位被当掉的学生,拿教授养的猴子出气。
看到第15张相片时,我停住了,目光被钉死在相片上。再一次,我又感到胃部打起结来,我看着这张相片,伸手拿起电话。
二十三
在下课后,再也没有比学校大楼更空的地方。这使我想到中子弹爆炸后的遗迹。日光灯照耀,水池喷着泉水,钟声按时响起,电脑终端机诡异地运作,人们都不见了。没有人交头接耳,没有人疾步跑向课堂,也没有键盘敲打声。整个校园沉静得就像地下墓穴。
我坐在魁北克大学派克·拜雷教授的办公室外的长椅上。离开法医研究所后,我先到健身房运动,再到超市买了一些日用品,然后吃了一份蛤蜊酱意大利面。现在,我则是一个人不耐烦地在此等侯着。
若说生物系很安静,不如说它像夸克一样小。楼上楼下各教室办公室的房门都早已关上,而我不仅把走廊上布告栏的内容全看过,而且看了两次。
我第一百万次低头看表——晚间9点12分。该死,他9点下课,现在早该出现了。至少,他的助教是这么说。我站起来,来回距步。似乎等人就一定要踱步……9点14分。混帐。
9点30分,我放弃了。当我把皮包挂上肩,准备离开时,我听见从视线以外的地方传来一扇门开启的声音。一会儿后,一个抱着一大叠实验书籍的男人匆忙从转角走来。他穿着一件破旧的羊毛衫,一边走一边调整手臂姿势,以防书本掉落。我猜他的年纪大约40岁左右。
他看到我,便停下脚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正准备自我介绍时,一本书从最上层滑落。我们一起向前想接住那本书,结果,他原本捧住的书全垮了。大大小小的书本像纽约市新年洒的碎彩纸般,一下子全四散在地上。我们一起花了几分钟把书一本一本捡起来,然后他打开办公室大门,把这整叠书放在桌子上。
“很抱歉,”他讲的英文有浓厚的法国腔。“我……”
“不要紧,”我说:“我一定吓到你了。”
“是……哦,不。是我不对,我应该分两次拿。我每次都这样。”他说的并不是美式英语。
“这都是实验用书?”
“是的。我刚才教的是生态学。”
在河岸那端,夕阳的光芒透进窗内,轻轻映在他的身上。苍白粉红的肤色,浆果般红的双颊,香英兰色的头发。他的胡子和睫毛都是琥珀色的。他整个人像是烧出来的,而不是晒出来的。
“听起来满有趣的。”
“希望我学生们也这么想。我能……”
“我是唐普·布兰纳,”我说,从皮包里掏出一张名片给他。“你的助教说我可以在这个时候来找你。”
他接过名片,我把来意表明。
“没错,我记得那件事。那只猴子不见了害我难过得要死,它总是逗人开心。”突然,他叫道。“你何不坐下来谈?”
我还来不及反应,他便匆忙把一张椅子上叠的书籍杂物全搬到地上。我趁机环顾四周。他的小办公室让我联想起洋基队的体育馆。
在办公室内每一寸墙壁上,只要有空位,就贴上各种运动的照片。棘鱼、珠鸡、狨猴、疣猪,甚至土豚,完全不按动物分类法,乱七八糟地挂在墙上。
我们面对面坐着。他坐在办公桌后,脚搁在一只拉出一半的抽屉上,而我则坐在挪出空位的椅子上。
“没错,它真能逗人开心,”他又说了一次,然后话题一转。“你是人类学家?”
“嗯哼。”
“熟悉灵长类?”
“不,曾研究过,但不太熟。我曾在夏洛特的北卡罗来纳大学人类学院教书。有一次我开过灵长类生态或行为学的课,除此之外,就很少触及这个领域。光是法医的事情就忙不过来了。”
“很好,”他摇着我的名片说:“你怎么研究灵长类的?”
奇怪了,到底是谁调查谁。“我对灵长类的骨质疏松症很感兴趣,尤其是社会行为和疾病发生的相互作用关系。我们研究动物模型,也常利用恒河猕猴,操纵它们的社会组织,制造压力状况,然后再研究它们骨头的变化。”
“你有到野地研究过吗?”
“只到过一些小岛而已。”
“哦?”他的眉毛拱成弓形,一副充满兴趣的样子。
“例如波多黎各的圣地亚哥岛。过去我在南卡罗来纳的摩根岛上一所学校教了几年书。”
“有恒河猕猴吗?”
“有。拜雷博士,你能不能讲一点关于那只失踪猴子的事?”
他不理会我的要求,仍追问道:“你怎么从研究猴子骨头变成研究人的尸体?”
“骨骼生物学。这是两者共同的核心。”
“啊,说的也是。”
“猴子的事呢?”
“那只猴子,也没什么好说的。有一天早上我进到研究室,发现笼子是空的。我们猜也许有人忘了把门闩锁好,或者,也许是阿莎——那只猴子,自己把门闩打开。你知道,它们的确会这样做。它的手灵巧得很。总之,我们找遍整个校园,也问过校警,找过每一个角落,结果你都知道了。”
“你养那只猴子做什么研究?”
“事实上,阿莎不是我的研究计划,是一个学生的。我虽然对动物沟通系统很感兴趣,但这不是我的专长。”
“你学生的研究计划是什么?”我问。
他皱了一下眉头,摇摇头说:“语言。新世纪灵长类学习语言的能力,这是玛丽丝的研究项目。”他拿起一枝笔在前额晃着,哼了一声,然后重重在桌上敲了一下。
“玛丽丝?”
“我学生。”
“实验成功吗?”
“谁知道?她根本没有时间。计划才开始5个月,猴子就不见了。后来玛丽丝也走了。”
“她休学了?”他点点头。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拿着笔在实验书上画着三角形。我等着,给他时间自己思考。
“她交了男朋友。那个男孩子经常来学校骚扰她,闹着要她休学。她只对我提了一两次,但我想这一定是主因。我在学校办的舞会上看过那男的几次,我总觉得他有鬼。”
“怎么说?”
“就是……我也不知道,反社会倾向、愤世嫉俗、性格乖癖、态度粗鲁。他好像也没什么一技之长……我一看到他就想到猴子。你知道吗?他好像从小就离群索居,不知道该怎么和他人相处。不管跟他说什么,他总是眼神不定地傻笑。天啊,我讨厌死他了。”
“你怀疑过是他干的吗?也许是他杀了阿莎,好让玛丽丝研究不下去,迫使她休学?”
他的沉默告诉我他的确曾这么想。“听说那时他人在多伦多。”
“他有提出证明吗?”
“玛丽丝相信他,我们也无话可说。她那时难过得要死,追查又有什么用?反正阿莎都死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问接下来的问题,不过还是开口了。“你看过玛丽丝的研究报告吗?”
他停止涂鸦,眼神锐利地看着我。“你是什么意思?”
“她会不会故意隐瞒什么?有没有别的因素使她想放弃这项研究?”
“没有,绝对没有。”他坚定地说。但是他的眼神却是否定的。
“她还和你联络吗?”
“没有。”
“你的学生都不和你联络?”
“有的会,有的不会。”他又开始胡乱画起三角形。
我换个方向问。“还有谁会接近那个……是实验室吗?”
“只是个小实验室。养在校内的动物不多,因为地方不够。她也知道,每个动物都得养在不同的房间。”
“哦?”
“法律有规定,不管是研究用、商业用、私人饲养,都必须遵照政府颁布的规章饲养。”
“有没有关于安全的规章?”
“当然有,那规章是很详细的。”
“那你们采取什么安全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