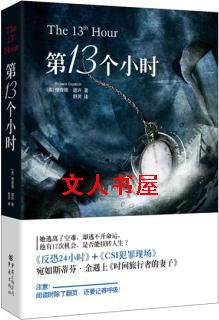2013103101-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地方都更狂热、更持久。重庆人干什么事儿,都是一窝蜂一窝蜂地去干,这跟受教育程度没什么关系,他们好像天生就是这样。
重庆人挣钱不多,但特别容易满足,尤其是通过吃饭的方式满足。他们全部的热情、精力和想象力似乎都体现在了饭桌上。每次我到舅舅家或者黄阿姨家里,要不了多久,他们就弄了一大桌好菜。一顿饭吃完,我基本上都是吃到嗓子眼儿了,两口茶刚喝下去,他们又问了:“晚上你想吃点儿什么?”真没办法。
重庆人特别热情,但似乎又太不善于表达热情,需要相当长时间的交往后,才能感受到他们那种发自肺腑的、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热情。我的重庆朋友没有几个会说话的,尤其不善于用语言表达他们的感情,只有处的时间长了才能用心感受到。我离开多年之后回重庆见亲戚朋友,一般来说,那么多年没见面了,总会热情拥抱或者寒暄什么的,但是他们没有,看到我的表情跟昨天还见过我一样—我能理解,他们的感情都刻在心里。
3、自恋的重庆人
重庆人的性格中,我觉得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自恋。他们有一种不知道来自哪里的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最典型的体现是美食和方言。
全国各地很多人都喜欢川菜和四川小吃(重庆菜也算在广义的川菜里了)。重庆人因此对他们的美食特别自恋。自恋到什么程度?只要有重庆人调到外地工作或者移居外地,重庆老乡碰到他们都会问:“那地方的菜怎么吃啊?怎么吃得下去啊?吃那些东西你们怎么活得下去啊?”并且你会发现他们在说这番话时发自内心的同情溢于言表。重庆人其实很容易接受新生事物,但他们偏偏很难接受外界的食物。在他们看来,只有吃重庆菜才能生活。我妈离开重庆都那么多年了,现在遇到重庆老乡,还是每次都会被问及上述的问题,而且你永远也不会听到重庆人夸别的地方的什么东西好吃。
这种对饮食的优越感和他们的狂热天性一样,和受教育程度没什么关系,从知识分子、机关干部,到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徒全都一个样。重庆日报社、重庆电台,这都是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地方,那里的人也都这么认为。因此我也觉得特别奇怪—难道他们没有去过重庆以外的地方吗?没有吃过川菜以外好吃的东西吗?
而说到重庆的方言,重庆人的自恋更是近乎滑稽。我至少听一百个重庆人说过:“其实我们重庆话,还是很像普通话的。”每次听到这里,我都忍不住告诉他们:“我认为重庆话和普通话的区别,就像广东话和东北话的区别那么大!”而认为重庆话和普通话很像的绝不是个别人的感受,那几乎是重庆人的集体意识。我每次不赞同他们意见的时候,所有重庆人都很吃惊,这也就让我更加吃惊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被彼此震惊了。
可能会有人认为我夸大其词,你要不信,可以到重庆去,随便找个人跟他说“我认为重庆话很像普通话”,他们肯定会对你说:“对对对,你说得特别对!”
4、袍哥式义气
重庆人很江湖,特别讲义气,可能多少有些受袍哥文化影响。在很多重庆人的逻辑里是不是朋友是特别重要的标准,相比之下,是非标准反而淡一些。比如,打女人对不对?我们都会认为,怎么能打女人呢,肯定不对啊!可是到了很多重庆人那里,如果是朋友打了女人,他们会说:那也得看那女人该不该打。但如果换作不是朋友,他们会义愤填膺地说:这他妈是啥子男人哦,简直是畜生,男人啷个可以打女人呢?!
说到江湖义气,又让我想起酒。重庆人喝酒不像其他地方,你敬我一杯,我回敬一杯,我再敬你,你再敬我,如此你来我往。重庆人喝酒必划拳,输的喝。开始我很不适应这种风俗,大夏天的,十个八个朋友一桌吃火锅,又烫又辣,想喝点儿啤酒,不行,得划拳,输的才能喝。那一套划拳的酒令跟说相声一样,重庆的男女老少基本上都会。因为我刚学,划拳总是输,只能自己一杯杯地喝。几圈下来,旁边有人喊了:“哎呀,这个酒你也不能一个人喝嘛,天这么热,也让我们喝几杯嘛。”
重庆的酒令也很有意思,一套一套的,从一到九,都有说辞,说辞还很幽默,有历史,有现实,当下最流行什么,重庆人都能与时俱进地把它融入酒令里。可惜我就是学不会,也没记住。我只记得这么一段:“酒酒酒(九九九),好朋友,万事莫过杯在手,我愿长江化作酒,有朝一日跳到江里头,一个浪子一口酒。”这要用重庆话说出来会很有意思。有兴趣的朋友到重庆去玩儿,可以留意一下他们划拳的酒令,绝对是一种有趣的酒文化。
5、吃不够的小面、凉面
全国人民爱吃川菜,不仅因为它好吃,而且因为它大众。川菜的材料基本上都不算高档,大多是猪身上的东西,贵不到哪儿去。同样的钱请人吃川菜能摆一大桌,而请吃粤菜,可能就只有两道菜。
川菜让人迷恋的原因都在调料里,所以重庆有句话叫“吃的是作料”。重庆最让我魂牵梦萦的不是川菜,也不是火锅,而是路边摊上的小面和凉面。小面其实就是最普通的素面,作料是关键。我小时候的小面是六分钱一两,我一般吃二两就够了。那种味道对我来说,至今想起都是幸福的味道。
前几年回重庆,我出去逛街或者上亲戚家串门儿,回外婆家的路上是一路走着一路吃着路边的凉面回去。重庆路边摊上的凉面都是用小碗装,面很少,基本上就两筷子的,但调料放了十几样,一碗面两口就吃完了,辣得心脏都疼。我接着往前走,买一瓶冰饮料,咕嘟咕嘟喝下去。大约过十分钟心脏不疼了,嘴唇和舌头也恢复知觉了,又看到一家卖面的,再来一碗,又是两口吃下去,又辣得不行,接着再来一瓶饮料。就这样,一路走到家也吃饱了。
上次回重庆我特别想吃小面,一大清早在去机场的路上,我不停地念叨着,热情的司机为了满足我的愿望竟然带我到了机场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找到了一家小面馆。我高兴坏了,热热乎乎的一碗小面吃下去,幸福感就在心里和胃里荡漾了一整天。
关于小面,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就算把所有的作料都原样给你,到南京就弄不出那个味道。我妈曾经多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所以现在每次有机会回重庆参加活动,主办方问我有没有什么其他要求,我的回答全都是:有,小面!
南京也有很多种面,但那基本就是酱油面,加块大排叫大排面,加块小排叫小排面,加大肠叫大肠面,说起来有几十种,其实面都是一个味道。而重庆的面虽然就三四种,但不同的作料却调出了截然不同的口味。相比之下,南京的面条实在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第六章小资本家爷爷
我爷爷很像电影《林家铺子》里的那个掌柜。爷爷是扬州邗江人,十几岁时一个人挑着担子进城当学徒,慢慢积累了本钱,后来开始自己做买卖。再后来,生意做大了,他和两个朋友合伙开了个钱庄。在那个时候能开钱庄应该算比较发达了。听我的叔叔伯伯们回忆,大概在一九四九年,爷爷还上过国民党的金融年鉴。当然,我有些怀疑那种年鉴跟现在一样,是给点儿钱就能上的那种。但不管怎么说,我爷爷都应该算小资本家了。
1、无法兑现的金条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的炮声近了。爷爷和他那两个朋友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去台湾。如今的我无论如何也弄不到二〇一二的船票,而当时我爷爷如果变卖家产,是能让一家人去台湾的。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爷爷权衡再三,终于横下一条心—不走了!今天我估计,老爷子当年最主要的判断恐怕是,自己又不是什么大资本家,要镇压资本家也还轮不到他这样的小资本家头上。最后爷爷把家产全变卖了,留了下来。
爷爷的两个朋友也抱着同样的心态留了下来,都变卖了各自的家产,最后三家人凑了一百根金条—那时候的法币跟草纸没什么两样,只有金条是硬通货。他们把这一百根金条存进了当时的国民党中央银行,票据上写了我爷爷和他两个朋友的名字,三人各执一份。
等到新中国成立后没多久,他们就发现这件事儿说起来变得很可怕了—虽然他们没去台湾,但在那个年代,家里存着国民党银行的金条存单也是天大的罪过。三家人冒着杀头的风险,想尽各种办法保存着各自的银行存单,一直保存到了“文革”之前。但当红卫兵开始大规模地抄家后,他们也就不敢留着那张存单—如果被抄家抄出来,真不敢往下想。万般无奈之下,我爷爷把金条的存单悄悄烧了,和另外两家人也失去了联系,爷爷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去世了。
到了八十年代末,我的叔叔、姑妈们所在的国营工厂倒闭的倒闭,停薪的停薪,这时候他们就回想起了爷爷在世时说过的金条。他们算计着,要是能找回那一百根金条,三家人平分,怎么也得有三十根吧。三十根金条再加上存了三十多年的利息,那可就发了!
在黄金梦的强烈驱使下,我叔叔真联系上了爷爷两个朋友的家人。我爷爷的朋友也都过世了,他们的后人也都知道有金条的事儿,但悲摧的是,“文革”抄家时,那两位老人也和我爷爷一样,没敢留着那张可能导致家破人亡的银行存单,不约而同地都把它给烧了!烧的时候三家人的想法还都一样—我烧了不要紧,另外两人会留着的,有朝一日去银行,上面不是还有我的名字嘛。就这样,悲剧了。
最后,我最小的也是混得最不济的叔叔,抱着渺茫的希望,辗转给台湾那边的银行写信,查询那一百根金条的下落。当时两岸还没“三通”,民间书信往来都要通过中国香港红十字会中转。几经辗转,台湾那边居然回函了。根据我叔叔提供的姓名、年份等信息,银行确认了这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