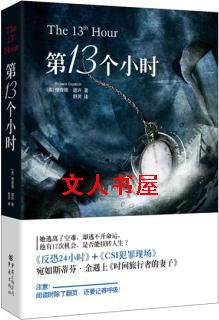2013103101-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大盒子后来主要用来放我的饼干之类的零食。遗憾的是,几次搬家加上后来父母离婚,其中一部分相片再也找不着了,非常可惜。
父亲给我和我哥拍过很多非常生动的照片,现在看来都是很有技术含量的。现在的单反相机都是自动对焦、自动测光,虽然也可以手动,但是相机完成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作。当时父亲用的是双反相机,取景一个镜头,成像一个镜头,取景还是竖式的,用好这种相机拍出好照片是相当需要技术的。当时我爸拍了很多我和我哥打闹玩耍的照片,手动曝光,手动快门,还要抓情绪,考虑构图,还不能浪费胶片,拍完之后,还要自己在暗房冲洗。小时候看这些照片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现在自己玩相机了,再看那些照片就知道厉害了。老爸现在退休多年了,我哥要送台相机给他,让他没事儿拍着玩儿,结果他却说不拍了,问他为什么,他说,现在这些日本相机我不会用。
4、第一次去西安
我父母在西安团聚后,我去过西安两次,都是去过暑假。我还记得在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去西安的情形。
放假以后,外婆买了火车票,把我送到菜园坝火车站,找了个列车员熟人把我送上火车—以他们的社会关系,最多也只能够上列车员了。说是让列车员关照我,但人家忙着呢,哪顾得上我。那个列车员阿姨就只是把我弄到列车员休息室,让我在里头坐着。我也听话,挎着一个小包就傻乎乎地坐着,看见她开始扫地了,我还过去帮忙。列车员阿姨连忙说:“别动别动,好好坐着,别乱跑!”我就又乖乖地坐下了。
那时从重庆到西安要坐两天火车,出门前外婆一再叮嘱:“中途在哪儿停站都别下,等所有人都下的时候你再下,那是终点站。记住,等一车的人都走的时候你再跟着走。”我懵懵懂懂地点头说好。
其实那会儿我已经明白了,尤其是一路听见广播里报站,等到听见“西安站到了”,我也就毫不迟疑地跟着下车了。但是西安站那么大,对于一个八岁的小孩儿来说,那个世界瞬间变得不知道有多大,有那么多火车来来往往,有那么多人进进出出。我就记着外婆叮嘱的—跟着大人走。于是,我就跟着我们那一列车上的我认得的人走。出去以后是哪儿,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爸妈和哥哥会来接我。
当时也就到大人屁股那么高的我,在黑咕隆咚的夜里,也不知道害怕,谁也不认识,就那么懵懵懂懂地出站了,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里。出站没走多远就听到了我哥叫我的声音。
暑假过完,我又按照之前来的程序,坐上回重庆的火车。想想现在的父母,之所以不敢让孩子这样出门,恐怕也是因为现在的社会治安没有当时那么好了。
西安是著名的旅游城市,大雁塔、华清池、兵马俑这些著名景点我都去过,但没什么印象了,只对一顿饭印象特别深。
我第一次去西安,一家人难得聚在一起,父母特别高兴,带我们下馆子。那是一个国营大馆子,叫“五一饭庄”,当时是西安最高级的大饭店之一。下馆子对当时的我来说是非常新鲜和高级的体验,因为在重庆,节俭的外婆认为下馆子是有钱人和不会过日子的人干的事儿。她什么都是买回家自己弄,把家里的伙食操办得很好,所以我在重庆就没有下过馆子。
那天在五一饭庄我和我哥一人点了一碗面,是有浇头的那种,还有两屉小笼包。那是我第一次吃小笼包,一口下去我就震惊了,完全没想到世界上还有那么好吃的东西。回重庆之后,我对小笼包子的幸福回忆持续了将近一年。童年的我心里暗暗地想,我要是当了皇上,天天让御膳房做小笼包子给我吃!直到今天,熟悉我的朋友、同事都知道小笼包子仍然是我最爱的食物之一。
几个月前,在化妆间我偶然跟黄菡讲起这段经历,没想到她也在西安待过,家里人也带她在五一饭庄吃过饭,甚至也特别说到了那里的小笼包。更想不到的是,她在西安待的那段时间也是一九七八年。黄菡比我大四岁,当时她在西安上学,住在亲戚家。听了她的话我就想:一九七八年,一个八岁的男孩儿,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儿,互相不认识,可能在同一天,在同一家饭庄,吃着同样的东西。三十多年后,当年的两个小孩儿已是中年人,成了朋友,又同时出现在了今天的《非诚勿扰》上,这是件多么神奇的事儿啊。
5、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我在重庆的亲戚都是最普通的劳动人民,文化程度都不高,但都同样憨厚善良、热情好客。他们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姨婆一家,我童年欢乐的记忆有很多都出自她家。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姨婆不是外婆的亲妹妹,她们是在抗战期间逃难的路上认识并结为姐妹的,但她们一辈子比亲姐妹都亲。我们两家的关系甚至比有血缘关系的还好。
那是特别可爱而且有意思的一家人—他们家也是“母系氏族”。姨婆在印刷厂工作,是个整天乐呵呵的胖老太太,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她嘴里永远都有说不完的俏皮话,她的语言似乎与生俱来地带有劳动人民草根式的幽默。她的那些话如果写出来一点儿也不好笑,但通过她的嘴,用她特有的方言和腔调说出来,就特别好笑,特别有感染力。我外公外婆的话不多,更缺乏幽默感,相比之下我姨婆是个话痨。逢年过节去他们家,从一进门开始,她就说个不停,一屋子人都被她感染了,笑个不停。
我叫姨婆的儿子“舅舅”,他和我妈一块儿长大的,一辈子都在供电局抄电表。打我记事儿开始就没听这个舅舅讲过几句话,偏偏我舅妈也是个话痨,也没什么文化,跟姨婆还特别能讲到一块儿去。她们是我这辈子见过的关系最好的婆媳。舅舅、舅妈生了一儿一女,分别是我表哥、表妹。表哥话也不多,表妹又是挺能说的人—说他们家是母系氏族真一点儿不夸张,他们家的话都让女人说了。
后来我回重庆也常到舅舅家吃饭。他爱喝酒,也能喝,他喝的酒很便宜,经常是几块钱一桶的散装高粱酒。我和舅舅喝酒的时候,就听舅妈、表妹一直不停地说,问这问那,他们家、我们家的事儿轮流说。舅舅在边上默默地坐着,隔个两分钟就端起杯子冲我说“喝一个”,一斤酒喝到底儿了,他从头到尾基本上只有这么一句话。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还有我妈在重庆电台最要好的同事黄阿姨。她是电台的资料员,前几年她去世了。我记得当时我妈接到黄阿姨女儿报丧的电话时,我正好在吃饭,看到我妈拿着电话听了没有两分钟突然放声大哭。
我小时候逢年过节有一半时间在姨婆家,另一半就在这个黄阿姨家。我从幼儿园放学回家只要妈妈不在,去的就是黄阿姨家。前面说到的,我妈和同事整夜聊天,基本上都是在黄阿姨家。黄阿姨家也有一儿一女,儿子叫小勇,女儿叫小辉(多么朴素的名字),我们也是从小一块儿长大。后来我妈去西安了,我在重庆,只要放暑假,黄阿姨都到外婆那里把我接到她家住一阵子,每年如此。
黄阿姨话不太多,也做得一手好菜,非常贤惠,在我心目中她就是我姨妈。她老公姓陈,长相酷似朱时茂,也不怎么说话,我一直叫他陈叔叔。陈叔叔是原重庆红岩电视机厂的总工程师,我人生中第一次看电视,就是在他们家。“文革”期间上上下下都在搞运动,陈叔叔却在家里攒零件,省吃俭用,自己组装了一台电视机,九英寸的。在当时电视机是高科技的玩意儿,放电视的时候一个院子里的邻居都聚在一起看,家里坐不下那么多人,就把电视机拿到院子里放,电线得拖得老长。黄阿姨家的院子里还有一棵黄桷树,大人们在院子里站着坐着看电视,我们这些小孩儿就爬到树上看电视。那个时候电视节目一天就播两个小时,就跟看电影一样。
现在我回重庆去,就看望两家人,一个是舅舅,一个就是黄阿姨的儿女。在我看来,黄阿姨家姐弟两个,就跟我的兄弟姐妹一样,是一家人。他们带给了我童年最为快乐和幸福的回忆。
第五章我眼中的重庆
我在重庆生活了十二年,没有生活在那里的人很难真正了解并理解它。这座城市在我看来有着非常特殊的性格,其色彩之鲜明之浓烈,超过其他很多城市,而重庆人的性格也像这座城市一样,格外地鲜明、浓烈。
1、重庆特色
重庆火锅全国闻名,但在前些年重庆市市政府曾经发布的“官方城市名片”中,排第一的不是火锅,而是美女,其次才是火锅。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把美女排第一的道理我懂,可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重庆的水土只养女人?重庆的女孩儿个子都比较高,皮肤也好—皮肤好倒可以理解,可能是在雾都终日不见阳光,有一种病态的白,打扮得也比较洋气。可为什么重庆男人的个子不高,长得也土气呢?在我看来,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漂亮的女孩儿如果性格温柔,在男人看来,这就完美了,但重庆的女人大多都不那么温柔,整体性格都很泼辣。我没有一次上街不碰到重庆女孩儿吵架骂人的。而在我的印象中,一群重庆男人在一起的时候,一个比一个牛,一个比一个能说,但只要有他们的女人在,就会变得都特别。重庆女人在外边基本上都会给足男人面子,随便男人怎么表现,都给他们挣面子,但是回家里以后,大多数都是女人做主。从我的家庭,到我所认识的周围的朋友、邻居家,无一不是这样阴盛阳衰。
这仿佛是重庆社会的缩影。
2、浓烈的感情
重庆人的情感特别浓烈,容易狂热。流行文化总是一阵一阵的,比如当年的呼啦圈、蝙蝠衫什么的,全国都是流行了一阵子就过,唯独在重庆流行得比其他地方都更狂热、更持久。重庆人干什么事儿,都是一窝蜂一窝蜂地去干,这跟受教育程度没什么关系,他们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