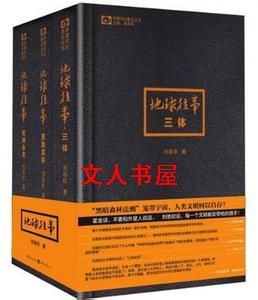��������-��27��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ɶ������
ˮ��ү���ã����û�����ϵ�������
��һ���ˮ��ү��û��ȥ�ɶ���������Ҫ�Һμ��Ϲ���������ģ�ƾʲôҪ���������⣿��������ү������ȥ��Ѿͷʰ���粻��������������ƫ����ڹ������䡣���µ�ת���������Ҹϡ����Ժ��ʱ����Ȼ����ɽ������ӢӢ�ɳ�Ժ�ţ�����̲�ϱ�ȥ��
����Ҫȥ�ģ���ˮ��ү��էէ�ʡ�
һ��紵�������������������ˣ��ٳ�ѾͷӢӢ��û��Ӱ��
3
Ѿͷʰ��ѡ�����ʱ�������������Ǻݺݱ�����һ��ˮ��ү�������ף�����Ȣ���ţ�����ֻ���ǽ���һ�룬��һ�룬�õȻ�������֮���۹ٵ���������ǰ����ʰ���������һӦ�¶������꾡���ţ���������ǰһ��ʱ����ˮ�ұ���رմ�С�����������ţ��ҪϤ����Ȧ��һ��Ҳ���������⣬Ժ���С�����߳�Ժ�Ű벽����Ժͨ����Ժ����ʯ·���ϣ����߲���һ�Ѳݻ𣬻�Ҫ���߸�С���ˣ����߸�С���ˣ��ⱸ�������㣬һ������������������ͬʱ��ȼ���ݻ�ǰ�������˰��أ���ǰ����һˮ�裬�Ȳݻ�ȼ����ͬʱ���������ˮ�裬Ȼ��ͬС����һ���뵽���ָ̲���ĵض���ˮ����С�볯�Ϲ��ɽ��Ȼ���ڵ�ʿ��ָ���½����������뵽���㡣
���Ź鰲�ţ��ܷ�������ȫ����ȫ�����⡣������������IJ���ˮ����Ը��ˮ��ү�������أ����ģ�Ժ��ʱ��Ժ������ˣ��������ˣ������ˣ����飩���ڵ��ϡ����ǣ����ݣ�ˮ��ү����ͷ�����µĹ�أ�Ժ���С���������͵�����磬�����Ŵ��͵ó��ţ�������λҩʦ��Ҳ�ð����ء����ºã��ֵ�����ʱ��һ��Ҳ�������ˡ�
˩��������������ɽ��ȥ���ˡ��ܼ�����ͷ����Ϲ����ɺ�����ȥ���ͺ�����ɩһ���ˡ���ֵ��ǣ����ٳ��Զ��������������ȫû��Ӱ��ˮ��ү������ֱ�У���������ͷ�Ǹ���Ͱ����������ƨ�������Ժ��զ�ͳ����£�
ˮ��ү�˲��ϻ����ѣ������Ϻõ����Ӿ�����Ժȥ���˻�û��Ժ���ͳ������ź𣺡�Ϲ�ӣ�Ϲ�Ӱ����Ҹ���զ���ٵģ���
���˸�ǰ���ŷ���������������Ҳ������ȥ������һ�������Ѿ����ˡ�
��ѽ���������������뿪Ժ��ôһ���̵Ĺ���ˮ�Ҵ�Ժ��û����������
��һ���ˮ�ң��������˻��ҡ���˩���Ӵ�ɽ�ϸ��ػ���������ˮ��ү�ѱ��ű����ĺ�ľϻ�ӣ���������Ժ���������ݺᣬһ���j�̡��ܼ�����ͷ��æ�ҵ��˺�������Ųݻ𣬿�Ҩˮ����ɩ�����ˣ���
ˮ��ү̧��ͷ�����Σ�����һ�������ܼң��Ұ������ʮ�꣡��
��������û��һ���������֮ˮ��ү����ֱ����Զ�Ƿ����������Ļ������ţ����۹ٵ������Ӱ��ٵ��£�һ��Ҳû��������ʱ�֣����˰����Ժ�����ڰ�������������ȫ�����ں�Ժ�����ܼ�����ͷ�Ը����ܼ�����ͷ��ʱҲ�����������⣬�ոհ����궫�������������Ȱ��������������ָ����ˡ������˴���죬������һ���¶�Ҳû������ȥ��
ˮ��ү��ȫ��ɥʧ�����⣬���һ���Ӷ�������������ˣ���һ��ͻȻɥʧ�����⡣���������������ɵ�ӣ��ճյر��ű������۾���ɶҲ������������Ҳ������ʵ�ˡ�
�������ջ��Ǹ��ٳ��Զ���Ŵ����ģ�˭Ҳ�벻������������������dz����ij��Զ����Ȼ�������¶����С����������˽�ˮ��ү̧�����ݣ��������ӣ�����ɩ�����辻ˮ����ˮ��үϴ�ɾ����������ţ�����Ժ����������ļ����﹤����Ժ��ɨ�ɾ�����ʰ�ݵ�ʬ���뵽���£����������������¡���˵ʰ�ݲ�ʮ�壬�Ͼ�����������ˮ�ҵ������̣������������ҡ�ȫԺ���³����ᤣ�Ժ�ſڣ���̲�ϣ�ȼ��ݻ�����ɽ�������ȫ����˱�ɥ����Ժ�������ú��Զ�ֲ���ȥ�������ʿ����Ϊ���˴����������ᣬֻ��һ��ʱ�䣬�빵������ϵ���Ȼ��������Ҳ����ˮ��үԸ��Ը�⣬���ٳ��Զ��������������Ժ���һӦ�¶��������ֵ����ϵ����ˣ�������ʱ�����е��˲ŷ���һ����Ҫ�����⣬һ������Ҫ�������⡣
����ˮ��үƽ���ж�ϸ�ģ���ô��һ�����£�����������ˡ�
��������ˡ�
��˭ȥնѨ��
һԺ������������ǰ�����˭ȥնѨ��
�����Ͽ��նѨһ������·���¡�����˭�������ˣ�ֻҪ���Т�ӣ�ȥ����·�ĸ�ͷ��������ʱ�䣬Ѩ��ʱ��Ȼ�ͺ��ˡ�������Ѩ����·ն�ģ�������ѨҲ����·ն�ġ���ʯ���������ϣ��ݶ���ͱ�����Ѩ��Ҳ������·ն�ġ�������̫�����ˣ���û˭�������ɸ��¶���ֻҪ��·�����ţ���Ͽ�������ˣ����еط��ɣ������Ҫ��ģ�����·��Ѿͷ���ܲ��������������ǰѻ�����Ѿͷͷ����ɣ�
��ͷ�����ͷ�ӣ����£�˭�ܸɵã�
һԺ�����ư��ˣ�˭Ҳû�뵽��ˮ�һ�������ô�����⣬�����⡣
���ٳ��ԶҲ�Ǿó�������û�뵽�����鵽�����һ����ȴ��ס����������Ŀ����һԺ��������ɨ��ɨȥ����ɨ��˭�ϣ�˭�����ͷ������նѨ�����Ǽ����°�������������˭�������õģ�
զ���죿
������ȥ����������ȥ��ˮ��ү����ʱ��ˮ��ү�ոջ���һ��������˵����û���۹ٰ����İ죬�����㣬������������ͷ������������м����Զ�أ���ͻȻ��������ôһ�����⡣
����ȥ����ȥ����·������ѽ����������������˺�
�������߹���˵����ʹ���ã���ү����·��ʰ�ݵĵ���ն���á���
��ն���ã��ԣ��ԣ���ն���ã��ɳ�����·��������˭����
��û�ˣ���û�ˡ���
ˮ��ү����Ҫ�����������ӣ��ۿ���̫��һ�������ȥ�����ϣ��¾���ʱ������Ҫ�Ǽ�ʱ�벻��Ѩ���������¶����ɾ����������ֹ���������ˮ�ң��¾�û�����ӹ��ˡ�
����һԺ���˽����ص����ۣ��ڵ���תĥĥʱ����Ժ��ͻȻ�߳�һ���ˣ����ߣ����ݣ������������ش߷����������ǣ��䣬��һԺ�˵������У��������쳯���������ȥ��
ʰ����
ˮӢӢ��һ���Ƿ蹻�ˣ����ˡ�
Ѿͷʰ����������ˮӢӢ��һ��֪���ģ�����˵��Ѿͷʰ�����һ�������Ǻ�����������ġ�
�Դ�Ѿͷʰ��̧��Ժ�ˮӢӢ����Ͷ�����������
�ⶫ��һ��ʼ�Ǻޣ��Ǽ��ʡ�һ����Ժ�ソ����˵�ӢӢ����Ȼ���֣�������˼ת�Ƶ��˱������ϣ���������ת�Ƶ���Ѿͷʰ�����ϣ����������졣̧��ʰ�ݵ��Ǹ�ҹ����ӢӢ����ӿ��һ��Ī������꣬������������ѣ��ճյض��ں�ҹ����龰�����������������ꡣ�Ǽ��죬���Ǻ��ģ�Ҳ��Ѿͷʰ�ݡ���Щ�����Լ�ӵ�й��ˣ�̰�����ˣ���Ȼ���һ˫���������ﲻ���ܲŹ֡�
�������Ǹо��ͱ��ˣ���ø�ԭ����һ���ˡ�ӢӢ�����Ȼ����ʰ�ݣ�����һ��������ҪС��������ã�һ����С��û����ĺ��ӡ�û��ĺ����ж�࣬ӢӢ�ȱ��������������Сʱ������ԶԶ�ص��������������ȥ����βݵ��龰������̲�ס�����ˡ�ӢӢ�����Ǹ����ij����ˣ��¿�������թթ����������úܣ��ĵ���������������ǿ���ʰ�ݣ�������������ͱ������һ�������������ʡ�����ĥ�ˡ�ҹ���˾���ʱ��ӢӢ��������Ǽ��������ʰ�ݣ�������������Ȣ�������ӡ���ʹ�����������ɵ��Ѿ����ˣ���û�취�ı䣬��������ô�ܶ�ʰ�ݺ�һ�㡣
���������������ݣ�Ϊ��������������Ժ���˵�ǽ��������ʰ�ݸ����������������Ӳ����������֪�����������������ǰ������������Ķ����ˣ����ˡ�ӢӢ���������ƶ����˸е������д����ӣ�ż������Ժ����̸��ʰ�ݣ�����ɵ�ͣ�²��ӣ���������ô���䡣ʰ�����������Խ��Խ�أ�Խ��Խ�з����ˡ���������ϲ���ij���ʰ����Ҳ����ʰ�ݣ����϶��һ�����������Ƕ������飬�ǰ�����һ���������õ��ۡ��ǵģ����ܸо������Ǹ���������������������ι����ʰ�����Ǹ��������ҩʦ��ϲ������ѧ��ҩ����ʵ��ʰ�����������а��ģ�����Ҳ���а��ģ���ҫ������ָ�ŷ���ij�Ҷ������кܴ�ͬ��Ҳ�dz�����㣬����Ҳ���Ⱥ�ʰ���ˣ�������Ϊ������������һ����͵͵Ĩ�����ᣬ����ô�����µ������أ���һ����ʵ���ֵ�����ˣ������ʲôӢ�ۣ���
ӢӢ������ң���������ǰ��û�й��ģ�����������Ȼ�������������ö��������������̣������Ҳ����ô��������ˣ���ϧ����û�����
�����糿��ӢӢ����磬��������ϰ��������Ҳ�������ڿ��ϵ���ͷ�ˣ������ˣ�����ӢӢ�½�����һ�����֣���ǰ�Ӳ����õ��ϣ����������ɿ�����������������������Ե��龰����������Ȼ������һ����ͷ�������ˡ������ͷһ��������Ҳ�ղ���ȥ�����õ���ĥ������������������һ�ϣ�����ҵĵ��Ӿͺ���������Ҫѹ�������ϡ�ˮӢӢ����һ�������찡��ѹ�Ҽ��ϣ����ܵ�����ˮӢӢ֪�����Լ���ѧ����һЩ���ˣ�Ժ��ģ�����ģ���������ģ����ܵȵ���ѹ�����ϣ���˵ʲôҲ���������ǿɲ��������Ը�ˮӢӢԭ����Ҫȥ���ǣ���Щ�������������������������ΪԺ������ʰ�������ҵ�������ǰ��һ���ˣ�������������ɽ�硣����̽��������Ҳ��˳���ʼ���ʰ����Ϊɶ����ҩ��ô���ԣ�����Ժ���˼�����ͻȻͣ�£�������Ժȥ������Ժ��������ԥ�ˣ������õ����֣���������Ѿͷʰ�����ϡ�����ô�ţ���ì����һ�����ϡ����������Զ���˵������ݣ�������һ��������϶�����������Ŵ��ŵ��ӣ�����Ժʰ������ȥ��
������ϣ�ӢӢ��������ģ�����վ��ʰ������ʱ������̲�סģ����˫�ۡ����������

![[HP]�����ִ�һ�����·���](http://www.xibiju.com/cover/3/380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