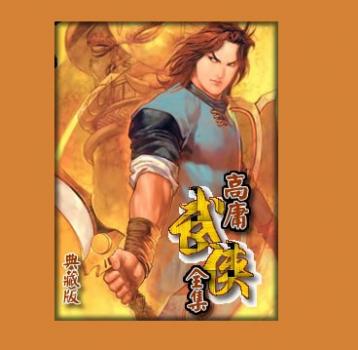大唐探幽录-第23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是终于,头颅停了下来。
本来侧着的脸晃了晃,头颅像是一个调皮的小人般跳起来,然后端端正正,不偏不倚地立定。
在它的双眼中,映出前方的光景,偌大的门府,匾额上写得是烫金的三个大字:梁侯府。
——这当然并非袁恕己所能看见的。
在他的双眼之中,这颗头始终安安静静地就在面前,分毫不曾挪动过。
“到底……是谁杀了你?”袁恕己喃喃。
头颅仍是十分安泰的模样,大概是死了太久了,又或者是因躯体久别重逢,袁恕己总觉着这颗头……比先前才带回大理寺的时候顺眼许多了,甚至……头颅的嘴角隐约微微地上扬。
真是个诡异的错觉。
阿弦醒来之后,还未起身,先沙哑着嗓子呻吟了数声。
她举手抱住头,这颗头疼极了,就好像被人踢来踢去踢了无数脚,又像是在地上滚动了无数圈,脸着地行了很长的路,自觉鼻子眼睛都要移位了。
阿弦举手捏了捏鼻子,又摸了摸脸颊,证明口鼻还在,脸颊也不曾破损,才惊魂未定地松了口气。
虞娘子正在外头做针线,听了动静掀起帘子走了进来,见阿弦正在摸头抚脸,笑道:“怎么了?是不是好洗头了?”
阿弦见她误会了,便道:“不是。”这一会儿,已经想起了梦中所见,蓦地一惊,“梁侯?”
虞娘子道:“说什么?”
阿弦忙问:“姐姐,现在什么时辰了?”
虞娘子道:“已经黄昏了,你可有事?”
阿弦低头穿靴:“我……”她本想说要去找袁恕己,可话还没出口,穿靴的手却停下了。
虞娘子道:“怎么不说了?要怎么样?”
阿弦慢慢皱起眉头。
她虽看见那颗头停在了梁侯府前,但……若把此事告诉了袁恕己,岂不是要他正面跟梁侯武三思对上?梁侯又是武后的人,岂非等同她亲手把个死结递给了袁恕己?
阿弦抬手捂住嘴:“不,我不能……”
其实就在阿弦沉睡的这半天里,长安城里,又有一个消息不胫而走,四处散播。
那就是……名闻天下的“王杨卢骆”之三,卢照邻先生,原来已经身患重疾,所以要离开长安,隐退江湖。
消息一出,从市井百姓到满朝文武,无不惊讶唏嘘!
然而卢照邻之所以染了重病的起因,却是因上一回他做了那不朽名篇《长安古意》之后入狱,在狱中感染了风邪所致!
因卢照邻为人极好,才学又是最佳,那些文人墨客们,无不推崇他,正为诗人患病而怜惜痛心不已,蓦然听说了这消息,又无不切齿痛恨梁侯武三思,虽因为梁侯势大不然明面如何,暗中却人心浮动,骂声如潮。
据说梁侯的车驾从街头而过的时候,被不知从哪里飞出的秽物击中,最后只得慌张而逃。
与此同时,崔府。
“大爷,二爷。”两侧侍女垂首相迎。
崔晔同崔升两人同过廊下,崔升正同他说及今日发现无头尸首、同袁恕己之间对话之事,又道:“这袁少卿看来是个性情中人,几乎就得罪了我部之人,我看在他曾在豳州相助过哥哥的面上,为他周全周全。”
崔晔道:“你既然在场,可看出那尸首有何不妥了么?”
崔升敛了笑,想了会儿道:“我冷眼看着,袁少卿似乎对尸首颈间所沾之物很感兴趣……虽然那东西沾泥带血,可以我看来,有些像是什么东西的种子。”
崔晔“嗯”了声,像是鼓励他说下去。
崔升会意:“若是凶徒挪动尸首的时候沾染,也不足为奇,再说,那地方是乱葬岗,杂物最多,这线索未必管用,除非……”
崔晔道:“除非这是一种难得一见的种子?”
崔升笑道:“哥哥说的正是我想的,这就要考仵作的眼力了,我还是觉着未必能从这上头得到有用线索。”
崔晔问道:“若这种子给你看,你可会查出其来历?”
崔升一怔,崔晔在袖底轻轻地摸了摸,取出两颗乌黑如玉的种子:“如今就考考你的眼力。”
崔升瞠目结舌:“哥哥从哪里得来的?”
崔晔不答,只说道:“这两颗种子,一颗是第一次发现头颅的时候所得,另一颗是这次所得,你瞧瞧是不是同一种?”
崔升接过去,放在眼底仔细看了片刻:“我确信这是同一类花籽。”
崔晔挑眉:“什么花?”
崔升斩钉截铁道:“牡丹花,但至于是何种种类,是否稀有,我却不得而知,我有一位友人最喜牡丹,拿给他看必然知道。”
崔晔道:“既如此,交给你了。”
崔升满面欢喜:“哥哥放心,一定给你查的清楚。”
崔晔淡淡道:“留意小心行事,不可张扬。”
崔升道:“哥哥正好放心,我那朋友是世外之人,他除了爱花诵经,对别的一概不轻淡。”
崔晔沉吟道:“你这位朋友,可是慈恩寺的窥基法师?”
崔升又忍不住笑道:“正是他,上次我去喝茶,他还特问起哥哥来呢。”
崔晔负手望天,忽地轻声叹道:“宁向西天一步死,不愿东土一步生,玄奘大师的高徒,自非常人,改日自当一会。”
崔升点了点头:“窥基是个豁达之人,大概是出家的缘故,每每有令人耳目一新之语,哥哥见见他也是好的。说到出家……哥哥可听说了卢照邻的事?”
崔晔的脸色略淡了下来:“怎么?”
崔升却并未留意,只自顾自叹了声:“真想不到,那样惊才绝艳之人,居然会染那样的重症,我如今还不信呢!”
崔晔不语,崔升继续道:“当初拖赖嫂子的福,我还跟他多见了几面儿,着实是个极好的人……偏偏如此的命运多舛。”
忽然崔晔淡淡道:“你该去了。”
崔升一愣,这才想起自己还拿着牡丹种子,忙道:“我一时想着替卢先生不平,几乎忘了,好,我这就去。”后退行礼,这才急急离去。
崔升去后,崔晔又看了半晌天色,才转身往内宅而去。
正走间,前方有一个侍女从屋内出来,冷不防看见崔晔,忙站住脚,又叫道:“大爷回来了。”
崔晔不禁看她一眼,侍女却忙不迭低下头去。崔晔眉头微蹙,却又并未做声,只仍举步入内。
屋内并无他人,外间空落落地,若非方才那一声“提醒”,必以为此间无人。
崔晔往内,进了里间,果然见烟年坐在梳妆台前,似正梳理打扮,见他进来,便起身行礼,轻声道:“夫君回来了。”
两下照面,崔晔自发现她双眸微红,眼角泪渍仍在。
古井无波的心中忽然起了一丝愠怒的微澜。崔晔道:“夫人哭过?”
烟年仍是微垂着头:“是,抱歉。”
崔晔道:“为何道歉?”
烟年道:“本不该如此悲戚,只是一时未曾忍住。”
“夫人因何悲戚落泪?”
“因为听说故人命途多舛,故而感叹。”
崔晔想笑,却又笑不出:“故人?”
烟年缓缓抬眸:“是,想必夫君也听说了,我……我们卢家,这一辈最出色的卢升之,竟身患不治之症。”
这并不算很长的一句,烟年却说的十分艰难,竭力按捺,却也无法止住嘴角痛楚的轻颤,眼中复泫然欲滴。
崔晔上前一步:“夫人为他觉着痛心?”
烟年道:“想来世上有心有情之人,皆与我一样感同身受。”
崔晔道:“想必我是个无心无情的。”
烟年垂眸,仍是轻声道:“夫君自跟世人不同。”
顷刻,崔晔道:“你是否觉着可惜?”
烟年问道:“我并不懂,可惜什么?”
终于无法按捺,崔晔一字一句道:“借问吹箫向紫烟,曾经学舞度芳年,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
在他面前,烟年面上最后的血色很快褪了个干干净净。
崔晔却仍不愿放过,他冷冷地盯着烟年,道:“好个千古名句,好个愿作鸳鸯,但不知夫人闻听此句,作何感想?”
烟年身形一晃,举手扶着妆台站住,气若游丝般道:“我……又能作何感想?”她摇了摇头:“我并无所想,任凭您处置就是了。”
崔晔右手握紧,忽然一掌拍出,只听“咔嚓”一声,妆台半边竟被劈裂,然而他的手却也因此伤了,血顺着重又攥紧的掌心点点滴落。
烟年原本以为这一掌会落在自己的身上,便本能地闭上双眼,却并未躲闪。谁知竟不曾。
外头侍女因听见动静,进来查看情形,正要上前,崔晔喝道:“滚出去!”
侍女一怔,她从未见过崔晔如此盛怒之状,吓得不敢做声,垂头退出。
崔晔猛地攥住烟年手腕,拽着她往内而去。
烟年起初懵懂,旋即有些明了他想做什么,脚下踉跄,几乎跌倒。
崔晔却并不理会。
他掌心的血压在她的手腕上,隐隐地竟滚烫。
烟年本要抗拒,但看着他微红的双眼,却又死死地咬住嘴唇一声不吭。
崔晔将烟年甩在榻上,他举手去解领口的纽子,一时却解不脱,索性用力一扯,那琉璃纽子跌落地上,兀自沾着血渍。
烟年仍是一动不动,只是轻轻地吁了口气。
就在此刻,外头有个声音,战战兢兢道:“大、大爷……外、外头有人找……”
崔晔冷道:“一概不见。”
那声音壮着胆子道:“是、是阿弦公子,他说有要紧急事……”
崔晔先是一怔,继而听到“要紧急事”四字,冷笑。
之前卢照邻入狱,阿弦便赶来求,后卢照邻患病,阿弦又欲求……这一次时机恰巧,崔晔理所当然也以为是因卢照邻。
当下不怒反笑:“你们都一心为他。”
烟年不懂这是何意。
崔晔望着她惨白的脸色,又看看自己手掌心血渍模糊,终于一笑:“罢了,罢了。我亦‘宁向西天一步死,不愿东土一步生’!”后退一步,拂袖转身。
作者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