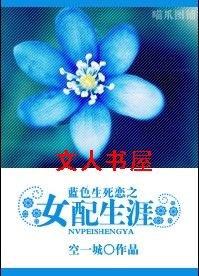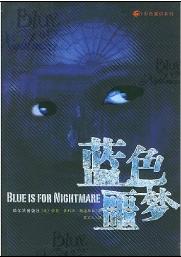蓝色噩梦-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家木门廊的秋千上,我在给她表演小魔术。我洗了一打扑克牌,在手里把它们扇形展开。“挑一张。任何一张。”莫拉咯咯笑着,从中间挑了一张。“现在看着它,记住这张牌,但不要告诉我这是哪一张。”
她点头,笑着,舌尖从上下齿之间伸出来,象是在偷看着粘在嘴边的草莓碎渣。
“现在把它放回去,放在哪都行。”
莫拉把它放在了扇形牌靠左面的一边。我把它混在其他牌里,洗牌。“哦,魔法、魔法、变你的戏法,”我逗着她说,“告诉我哪颗牌该打。”我一张一张地拨牌,脸朝上看着秋千,想猜出哪一张是她的。我停了一下,用手指弹了弹方块Q。我抬头看她,她咯咯地笑了。
“不是。”她说。
我把她被草莓粘污的刘海儿从眼睛上撩开,又轻弹了几张牌,停在红桃A上面。“是这一张吗?”
莫拉开始鼓掌。她把胳膊缠在我的脖子上。她衣服上的苞米花和红色欧亚甘草味儿,让我觉得自己在给她下午点心时太过慷慨了。“你能教我吗?”她问。
“我当然可以教给你。但你得先去洗脸,该吃晚饭了。”
“我能先告诉你一个秘密吗?”
“当然。”
“我真希望你是我的姐姐。”
“我也是。”我说,更紧地搂住她。
我睁开眼睛,看向笛瑞儿。她正在对着镜子梳头,要梳到一百下。所有我能想到的只是,我永远没有机会告诉莫拉,我的戏法是怎么变出来的了。
第八章
“你什么意思呀,你说你撒谎了?”笛瑞儿啪嗒一声把梳子扔在梳妆台上,在坐位上转了半圈,面向我。
“我是说,我没有完全地,诚实地告诉你,你的扑克牌是什么意思。对不起。这太蠢了。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实情。”
“实情是什么?”
“我说的那些,关于查德要约会你,然后又爽约的事,都是真的。而其他——”
电话铃响了,打断了我。笛瑞儿起身去接电话。“喂?”她说。“是的。谢谢回电话。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挂电话说我们破碎的窗户的事儿了。那我们什么时候等着来修玻璃?”
当我听她说到查德的球衣丢了的时候,我转过身,猜她是在和校园警察通电话。我也不能怪她对我发火——换作我,我也会。我仅仅是希望这不要毁掉她对我以后的信任。
我靠着床,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马上想起了,我的衣物,在洗衣房。沾了尿渍的床单。我想回去,但经过了对扑克牌、撒谎的解释,再加上那个愚蠢透顶的曲奇礼物,我的心在这一夜已经折腾地够戗了。我会把闹钟调到明天早上五点,震动档上,藏在枕头底下,然后在还没有人醒来的时候冲到洗衣房去。
笛瑞儿咔哒一声把电话挂断,然后重新拨号。给查德挂,我猜。
不再多想,我得做点儿事了。我起来在壁橱里翻出家传的剪贴簿。又沉又笨,有的地方被撕坏了,纸页已经发黄,在角上还有烧过的痕迹。里面满是各种各样的祖传资料——家庭秘方,魔咒,喜爱的小诗,甚至是秘密配方,比如说我表哥的表哥的表哥的咖啡配方。
奶奶在她临去世前两周把它交给了我,而我每次用它的时候,都会想象,在许多许多年前,系着长围裙的女人,在蜡烛旁做魔法,或是在读不可思议的诗歌。当我问奶奶她怎么得到的,奶奶说是她的婶祖母伊娜给她的,并且让我将来也传给一个人,一个象我一样有天分的人。
我把书翻开到半折的一页,上面写着我曾曾曾祖母伊娜的字迹。这是一个家庭秘方,教人治疗夜盲症的:晚餐吃生的鱼肝。腻人,但恐怕要比餐厅的东西好吃。我又继续翻了几页。今晚,我想做一个关于梦的魔咒,让我的梦境放大,变得完整,不要暗淡消失。
我并不经常使用这本书,尤其是奶奶总是说,依赖于它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魔法和秘方是来自内心的,是我们给了它们意义。而每次我用它的时候,我都喜欢看它上面的写的字——有的地方钢笔尖跳了一下,有的地方滩了一块墨迹;有的人的字总是斜向一边,有的人的笔画却是弯弯曲曲。我甚至根据她们的名字和她们写名字的方法,就能猜到她们的性格人品,猜到她们是干什么的。它总是让我感到自己和家里人的神秘联系,甚至和那些从未谋面的人。
以前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类型的魔咒。既然要救笛瑞儿,我就得有更多的线索。
我点燃了一只柠檬草薰香。然后把要用的工具都摆在床上:一只迷迭香,一个空铅笔盒,一瓶熏衣草油,和一支黄色的蜡笔。铅笔盒是袋状的,里面衬了里子,在上面有拉锁。和我奶奶一样,我总是把可能要用到的魔咒工具放在手头上,即便有些东西我从来就没派上过用场,即便她总是保证说,最根本的魔咒是来自内心的。这不过是我感到和她联系的另外一个途径罢了。
我伸手到抽屉里取一支蜡烛,停在了我昨晚用过的那只兰色蜡烛上。笛瑞儿的名字缩写——烧掉了一半的字母O和E,S——正瞪着眼看我。D。O。E。S代表DreaOliviaEleanorSutton;笛瑞儿·奥利维亚·埃莉诺·萨顿。而自打我认识她,这个缩写就是一个笑柄。男生们开玩笑说,“笛瑞儿做得最好”,“笛瑞儿在任何时做任何事”(does是英文“做”的单数第三人称形式,译者注)一开始我以为她是找着让别人取笑的,因为她几乎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手巾,信纸,羊毛衫,甚至是书包——都标上了的她的名字缩写。后来我意识到,让她改变?我们以为自己是谁呀?!她的桀骜不驯,恰恰是我喜欢她的原因之一。
“狗屎。”她说,把话筒摔掉。“查德没在他的房间。现在我该怎么想?”她凑过来坐在我的床上,看着她经过了“法国式”修剪的、边缘凸凹的脚趾甲。
“扑克牌的事上我撒了谎,对不起。”我说,“只是因为我害怕了。”
“不管怎样吧。我现在心情不好,没心思介意这件事。”她看着我们中间的魔咒工具。
“那你今晚还真得介意,这个魔咒涉及到你。”我掐着陶罐的盖,从薰香的烟中来回穿过了三次。然后我点燃了蜡烛,把它放在床头柜上。紫色和白色相间,是紫色和白色两只蜡烛融在一起以后形成的。
“绝妙!”笛瑞儿说。
“象征意义,”我解释道。“紫色意味着直觉;白色意味着魔力。二者的结合意味着我要把梦里的形象整合起来。你可以从你的日记本里撕一张白纸给我吗?”
“为什么?”
“因为那些纸里保存着你的能量,即便是空白的。这个魔咒是给你做的。”
笛瑞儿伸手在床头柜的抽屉摸日记本,然后从后面撕下一页。“这都是怎么回事呀?”
“我告诉过你,我们需要谈一谈。”
电话铃又响了。笛瑞儿跳过去接电话。“喂?啊,嗨。”她转过身,背对我,低声继续着她的谈话。
我猜她又在和他通话了——那个早上来电话的男人。我本来应该跳起来欢呼的,既然和她讲话的不是查德。可是不是这么回事。我对这个男人一无所知,而且,把自己迷恋的对象当成秘密,似乎也不象笛瑞儿的做派。
她终于挂了机,看上去不太高兴。她自己扑通一下坐到床上,蜷起膝盖,伸手够一只保健型的巧克力。我正准备问问怎么回事,电话铃又响了。这回我接了电话。“喂?”
沉默。
“给我。”笛瑞儿说。
我摇头。“谁呀?”
还是没有声音。我挂机。
“可能是找我的。”笛瑞儿说。
“如果他是想和你讲话,他为什么不吱声呢?这个男的是谁呀?为什么总骚扰我们?”
敲门声。我轻轻地从床上地起来,从门后抓起一只棒球拍,把另一只手放在门的球形把手上。“谁?”我查问。
“这么晚还能有谁?”门外的声音说。
是安珀。我又可以呼吸了。
“你什么毛病呀?”笛瑞儿说。
我开门。
安珀看着我肩上的棒球拍。“到球队去试训吗?我得想想。聚酯球衣和夹板在你身上看起来可真不大好。”
“安珀,你们那最近接过骚扰电话吗?我和笛瑞儿最近接到不少。”
“那不是骚扰电话。”笛瑞儿说。
“可能是PJ吧,”安珀说,“他喜欢骚扰别人。我们约会的时候他总是骚扰我。”她四仰八叉地躺在笛瑞儿的床上,双腿在床下晃当着。“你的床比我的舒服多了。今天晚上换换怎么样?”
“这么说,你从来就没接过什么骚扰电话吗?”我问。
她摇摇头。“你们没有拨*69吗?”
曙光乍现。我抓过电话拨号。“挂不通。”
“猜到了。”安珀说,“PJ在挂电话之前总是先拨*67。书上讲过的老把戏。PJ教过我的。也许真是他。明天早上的法语课上我再问他。你们在做爱情魔咒吗?”
我在垃圾桶里掏来掏去,拽出弄得一团糟的曲奇盒。“你们收到曲奇礼物了吗?”
“这是曲奇吗?”安珀说。
“是个意外。”我说,“它被放在窗台上。”
“真是可爱,”安珀说,“我喜欢神秘的景慕者。给谁的?”
我把曲奇字条从兜里掏出来递给她。
“我猜烹调艺术俱乐部是不希望我参加,”安珀说,“是谁不愿意尝尝这些曲奇?”
“我该给你列个名单出来吗?”笛瑞儿哈欠着。
电话铃又响了。笛瑞儿去抓它,可我比她早到一步。“喂。喂?我知道你在那。”
“给我。”笛瑞儿说。
我摇摇头,继续听着。我能听到电话线的另一端,那个人的呼吸——重浊、平稳的呼吸。接下来,他终于挂断了。
“笛瑞儿,”我挂断电话,命令的口吻说,“这个家伙是谁?”
“我告诉过你,就是和我通过电话的一个人。”
“他的名字?”我问。
“我不知道,”她说,“再说这也不重要。”
“他的名字不重要?”
“名字只是我们给自己挂的标签。”她说,“它们什么意义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