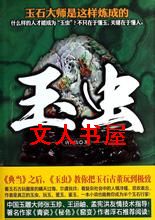未见萤火虫-第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站在一边有点小郁闷,原来弄了这半天我周围全是天才合着就我一笨蛋啊。我烦躁得有点吃不下饭。
我说:“锦春,你在家玩,我去超市买个东西哈。”
凯扬说:“粉红猫,都怪你,罗小末又自卑了。”
“小鸡脚,你为什么说是我啊,又不是我提的勒祈诺”
……
我把他们的话都丢在身后,出了门。
我一个人在街上走了好久,我是要去超市,可是路过之后又走掉了,我审视我自己这么多年的生活,怎么就像一出糟糕的文艺片呢,是胶卷不好还是演员不好我自己都搞不清楚了。这些在我生命中路过的人,原来都这么优秀。
我路过一个很大的广场,坐在那里喝汽水,有小混混过来找我麻烦,我就把残废的右手伸出去吓他,他立刻吓得惊恐的走掉了。我继续坐着喝汽水。觉得生活特没意思。
不是因为锦春,只是感慨。感慨我这个落魄的原富家千斤原来这么差劲。
从广场出来,对面有一条喧哗的满是酒吧的街,很奇怪的,我想起了佐树,好象只有他才能给我憎恨的感觉,那种感觉甚是奇妙,可以持续很长时间,怨恨他打了祈言,让夏朵雪离开,打心眼底的想要消灭他。
我发现怨恨也是一种动力,可以让精神振奋。
我转身要走的时候,有个人东倒西歪的从里面出来,他穿了很厚的黑色毛衣,蓝色的皮裤,一下子就晃倒在我眼前趴在我身上。
没多久,我看到有一帮人冲出来,好象要抓他,他身上很浓重的酒味扑了过来,我想把他甩掉,他像章鱼一样抓住我,我没办法,只好赶紧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盖在他身上,然后把他拉到一旁的广告牌后面把他的头搭在我的肩膀。
那阵势,像两个很亲密的恋人在等车。我把我的外套牢牢的包着他的脑袋,看到一群人凶神恶煞的边跑边说:“他还敢到夏老大的地盘来喝酒,活得不耐烦了。奇怪,人怎么不见了。”
他们说的夏老大不知道是不是夏朵雪的爸爸,这个酒吧街确实是夏朵雪爸爸的地盘。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我赶紧把这个少年的脑袋拨到我眼前看,虽然夜很暗,我还是认得那张嚣张的脸——佐树。
我恼火我自己为什么救了这么一个人渣,我好后悔。我狠狠的打他,他像烂泥一样死死的靠着我,我只好把他拖到广场的某个角落坐下。
“别给我装死,快醒醒。”我推他,用力的推他。
他倒干脆,一把抓紧我的胳膊,死死的睡下去,我用尽我全身力气打他,他都无动于衷。11月的天有些凉,他喃喃的说:“妈妈,我好冷。”
不知怎么的,又觉得他是个很可怜的小孩。虽然他比我大了两岁,可是此时的他,闭着眼,退下所有的戾气和狠毒,真像个18岁需要父母关怀的孩子。
他的脑袋从我的肩膀又滑到我的腿上,他还真会找,把我的腿当枕头呢。
他刚毅的脸在月光下有柔和的线条,我看着他,他握紧我的手,说:“妈妈你别离开我,佐树会听话的。”
他多像妈妈刚离开时候的我,就连做梦,也全是妈妈温柔的笑和动人的声音。
我看到他哭了,他握我的手也很紧,他害怕失去,那一幕我不知在梦里发生过多少次,那种感觉很凄凉很凄凉,让我不忍心把他丢下,我只好拍拍他的头,用妈妈小时候哄我的歌唱给他听,他就不哭了,在我膝盖上很乖的睡着了。
我怀疑我真的成了锦春嘴里的神仙姐姐,可以普渡众生救苦救难,可是,为什么,我唯一救赎不了的,却是我自己。
天空既白,我在一个很宽大的肩膀中醒来,佐树笑着看我,眼中还是那种邪恶的坏蛋一样的光辉。
他问:“昨晚,是怎么回事?”
我从他肩膀里挣脱出来感觉腰酸背痛:“谁知道你喝醉了倒我身上打你骂你也没用。”
他靠近我:“那昨天你有没有对我怎么样?”
我一阵头皮发麻,早知道这种人不好惹,这么可怕的问题都问得出来。
“谁敢对你怎么样啊?黑帮大少爷。”
“那我怎么在你腿上睡了一夜?”
“你以为我爱让你靠啊,我也很累的好不好?”
“你不是很讨厌我么?”
“要不是你昨天喊妈妈,又对我哭个没完,我会这么心软把腿给你做枕头啊?我现在脚还很麻。”
“妈妈?”他嘴里念了一下,脸色立刻变得凶狠:“不可能,我怎么可能提到那个坏女人。你别乱说。”
“不承认拉倒,算我还你上次没砍我手的人情,我们现在两清了,我一夜没回家,我家里人肯定急死了,再见。”
我朝前走了几步,就看到宁诗诗出现,她的假睫毛掉了下来,衣服有些凌乱,妆也不清楚,脸上还有泪痕。
“佐树,你为什么和罗小末在这?”她几乎咆哮着对我们说。
我的头震了一下,随便找了个理由:“我散步,刚巧路过。”
“你的理由真蹩脚。你怎么不说我们俩一起数了一晚上星星不是更有说服力么?”佐树说。
我都来不及反驳,宁诗诗的巴掌就呼的一下砸在我的脸上,包括她细长的指甲,活生生在我脸上拉出五个划痕。
我疼痛的惊呆了,佐树上前,立刻给了宁诗诗一个巴掌:“你又发什么神经病?”
宁诗诗坐在地上哭了,是那种很绝望的哭泣,她边哭边说:“你知不知道昨天我听老西他们说夏老大的手下要去抓你,我就想过去通知你,我到的时候你已经不在了,他们就抓了我,还……还……”她的哭声撕心裂肺的,在这个天微亮的早晨显得那么张牙舞爪的疼。
我捂着被打肿的脸看着佐树的眼睛闪过从未有的神色,我突然明白,我眼前这个女生在昨夜遭遇了一场我们谁也无法承受的恐怖,和我昨天那些自卑,烦躁,焦虑比起来,简直就是炸弹和布枪的鲜明比较。
我突然想起一句话:你看不见我的爱,因为它已经被人很早以前撕碎,所以现在,我无法再呈现给你。
歌词唱:爱你错了吗,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惩罚。
鸟飞过了。痕迹,却一直留着。爱情来了。痛苦,却突然开始了。
未见萤火虫(八) 大小二选一
轰隆隆的天空却没有下雨,我和祈言如往常一样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狭小的空间,我看到他削苹果的认真表情,苹果皮是连贯的,宽度都没有起伏,我笑他越来越像家庭妇男。
笑容卡到一半,脸上的伤疤就疼了。
“让你笑。笑死你活该。”祈言赶紧拿热毛巾给我敷脸。
“回来一礼拜了,请问你可以交代一下那天晚上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吗?”
一个礼拜前的那个早上,我被宁诗诗刮了一巴掌之后我就把很“惨烈”的“现场”还给了当事人之一的佐树。自己朝回家的方向走去。
在半途中遇到找我找得两眼冒凶光的祈言,他想骂我的嘴在看到我脸上的“花猫”抓狠之后就停住了,我假装很痛苦的硬是挤了两滴眼泪说晚上被猫群袭击,奋战一晚天亮才脱身。
可是祈言到底是个智商160的天才啊,他怎么能相信我这么蹩脚的谎话呢。可是他当时没逼问我,他知道用逼问的方式我是绝对不会就范的,他改用怀柔政策,他先给我裹了外套领我回家,喝了豆浆吃了油条。
连续几天,天天和我一起上学放学,晚上还把桌子搬到客厅来和我一起写作业,他站在教室门口等我的样子真让女生流口水,绿色的校服,藤树青,蓝裤子,半边肩膀上挂一个书包,眼神游散的看进进出出的女生。
艺安还是以女多男少的比例在生存,虽说帅哥众多,但也很少见又帅又会学习的。
锦春说:“神仙姐姐,你就老实交代你那天去干什么了吧?要不小优哥哥和你没完啊?”
锦春给祈言取的最新呢称是“小优”,就是质优生的缩写。
我怎么能告诉祈言我那晚让佐树那混蛋在我腿上睡了一晚呢,我怕他会杀了我。我决计是不会冒这样的风险的。
最后我编织了一个谎言,似真似假,我说:“我只不过在公园里坐了一夜,想了一些事。”
祈言半信半疑,也找不出什么特别的古怪,只好放弃用追随左右的方式来逼供。
只是那之后,我好怕路过宁诗诗的教室,更害怕看到她的那张脸,她让我知道了什么叫“美丽姑娘脸蛋变形记”,太惨了,惨到我觉得我的人生还是很幸福的,所以我还是得积极的面对生活。
我在周四上午的体育课上遇到佐树,这不是巧合,是他来找我的,他在我休息的空挡给我拿了一瓶药,他的精神很不好,所有人看到他都避开了,本来我也想假装不认识他,谁知道他很大声的喊我:“罗小末,你过来一下。”
我硬着头皮,在众人同情又怜悯的目光中走了过去。
他给我一瓶药,我险些以为是手榴弹不敢接,他急了,把我手硬拽过去,生生的把药放在我手里,很凶的对我说:“一天两次,外敷,听到没有。”
我狠狠的点头。知道了。
然后他的脸又软下来,细声的问:“脸还疼不疼?”
我这一惊一吓的,把头摇得像拨浪鼓。
他用手拨了拨他额前掉下来的棕红色头发说:“那就好,别留下疤,不漂亮的。”
我看到他手上的粗链子,金银相间,感觉很奇怪的造型。
等他走远了我才想起来,那个链子的银色部分明明他从我手上取走的那条,他只不过把两条链子用细银勾缠绕着串了起来。
可是,那明明是我妈妈送给我的手链,他凭什么接到自己的手链上去啊。我非常抑郁的和锦春说。
锦春当时正在房间里随音乐乱跳一通,没听到我说的具体内容,我看看锦春跳舞的小模样,还真的不错。
我突然想到我们“琉璃赛”上要表演什么了。
我说:“锦春,要不你就来个跳舞画画,你边跳边画,你看这样好不好?”
锦春问:“那你干什么?”
我眨眼:“我做指挥,顺便写诗。”
展凯扬问:“你不是打算让锦春又跳又画最后就去题个五言诗就了吧?”
我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