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没有女性-第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五岁那会儿根本不懂诗歌,可是达莎姑姑非要教我祈祷不可。我就成天为爸爸妈妈祷告,保佑他们活下来。这种。生怕失去妈妈的恐惧心理,我保留至今。我现在每天早晨都要给妈妈挂电话,我必须跟她说上两句话:‘你感觉怎么样?好吗?’‘嗯,很好……’我这才把电话听筒搁下,开始自己的一天。”
“天天如此吗?”
“要是我没打电话,或者妈妈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会一整天心神不定,慌得两只手都不知放在哪儿才好。晚上睡觉之前,我还要打电话给她。虽然我现在已经四十多岁了,我仍然每天要亲耳听听妈妈的声音,哪怕是一两句话。”
“您常常到妈妈那儿去吗?”
“每天都去,如果我不在医院值班的话。我是儿科精神病医生。跟妈妈一样,我当上了大夫。我丈夫无法理解我为什么总是慌里慌张,早先他还委屈过、嫉妒过,现在他认可了。他看到,这并不是什么怪癖,而是我不得不如此。
“我从小就渴望当医生,但我不能当外科医生。我例不怕见血,而是怕给活人动刀。因为那总使我联想到我在战争期见的所见所闻:那些伤口,还有被狼狗活活撕碎了的人……我们在大学里上实习课,这对我实在是极大的困难……”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三日,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卡希契金娜被装进女囚专列运往英吉利海峡边上的克罗泽集中营为法西斯干苦役。三月十八日,巴黎公社纪念日那天,法国人组织了越狱。她逃了出去,参加了“马基”(二次大战时法国抵抗运动游击队.——译者注)。
“那些日子留给我的纪念,是受伤的脊椎和一枚法国‘战斗十字勋章’。我经历的事情太多了,以致于战后什么都不愿意去回忆。所以有很多细节忘记了。几十年来,我反复强迫自己:‘忘掉它忘掉它’“只有一件事我不愿忘掉,那就是从法国回来,踏上祖国土地上的第一站……我们当时全都跳出了车厢,吻着土地,把泥土捧在怀里……”
过了几天,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突然打电话给我:
“我刚刚回到家里。我找到那个地方去了……什么地方?就是当年党卫军集中营所在地。这么多年,我连往那个方向看—看都害怕,如果偶尔必须到那片地区去,我就远远地绕着走……自从我们上次交谈以后——当时您问,现在那个地方究竟怎样了,我也暗暗想:‘那儿现在是什么样了?’我在那里就象喝醉了酒似地,游荡徘徊。一切的一切都想起来了:哪儿是过去的板棚,哪儿是过去的澡堂,哪儿是吊死人的绞架……如果您愿意,我可以和您一起再去一趟。那儿离地区中心不远,乘有轨或无轨电车都可以到……”
于是,我们一块儿来到了当年的希洛卡雅大街。我看到了许多新建的公寓楼房,还有某设计院的长方形小楼房,一切都显得很平常,很普通,练毫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站在这里却流出了眼泪:
“这儿的一切都是在白骨上建起来的呵,就在这下面躺着成千上万的人,我连他们的模样都记得……”
后来我又得知,当年这座集中营的囚徒们曾经找到明斯克执委会,请求把集中营原址列为永久性纪念地,要竖纪念碑。要是在我们过去呆过的地方没有纪念物,谁能在这种土地上健康成长?我们应该记住这一切。
“在明斯克还应当为无名的地下工作者竖立纪念碑,因为地下工作者大都是隐姓埋名的。不能因为他们死时没留姓名而被我们遗忘。”
只要这位受到战争伤害的妇女还健在,她的回忆便是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桥梁。但她还想知道,明天将会怎么样。
在另一位明斯克女地下工作者的心中,保留着她对战争的一笔细帐。她叫娜杰日达·维肯吉耶夫娜·哈特琴科。她对我讲:
“我带着儿子在街上走,到处躺着死人一一躺在马路这边和那边。我在给儿子讲童话小红帽的故事,而周围全是死人。当时我们离开了难民群,到我母亲那儿去。我拿儿子没办法:他老是爬到床底下去,在那儿一坐就是好几天。他那年五岁,又不能放他到街上去……
“我跟他在一块儿吃了一年多苦头。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他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住在地下室里,有时候能看到街上走过的大皮靴。有一次他不知为什么从床底下爬出来。但一看到窗外有一双大皮靴,就突然尖叫起来……后来我才明白,法西斯曾用皮靴踢过他……
“不过,这些现象在他身上很快消失了。有一次他在院子里和孩子们玩,晚上回到家里,他突然抬头问我,“‘妈妈,爸爸——是什么?’
“我给他解释:
“‘爸爸是面孔白白的美男子,在军队里打仗。’“明斯克解放那天,坦克最先浩浩荡荡开进城来。我儿子哭着跑回家来:
“‘没有我爸爸那些人全是黑面孔,没有白面孔……’“那正是七月份,坦克手们全是年轻小伙子,面孔晒得黑黝黝的。
“我丈夫从战场上回来时已成了残废,而且不再是一个年轻人,变成了老头。我真是有苦说不出:儿子已经认定,父亲是白面孔,美男子,可是回来的却是个老头,一个病人。儿子好长时间不承认他是父亲。我只好想法让他们父子俩彼此亲近起来。
“丈夫下班回家经常很晚,我就问他:
“‘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季玛急坏了:我的好爸爸到哪儿去了?’“他打了六年仗(还参加过对日战争),是跟儿子生疏了。
“每次我给儿子买了东西,总要对他说:‘这是爸爸给你买的,他惦记着你……’“后来他们有交情了。当父亲的有很多故事要讲给儿子听……”
把父亲还给儿子,再把儿子还给父亲——为能做到这一点,一个女人耗费了多少精力心血啊她首先要考虑怎 样安排战后的生活,管好家,促使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忘记战争。她自己先得做到这一点,以女人的基本天性来说,她是创建和缔造生活的。
“我看到了那么多死人,所以我在前线时就想:倘若我活下去,我一定要找个好人,生好多好多孩子。”——索菲亚·伊万诺夫娜·舍列维拉(近卫军下士,报务员)说。
玛利亚·亚历山德洛夫娜·阿列斯托娃,是我国第一位火车女司机,一位风靡一时的女性。她说:
“我从一九二九年起就当火车副司机。当时在苏联各地没有一个女司机。机务段领导很不理解:‘一个姑娘家, 一定要干男人的活儿,图什么呀?’而我就想当火车司机,一心一意想当火车司机。
“三一年,我成了咱们国家第一个女司机,那时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写了好多文章,号召男女平等,要妇女掌握男子的职业。当我开火车时,每到一个车站,许多人就围上来:‘姑娘家开火车了。’“……我们那辆火车头时常放气,就是说要检修。后来我和丈夫轮流开车,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个孩子。我们做了这样的安排,如果他出车,我就带孩子,要是我出车,他就得呆在家里。这一天,正好丈夫回家来,该我去出车。早晨我醒来,听到大街上有些反常,人声鼎沸。我打开收音机一听:‘战争爆发了’我赶忙叫醒丈夫:
“‘廖尼亚,快起来战争……快起来,战争’“他跑到机务段去,回来时泪流满面:
“‘战争战争你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吗?’“怎么办?把孩子送到哪儿去呢?
“我和孩子撤到了后方,撤到了乌里扬诺夫斯克。我们分到两间一套的住房。房子很好,到今天我都没有那样的住宅。儿子也上了幼儿园。—切安适,人们对我都非常好。还用说吗,我是女火车司机,又是全国第一个……可是我在那儿没住多久。不到半年我就住不下去了:这怎么行,人人都在保卫祖国,而我却蹲在家里!
“我丈夫回家来,问我:
“‘怎么,玛露霞,你还打算呆在后方吗?’
“‘不,’我说,‘我们一起走吧。’
“当时,上面组织了一支为前线服务的特别预备纵队。我和丈夫都申请加入了这支队伍。丈夫是司机,我也是司机。一连四年,我们都住在闷罐子车里,儿子也和我们在一起。他在我身边度过了整个战争,甚至连猫也没见过。有一次他在基辅弄到一只小猫,我们的机车正好遭到猛烈轰炸。五架飞机向我们袭击,可是他却还抱着那只小猫:‘基萨尼卡,小乖乖,我看到你真高兴,我在这里谁都看不到。好吧,和我坐在一起吧,让我亲亲你。’真是个孩子,只有孩子才这么天真……
“我把多少列火车开上了前线?您可以算算:火车头一昼夜就能开个来回,每年平均出三百六十五趟车,那么四年是多少?您算算吧——近一千五百列火车哪。斯沃博达上校(卢德维克·斯沃博达(1895—1979)捷克斯洛伐克著名领导人,曾任共和国总统兼武装力量最高统帅(1968—1975)。——译者注)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就是我和丈夫送上前线的。我们常常遭到轰炸和机枪扫射,敌人专打机车头,他们的首要目的,是打死司机,毁掉机车头。飞机进行低空俯冲,向机车和闷罐子车厢扫射,而我的儿子就呆在车厢里。每次敌机轰炸扫射,我最担心的就是儿子。没法子,我只好把他从车厢转到机车里,放在身边。我紧紧抱着他,贴在心口:‘让同一块弹片把我们娘儿俩都打死好了。’难道想死就死得了吗?您瞧,我们偏偏活下来了……
“儿子现在是医生,而且是主任医生。我为他吃了好多苦。我们从前线回来时,他已十岁了,可只能进一年级。我还担心他精神会不正常,因为我们多次受到可怕的轰炸。他后来长成了一个漂亮的小伙子,现在我已经有了儿媳,三个孙子。
“火车头,是我的生命,我的青春,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所在。我现在还想开火车呢,可是人们不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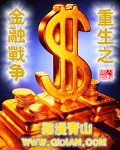
![[兄弟战争]喃喃爱语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0/491.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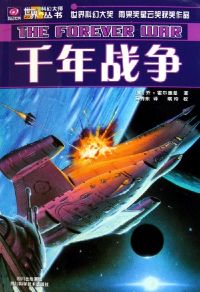
![[战争与和平]穿越成为公爵小姐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3/303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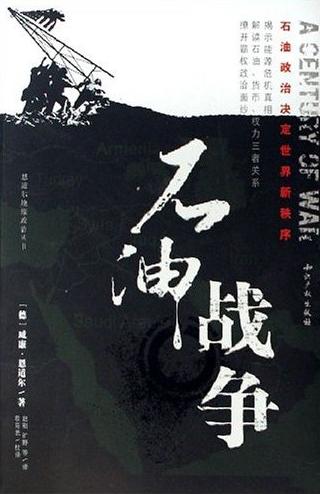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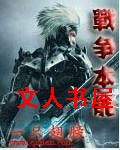
![[兄弟战争]我愚蠢的弟弟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5/584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