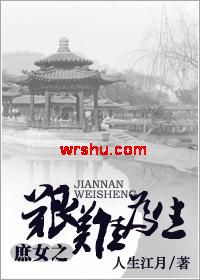红蛇女之怨-蛇怨-第7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次排戏,学堂还在镇上最好的裁缝店里订做了服装。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演出的一切开销,王兴国说全是镇上来。南校长、周教导和许多先生几乎天天下午来看他们排练节目,女施先生也常在前排就座,虽然她没有恢复汝月芬可以去她宿舍和办公室抱作业簿的资格,但也再没有对汝月芬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而对阿德则完全恢复如初,一如从前,不论在哪看到他,她都会老早抬着手,然后在他的头上背上轻轻地拍这么一两下。她对他和汝月芬出演节目一事,说的一句话是:“不要为此尾巴翘到天上去。”
他和汝月芬有一出联手戏,演一个独幕剧,是《猫和狼》。阿德扮狼,汝月芬是猫。戏讲的是一只狼被猎人紧紧追杀,命在旦夕。狼在逃命时撞入一个村庄,遇见蹲在房头的猫,苦苦相求,搭救它的性命。
“我是一匹好狼,我赶走过欺侮残杀过这个村子里所有动物的其他恶狼,为你们守护畜群和财产!”阿德摇摆着脑袋,心神荡漾地对汝月芬说。
“那你快去小羊家吧,小羊或许能救你一命!”汝月芬在硬纸板面具后,笑逐颜开地对阿德说。
“哦,不行呵,去年秋天我咬伤过小羊的妈妈。”阿德沉吟一晌,甜甜地说。
“那实在不行,你就去鸡大婶那儿,问她能不能帮你!”汝月芬翘起兰花指朝台后指指。
“啊哟哟,可不敢,可不敢。今年春天,狐狸兄弟把她的鸡娃儿连锅端的时候,我只装没有看见,她恨着我呢!”阿德可怜兮兮地低下头来。
“要不,你再去老牛伯伯家看看?”静场片刻,汝月芬不耐烦地说。
“天哪,也不行,去年冬天,我吃掉了老牛伯伯最小的儿子,它正愁着没有机会找我报仇哩!”阿德惊慌失措地在台上跳起来说。
“那就再没有人可以帮你了,你这头十恶不赦的恶狼!当你赶走其他狼的时候,你说你会给我们带来福音,你会守护我们的生命财产。但是,待你坐到他们的位置上后,你同他们毫无区别,甚至更坏!当危险来临时,你再也不要指望我们会帮你!我们只会诅咒你:快点,快点去死吧!”汝月芬声色俱厉地谴责道,然后扭扭腰,快步走到幕后。
这是他们五年级国文课本上的一篇寓言,男施先生改编的。学堂要出的这台节目,南校长就交给了男施先生和万先生。他们一排练,男施先生就在台下怒气冲冲地看着他们。
阿德觉得男施先生自打在街上与那个张阿二和阮老三发生冲突过后,变得很易怒,讲课时与课文内容搭界不搭界,他都会扯到时局上来。男施先生说,当下中国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什么诸侯政治,藩镇割据,政府官员上行下效,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国家,国家是如此,唯实力是论,民间,民间亦如此,唯实力是论,好勇斗狠者,恃强凌弱,或欺行霸市或横行乡里;盗匪四起,民怨但却又无所作为,明哲保身,得过且过。还有什么精神沦丧道德垮坝,诸如此类的,弄得阿德他们常常云里雾里的。
但有的时候,坐在台下的男施先生也不发火,只是闭着眼睛,口中念念有词。阿德一见他这样就害怕,这就意味着他在琢磨着要改台词。台词老变,搞得阿德很辛苦。
昨天下午,万先生在台上对在台下的男施先生突然提出来,汝月芬最后结尾的那段台词有点冲,不要让人家说是指桑骂槐。阿德看到男施先生一下子又激动了,他唾沫星子四飞地对万先生说,当基督教未成为西方国教前,许多基督信徒被投入斗兽场喂狮子老虎,或者被活生生地钉上十字架……成千上万的信徒惨遭杀害。但是基督教形成燎原之势,他们立即成立宗教裁判所,迫害绞杀成千上万的异教徒,有的还被扔进火里活活烧死。男施先生还说,许多国家的统治者也是如此,当他们取得国家权力前也被追捕加害,或投入牢狱,或砍头枪杀……但他们一旦摇身一变,君临天下时,也党同伐异,滥捕滥杀,如出一辙。这就是历史,一部血迹斑斑的人类苦难史。他对万先生说他一定要以自己的方式说话,他定下的一个字也不能动,要不他就撂挑子不干了,至于谁要自作多情就让他自作多情好了。
阿德听了男施先生这话,一直有点提心吊胆的,生怕男施先生真的不干了,这台节目中他只有这么一个角色。
不知道男施先生后来又同万先生说了点什么,说得万先生心里像是热乎乎的。于是,阿德他们排练的时间也就更长了,常常弄到天快黑时才回家。可怜的是哈松,他一直干坐在一边。他在《猫和狼》中没有一句台词,他演猎人。待到全剧终了前,汝月芬走人,阿德焦躁地原地徘徊,他拎把木头长枪,跑到台上准准地瞄着阿德。一个男生在后台像拍惊堂木似地用木块在地板上猛拍一记,算作枪响。阿德倒下,哈松捉住他的衣领,豪气冲天,举枪亮相,阿德作死狗状,然后大幕落下。
起先,阿德老大不愿意哈松演这么个角色,死在谁那儿都行,就是不能死在哈松手里。他告诉万先生他和哈松有仇。万先生说,哈松五大三粗,学堂里没有一个比哈松更像一个猎人了。他阿德是这出戏的主角,连汝月芬都是配角,而哈松则干脆就是个跑龙套的,连一句台词都没捞着。万先生劝阿德算了,哈松演得也很认真,傻乎乎地拎把木头长枪,一趟趟跑到台上。不过,哈松这阵子一点也不嚣张,时不时讨好兮兮地看一眼阿德。特别是阿德看到哈松在幕后用木头长枪瞄准台下的女施先生、周教导和镇上的王兴国,他们相视一笑,阿德心中的怨结松动了不少。想想也是,阿德几年前在湖边的时候就看出哈松很喜欢汝月芬,他们当时又算邻舍又是同学。阿德决意宽恕这个几次欲与之殊死一斗的哈松,换作他是哈松又会怎样呢?宽恕他人与被他人宽恕,都是一件令人生出躲过一劫的感觉的快事,因而阿德感到从未有过的一种舒坦。
一大早,一个挑水的后生站在像糖葫芦似地几乎串在一起的三潭边上,看见波光粼粼水潭深处,似有一团若隐若现的红晕,随水沙向黑黝黝的潭石后边荡去。但一会儿,潭水便又显出水天一色的清冷。他正心生惊异时,只见几条巴掌大的死鱼从水面飘飘而来,不由得一阵狂喜。
他赶忙用扁担将几条死鱼捞过来,折草一串。鱼新新鲜鲜的,拎在手里沉甸甸的,他心花怒放地笑了。一小点细皮碎肉飘浮过来,他用水舀子赶开,然后才将潭水舀进水桶里。水里哪怕有一点点异物,挑回去,没人会付钱给你。被骂个狗血淋头事小,这样传开去,没人再要你送水了。
那后生将鱼挂在桶边,喜滋滋地上路了,他也记不得自己已有多久没吃鱼了。
他挑着水担边走边用坎肩扇扇热气腾腾的胸腹,草鞋在脚底下的沙砾地上发出欢快的呱唧呱唧的声响。桶中水漾出一圈固定的水纹,一波一波向桶中央轻聚轻散,没有一点水花溅出桶外。挑完这担水,他就歇下,回茅屋烧早饭。他们几个挑水的都来自皖南,租住一处,轮流买菜烧饭。
“喔哟,还弄了几条鱼呵,福气,真福气!”有两个伙伴大声地向他打个招呼,挑着空桶吱嘎吱嘎经他面前向三潭走去。镇上很多没有壮劳力人家的吃水几乎都由他们几个包了,不论河水还是潭水。
那后生这两日,一天到晚都喜气洋洋的。他已攒足了盘缠,打算明天动身。两年没见到老母妻子和儿子了。出来时,只要说声“虫虫虫,飞飞飞!”,他的小石头双手食指拇指就会一触即分,然后龇出满嘴的牙花子咯咯地笑个不停。
他有些口渴了,于是慢慢地歇下担桶,取下系在水桶柄上的水舀子,舀一勺水咕咚咕咚地灌进喉咙。清冽的潭水使他浑身一爽,他解下扁担上的毛巾擦一把,嘿的一声又挑起水桶,健步如飞地走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
一只小鸟神神秘秘地在一丛丛灌木上空飞来飞去,趁人不备立即落入巢窠。
那后生劲劲地走着,可他觉得怎么这担桶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他好不奇怪。每天从日出到日落,他连歇歇脚都是少有的事。忽然,他的腹中一阵绞痛,便步履踉跄地停下来。一股寒流活物似地在腹中四处游走,他弯下腰,想待这股寒流自行散去。寒流在他的小腹前鼓起一个大包,又下行直奔肛口。他即刻放松肛肌,想排出这股令他极为痛苦的寒气。一股黑色黏液,汤汤水水地顺着他半裸的大腿淌了下来。
叉开两腿站在那儿的后生,身子如弓,一口黑水便呈锥形喷涌而出。随即,他砰的一声,连人带桶地滚翻在地。
两个刚过去的水夫,嗨哟嗨哟地挑着担桶大步走来。
“哎……”他们咣啷一声扔下水桶奔过来,推一身泥水的后生。
“啊,死人啦!”一个水夫原地弹起来惊叫。
两个水夫在高低不平的河谷上着魔似地狂奔。
在人来人往的一条石板街上,一个左眼被一块紫红色胎记覆盖的壮汉,在人丛中横冲直撞,招来了许多的白眼和抱怨,但那壮汉毫不理会,只管向前闯去。他奔到一扇包着黑铁皮的窄小的屋门前,一推,不开,便抡起如钵大的拳头,猛擂起来,将门板敲出一片破碎声。
“来了,来了,火烧呵,恁急!”王阿婆放下碗筷,颤颤巍巍地颠着小脚奔过来开门。
“快点,快,要养了。前一阵吃了炖蛇汤一直有点作痛,现在痛煞,吃不消了!”那壮汉冲王阿婆大喊。
“瞎讲,你媳妇少说还得有两三个月才养儿子哩!大清老早把门敲成这样,做啥呢!”王阿婆一看来人,呵斥道。转而又问:“啥吃蛇汤!你夜里又弄过她了不是?弄出个小产来吗,要命了!”
“啥也别说,快点跟我去!”壮汉拖过王阿婆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