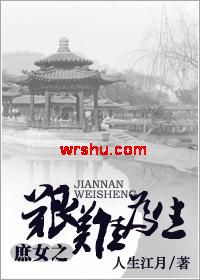红蛇女之怨-蛇怨-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女儿的眼睛满是骇然,小脸通红通红的,一头汗,连头发都是湿的。
“一只手,潭子河里伸出只手……”女儿一头扑进郝妹怀里,大着舌头说。
“做个梦!”郝妹拍拍女儿的背心,对踢踢踏踏走过来的男人说。
天大亮了,郝妹才起床,女儿昨儿夜里,哼唧了半天,才重新睡着,她等到女儿睡踏实了,才回到男人身边躺下。
男人早就到山塘街开店门去了。郝妹又去女儿的房里瞅瞅,见女儿睡得好好的,才下楼揩把脸,弄杯水漱漱口,然后去换掉拖鞋,准备出门。她最看不上那些拖着拖鞋上街的人了,那些拖着拖鞋满世界乱窜的人,一看就是才将两腿泥洗净不久的乡瓜,虽则他们的穿着长相与镇上的人没多大区别。
郝妹虚掩上大门,站在大门的踏步上,朝蒲包老太家门喊了一嗓子,让她去照看一下她家小芬。每次出门,只要把女儿单独留在家里,她都这样。郝妹在蒲包老太一连串殷勤的应诺声中,提个小菜篮,走出蚌壳弄,直奔大桥头去了。
桐镇的清晨,除了设早市的舭定街大桥头,大约就算沿这街这桥的这条河忙碌了,载着瓜果、蔬菜、鱼虾的小船来往如梭,显得特别闹热,有些菜船就将缆绳系在驳岸肚裆处的铁环上,有的则直接将缆绳挽个扣,套在驳岸的拴马桩上,在河里与驳岸上的主妇交易。
平日里,买小菜是郝妹最惬意的时刻,她把这个看作是一个镇上人的标志之一。但今儿,她觉得胸口有点堵,仔细想想,这与女儿那个黑龙潭的梦有关。怎么会呢,一个人怎么可以梦见一个她从未去过的地方呢?!
周围有点乱哄哄的。在路上,买菜的男人女人绷紧着面孔短促地交谈两句,便匆匆忙忙地向通太桥那儿走去。郝妹拦下一张熟面孔,问道:“说啥呢,出啥事了?”
那张熟面孔两片薄嘴唇皮上下翻飞道:“喏,潭子河里死个人,也不知是男是女,哪儿的人,大清老早就被下河桥口淘米的张老太发现,她一见河里伸出只手……”
郝妹直觉头皮一麻,脑袋里轰的一声,什么都听不见了。
那张熟面孔走出去很远,还回头不住地向立在原地呆若木鸡的郝妹张望。
桐镇的镇北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湖,叫蠡湖,相传吴越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在此隐居过很多很多年。蠡湖是个荒湖,湖岸上只有一间孤零零的颓败的茅草棚,只有采菱摘莲蓬头的季节,才有些人气儿。但湖滩四周不时地可以看到零零碎碎地堆着一些碎砖破瓦。
阿德凹肚挺胸,脖子上戴着那枚黑白麒麟玉佩,迈着自以为非常得体的步子,向一堆碎砖破瓦走去。那玉佩随着他的脚步,轻轻地叩击着他的胸骨,似乎告诉他,他戴着那玉佩呢。这玉佩是娘在他很小很小的时候,从走门串户收玉又卖玉的王瞎子那儿买的。王瞎子不是两眼全瞎,是独眼龙,做玉生意有好多好多年了。这枚黑白麒麟玉佩买下后,一直戴在阿德脖子上,除了汰浴,几乎从不离身。因为戴的时间长了,阿德有时会忘了自己戴玉佩的事。
阿德大头瘦身,圆脸圆眼,眼中什么时候都透出一股子疑惑。他不停地扬起两条有些高低的眉毛,疑疑惑惑地看一眼隔湖那间从来没有看见有人住过的茅草棚,他心想,要是夏天,他肯在那儿过夜的。他打算呆一会儿领他的小哥们到那儿转转。
阿德弯腰开始在那堆碎砖破瓦里选削水片的瓦片时,又偷偷摸摸地向那个红衣女孩瞅了一眼。她是蚌壳弄的,但她远离着蚌壳弄的人,和另一个女孩站在一边。
红衣女孩若有所思地凝视着湖面,时断时续地将手中各色野花抛入湖中。另一个女孩,用青竹条捞着湖中的水草。那些被她捞起来的好似龙须菊的水草吸附着零零星星的白壳小螺蛳,乱乱地堆成小堆,水草草叶迅速脱水,皱缩着很难看地堆在河滩上。
阿德认识这个文静似水的红衣女孩。他和她家虽则隔开好几条街弄,可偶尔也会打个照面,不过却从未说过一句话。每次都是她走出很远,他才折身赶过去几步,细细地看那个红晃晃的背影消失。
镇上的小孩结帮大都以住地划块,有时互不相识的两帮,为点屁事火拼前,报上名头时,全是我是什么街或者什么弄的谁谁谁。这蚌壳弄的同他们藕河街的刚才相互一通报,便一声不吭地开始削水片比赛。这种较劲全是秘而不宣的,有关这一点,阿德是清清楚楚的。阿德还清楚那个长得又壮又黑的男孩,是蚌壳弄的头儿。不用搭脉,一望便知。
哈松在蚌壳弄的那拨人一片唧唧喳喳声中,奋力将一块瓦片削了出去;瓦片在水面上嗖嗖嗖地带出一圈又一圈水花。
“五个!”蚌壳弄的人齐声喊道。
阿德选出了两片特别上手的瓦片,二话没有,歪头展臂,一抖腕。只见那瓦片劈劈劈激起一连串大大小小数不过来的水花,然后前摇后晃,稍息片刻,悠悠沉入水中。
哈松在藕河街的人的欢呼声中,向阿德翻了一次白眼,又翻了一次白眼。但阿德完全无所谓,让人没劲的是削完水片,他向那个红衣女孩丢了一眼,发现她看都没有向这儿看过。
蚌壳弄的那个叫泉福的胖墩,立即挺身而出,削出一片。
“一、二、三,触!”蚌壳弄的人很是泄气。
长得尖嘴猴腮的阿钟挺起他高高的鸡胸,咬牙切齿,喷出一口大气,也削出一片。
“一、二、三、四、五、六——”藕河街的人像唱票似地唱道。
“触!”哈松低声骂道。
比赛结果,藕河街遥遥领先。他们的瓦片,削得比蚌壳弄的圈多不说,还比他们远,而且还密。这自然惹得蚌壳弄的人很是不满。
削水片比赛,不欢而散。他们自动分成两拨,分别朝不同的方向走去。
阿钟远离众人,在湖滩上溜达着。他突然沙哑着嗓子叫了起来:“金山,快点来呢,一条死蛇哎!”
阿钟是藕河街有名的贼眼,没有他发现不了的物事。
那个叫金山的同样也长得瘦骨嶙峋的,他爹开了一爿米行,不像阿钟家顿顿素小菜,但用金山娘的话说,肉呀鱼呀尽多尽少都倒得进去的,但他就是只长骨头不长肉。
一听阿钟喊,金山撩起汗褂擦着脸上的汗,露着半扇琵琶肋骨,颠颠地奔过来了。
隔开一段距离的两拨人,蜂拥而至,又迅速汇成一股。
死蛇,如一大捆草绳,隐在一片浆板草下。乌青色的蛇身粗如锹把,散散乱乱,七扭八歪,与水草融为一色。但有蜂窝状图案的蛇腹,却是一片乳黄色,新新鲜鲜,煞是抢眼。
“泉……”蚌壳弄的哈松推推一边的泉福,但突然掩口噤声。
“到你屋里去困觉,你……你想害人呵!”金山忽然醒悟过来了,哭声哭腔地向发现死蛇的阿钟扑去。
“不是有意的呀,又不是有意的!”自知闯祸的阿钟双手护头,任凭金山劈头盖脸打上来。
“没完了吗?”阿德见金山又下脚踢人,上前拖开阿钟不满地说。
“今夜里,要有一点点事,就找他算账!”红衣女孩身边的小姑娘为金山抱不平。
大家都知道,看见蛇,尤其是死蛇,不能说人名,否则必有祸事上身。夜里,死蛇找上门来的事,又不是没听说过。阿钟号哭着离群而去。一个小小孩独自一人翘着屁股,在乱砖堆里翻寻什么。哭着跑过来的阿钟飞起一脚将他踹翻在地。小小孩一个狗吃屎,一脸泥爬起来,扎着两只脏手,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一路“姆妈来呀,姆妈来呀”,跟在同样哭天抹泪的阿钟后面离开湖岸。
死蛇随着水草起伏不定。
阿德见独自站在一边的红衣女孩眼神忧郁,脸色发白,他心里很不好受。
“叫绰号行不?”有人问。
“那也不行!”哈松权威地说。
“白皮头,这蛇咋死的?”泉福不无得意地问哈松。
“矮佬佬,你说说看!”哈松也很得意地向一个矮小的男孩投去一眼,嗓门高高地说。
夕阳,铜锣似的,又大又圆,彤红彤红落在湖对岸。红衣女孩一声不出,兀自面湖而立。
晚霞打在红衣女孩的前胸后背,她全身笼罩在一片炫目的红光之中。
阿德听着他们怪腔怪调地胡乱称呼,觉得真他妈的滑稽,也很恶心。又不是你们弄杀的,怕个屁!
“我叫卞德青,住藕河街四十七号!”阿德脑子一热就这么说了。
“你傻了哇,你傻了哇!”住阿德对门的玲玲凶悍地摇着他的臂膀。
霎时,藕河街、蚌壳弄的人,眼里满是哀怜地看着阿德。在死蛇跟前说出人名,本来就是一劫,那死蛇会在月黑风高中喊着听来的人名,四处游走,满世界找人,但若是无人应答,死蛇只是无的放矢,它不知你住哪,还不能把你咋的。这个阿德居然直接报出名字地址,那么,死路一条!
阿德眼尾扫一眼红衣女孩。她一直看着死蛇,一脸凄恻,似乎并未留意他的壮举。
说话间,走来一个粗壮的中年农夫,隔老远就喊:“哎,你们看啥,死蛇一条,对吧!”
红衣女孩突然杏目圆睁,凛然地看着中年农夫。
“干吗,这么看人,寒丝丝的!”中年农夫对红衣女孩道。
红衣女孩垂下眼睛,向边上走出几步。她的眼里是一片跃动着的火焰。
“你咋知道一条死蛇?”自知有些冒失的阿德心里有几分毛扎扎地问。
“我咋能不知道是一条死蛇!是我夜里打杀,今早出街带上想卖掉。都讲死蛇卖不掉,街上没人吃死蛇,全要活杀。就甩在这,回去顺便来看看,还在不!”
“死蛇卖不掉,那打杀它做啥?”玲玲恼火地说。
“又不知卖不掉的,再说这是蛇呀!”中年农夫哈哈一笑。
“蛇咋了,总归也是一条命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