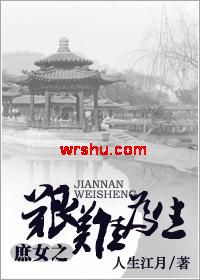红蛇女之怨-蛇怨-第1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双鱼肚白的眼睛。郝妹又埋头发出了低低的啜泣声,她一头杂乱头发的光影在墙上突突突地跳个不停。
门口有几个黑影从大门口迅速地一闪而过。
根发脸上的方巾又被一点一点地拖了回去,但他的手又一点一点地异常吃力地抬了起来,空空地悬浮在门板之上。
蒲包老太取下掖在腋下的手巾,拭去郝妹的眼泪,然后抓起郝妹的一只手握在掌中,喉咙里发出一些奇怪的嗽响。
“郝妹呀,我想问一声,你千万千万不要动气,弄堂里的人都在这样讲……讲我们小芬是……是条……蛇!”
根发的手一下跌落下来,荡在门板沿颤个不停。
“你说啥?”郝妹睁大眼睛看着蒲包老太。
“喏,都是弄堂里的人瞎讲的呀!说小芬是条蛇,咬一口毒杀人,屋里还养着条大蛇,就是掀掉你家屋面的那条蛇。我同你家做邻舍,这么多年,咋就不知道你家还养了条大蛇啊!”
郝妹倏然直起乱颤的身子,咬紧牙关,怒视着蒲包老太道:“啥人讲的,啥人讲的?我要同他拼命,拼命啊!”
“你看看,看看,叫你不……不要动气,不要动气,你还是动气了。”蒲包老太连忙劝慰郝妹,“你只当他们在放屁好了,快别这样,别这样!”
郝妹突然从胸腔中迸出一声哭叫:“是啥人说出这样绝子孙的闲话来呵,我刚刚死掉男人,又来这样的戳我的心,造遥我的小芬呀!”
“这可不是我老太婆想出来的,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邻舍,面孔都没有红过一红。喏,就是住在咱们弄口的那个羊行老板的儿子讲的,他也是听人讲的。”看到郝妹忽然以头戗地,蒲包老太拖拉不动,就急得小脚乱跳,她用手一下一下地掴自己的嘴巴,“叫你搬嘴舌,叫你搬嘴舌!”
蒲包老太一急眼,郝妹这才慢慢地从地上坐起来,一额头的青伤。她痴痴傻傻地看着门板上的男人喃喃自言道:“我也不想活了!”
“我到今朝才知道,我老太婆活到七十几,一把年纪活在狗身上了。”蒲包老太团团乱转,“你郝妹再不敢讲这种活不活,死不死的话了,你要再这样,我马上跳起身来死给你看!”
“根发活过来了!”郝妹惨叫一声,突然跳起身来扑向门板。
蒲包老太觉得脑袋轰的一声炸开来了,她前后一晃,差点儿一屁股坐地下。可她看到的根发眼睛依然是一双死人眼睛。
郝妹对蒲包老太嚷道:“他脸上的方巾刚才遮得严严实实的,手也明明搭在身上,怎么就自己荡下来了呢?”
“呃,你这个郝妹,就不作兴他自己滑下来啊?我年纪大了,不经吓的呀!”蒲包老太急忙又将方巾盖回根发脸上,她连连拍打着自己的胸口,声音战栗地说道,“哦,吓杀我啦,吓杀我啦!我去弄口茶吃吃,顺带再给你绞把毛巾揩揩面,你的额骨头上血也出来了。真是前世作孽呀!”
蒲包老太说着就颠颠地往后面的灶屋跑去。
郝妹坐回小竹椅上,又痴痴傻傻地看着门板上的男人。
蒲包老太掂掂几只竹壳暖瓶,里头没有半点开水。于是她唠叨叨地将水缸里的水舀进灶头的大铁锅中,轰轰地燃起柴火开始烧水。
蒲包老太一手端茶,一手拿了把毛巾,走回客堂间。但客堂间里除了死人根发,空无一人。蒲包老太扯开嗓子凄厉地叫了起来:“郝妹啊……”
蒲包老太赶紧奔出大门去自己家里叫人,她隐隐约约看见几条黑影扛着件东西,消失在弄堂的北出口,便扑进门去大喊:“快点呀,郝妹不见了呀!”
这时从楼上的扶梯口慢悠悠地露出了半个硕大的血红蛇头,俄顷,那蛇头龇出带着些笑意的满口利齿,悠然垂下。
此刻只见大门口红光一闪,那条巨蛇便飞身而下,夺门向南而去。
那红绸穿街过巷,飘飘忽忽地落进了老山泉茶馆后园的潭中。
悬在花厅房梁上的几盏灯的光,打在房顶上,若明若暗地泻在隔壁的耳房墙上。花厅与耳房的房梁是贯通的,两者的隔墙砌到梁下为止。
耳房里有一桌一椅和一床,以供人临时小憩。
杨标目光朝天,躺在床上看着房梁屋顶上那一片散散淡淡的灯光,这灯光又是从隔壁的花厅那儿递过来的。
杨标的手下敲门而入,向他报告镇公所的那个人要见他。
杨标点点头,一挺身跳下床来。
当他刚才在押陆子矶回望江园的路上见他的手下和这个镇公所的人,随便问问他们值守的情况时,竟意外得知:夜半三更,想从司空坊过关的三个孩子中有一个女孩,长相穿着竟与到伤科郎中那儿配伤药的女孩特征完全相符。他的心立刻一动,命他们去查那个声称他爹爹去乡下作法事的孩子,只要找到这个人的儿子,就能找着那个配过伤药的红衣女孩。
闷葫芦一步一个坑地走进耳房,这人长着一张木讷的大脸和一对同样木讷的大眼,一副闷头闷脑看人的样子,令人无形中会多了一分戒心。
杨标坐在床上听他把事儿从头到尾地讲了一遍,发现这人说话音调有些拖泥带水,但涉及的内容倒是讲得清楚明白,几乎没有多余的话,这让他对这位闷兄有了一点好感。
“这小子他娘的说,他爹去了北面的大港村,可这小子却到南面寻人,关键问题在这儿。”闷葫芦慢吞吞地对杨标说道。
“哦!”杨标立即来了兴致。
那个叫阿钟的小孩虽然不知去了哪里,但他们却拿下了另一个,一样的。
杨标让闷葫芦去带人,他要亲自问一问。
“那个孩子,放掉不?”闷葫芦转过脸来问杨标,他指的是林立生。
杨标沉吟一下,点点头。
阿德看到林立生被放掉,心里就慌开了,而看到闷葫芦也走了,他被交到一个眼神冰冷的壮汉手中,并被单独带进花厅的耳房时,他的心里就更慌了。
杨标端坐在窗下的一张琴桌后,窗开着,窗下那一池在暗中明明灭灭地散出一抹抹水光的皱水中,有几篷红莲正在悄然盛开。
杨标的目光冷森森地向阿德看来,阿德则眼神空洞地看着那人身后池中的那一架婀娜有形的大湖奇石。
杨标一看到阿德,马上就认出来,这是他在施家祠堂碰见过的那个孩子,那个常在天黑溜出家门满世界玩的野小孩子。他不觉一阵失望。
杨标轻轻地叹了口气,问道:“为什么要把你带到这儿来,你知道吗?”
阿德哆嗦了一下点点头。他很清楚,这儿和镇上的警所是大大的不同。
“跟你在一起的那个女孩和你另一个朋友,现在在哪里?”
阿德觉得他的腿开始不听使唤地抖了起来,他拼命地用指甲掐自己,抑制着那阵大抖。他觉得只要不说出汝月芬现在在哪儿,汝月芬就没事。他低声道:“汝月芬一早被我们先生叫走了,好像在一起,排练节目吧,夜里讲好要在礼堂演出的。阿钟么,我不知道,今儿一早我也在找他呢。”
说到阿钟,阿德一阵心悸。闷葫芦刚才一直在问阿钟,要是这会儿,他们捉住了他,那可咋办呀!他抬起一高一低的眉毛,疑疑惑惑地看着杨标。
杨标看着这张诚实而又有几分滑稽的小脸,声音不觉带着几分温和地问道:“你害怕什么呀?”
“打!”阿德老老实实地承认道。
“干吗要打你呢?”杨标饶有兴趣地问道。
阿德看看杨标的眼睛,人不抖了,他清清嗓子道:“我们小孩又不知道你们大人的喽,要是你们以为哪一句话说得不对,你们说动手就动手的。”
“你只要照实说,没人打你。照实说,明白吗?”杨标身子向后一靠,替自己点了一支烟。阿德拿出一副很乖顺的样子用力地点点头。
“这个事,如果你说得清楚,马上可以回去。”杨标迟疑了一下,但还是这样问了,“跟你在一起的那个女孩子,半夜三更去一个伤科郎中那儿配伤药的事,你知道不知道?”
阿德一紧张,几滴尿热热地顺大腿滚了下来。连汝月芬配药这事,他们都知道了!他又觉得一层汗从头皮里滋了出来。突然,他脑子豁地一亮,忘乎所以地大叫一声:“知道,咋不知道,那是为我呀!喏,你看看,看看!”
阿德连忙使劲地揪开后脑勺上的头发,低头向杨标亮出他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血痂的伤口。此时此刻,他恨不得向那个阿三伯伯跪下,拜三拜。
“神经过敏!”杨标感到自己非常无趣,忽然他又沉下脸来问阿德,“你兴奋什么?”
阿德意识到自己失态了,连忙陪着小心道:“高兴呵,叔叔不是说,这个事说得清楚,就可以回去了吗?”
“再问一句,你们三个三更半夜不睡觉,到司空坊那儿干什么去?”杨标将烟掐在烟碟里。
阿德马上想起汝月芬眼睛一翻,手指阿钟,声音清亮地答道:“喏,伊拉爷到乡下死人家里去作法事,说好吃夜饭转来,到现在也未回转,去看看。”
阿德赶忙向似乎准备走人的杨标,开始如此这般地作解释。
杨标用指关节敲敲桌面,一脸冰冷地说:“哼,你就编吧,小孩。我刚才咋说来着,你只要照实说,就没有人为难你,是吧!”
阿德自以为万无一失,他一脸天真地说:“是照实说的呀,我要是耍弄叔叔,咋的都行。”
这时杨标一个手下敲门进来,向他示意。
杨标走到阿德面前近乎耳语般地对他说道:“我实话对你说,我们查过一查,你说的那个叫阿钟的小子,他娘说他爹去了桐镇北面的大港村,你的那个阿钟也知道他爹去了桐镇北面的大港村,可你们却到司空坊那面去找人。司空坊在桐镇的南面,我想你不会不知道,是吧!”
阿德浑身一震,他恨不能杀了自己。真他妈的该死,他们连汝月芬配伤药的事都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