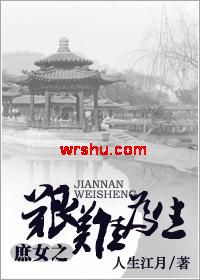红蛇女之怨-蛇怨-第1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到处都是断枝败叶和残砖瓦砾,那地下还有一大片的碎胳膊断腿。
塔上,灵蛇的双眸在那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蓦然一亮,它略一迟疑,便呼的一声,顺梯而下。
毕节生和军士们听到动静,猛抬头,一个个便都噤声而立,呆若木鸡。
陆子矶目击四处喷烟的冒辟尘,从塔上飞身而下,紧接着墙外的老宅里传来几声巨大的爆炸声。他的心在这一刹那也被炸得粉碎,泪水夺眶而出。
南禅寺里的那些军士如流水般地涌出了寺院。
陆子矶拭去眼泪,走出树丛,大步退后,再飞身一跃,一脚蹬上南墙,两手一抓,便上了塔院墙头。他在墙头发足狂奔,避过那幢已经起火的老宅,正要纵身跳下,猛然听见远处传来一声断喝,在他头也不回纵身向下跳去时,突然两声枪声响起。
陆子矶只觉肩头一麻,一个失手,坠落在地。他迅速从地上爬起,向两墙形成的夹弄尽头狂奔。
灵蛇镇定自若地游出扶梯空门,从口中吐出一对相连的大腿,那包裹着白亮亮的黏液的腿脚上穿着一只方口布鞋。
灵蛇仍然将粗大的分叉舌伸向空中探询着,而后抬身钻出南面塔墙的空窗,浩浩荡荡地游过甬道,再直立上墙,弓身滑行而下。
楼下那几扇花窗上有几小股上蹿下跳的火舌,但不一会儿,那些火舌便蜕变成长身吞吐的火蛇,火蛇随着一股股烟雾从楼下的屋子里呼呼地冒了出来。
王伯爵歪斜着被削去半拉头皮的脑袋靠着墙,半坐在如一汪积水似的血泊中。他吃力地撑开被血粘连的眼皮,看了看自己已完全撕开的胸腹和牵扯在外的肠肠肚肚。他不以为他的内脏是被炸开来的,而是被弹到墙上控出来的。他觉得自己的脊背真痛呵,似乎每一节脊骨每一根神经都统统断裂了。他知道他要死了。在这之前,他一直以为死亡是离他非常遥远的一件事,有时他甚至觉得自己不会死,死从来都是别人的事。
这会儿,他觉得自己很傻,干吗呢,大半辈子都在杀来杀去的,提心吊胆,心惊肉跳地过了这大半辈子。他瞅了瞅那几个身首异处的
保镖,觉得他们也傻透了,他们为了一个三百大洋,就把命留在这儿了。哦,这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是属于他自己的,那就是他的生命,这世上最重要的一样东西,那就是活着。
王忆阳披头散发地在那一排破损的楼窗后,来回奔跑。她看着从锁死的房门和楼窗下漫延过来的火舌,号哭着叫道:“爹爹……爹爹呀,救救我……”
他抬着沉重的眼皮又去看那一棵玉兰树上挂着的一颗目眦尽裂的头颅。他一眼就看出了他是谁,虽然他从未见过这张嘴脸,但知道他是谁。他仿佛听见那头颅嘴里的牙齿被咬得格格作响。他从来没见过什么叫做面目狰狞,而这张面孔就是。他不明白他的女儿怎么会和这样一个恶煞通好。
他看看如皮影一般在火中跳动的女儿,忽然觉得裸露在外的心脏一阵大痛。
大门被一阵枪托砸得山响,砸门声中伴随着许多人的叫喊声。看着纹丝不动的大门,王伯爵的脸上露出了一抹莫名其妙的微笑,但那一抹笑容渐渐地变得僵硬起来并很快地凝固了。
一条皮开肉绽但双眸却是精光四射的赤色巨蛇,弓身从墙头上滑行而下。它龇出一排带着寒气的利齿,向他直直蜿蜒而来。当那个带着盔甲质感的龟纹密布的蟮首,吐出Y字形的血舌,目光炯炯地凝视着他的眼睛并将一阵阵带着浓腥的口气丝丝拉拉地喷在他脸上时,他拧过脸去,嘶哑地叫一声:姆妈……而后便一头垂下。
那两楼两底的屋子发出轰的一声巨响,大团大团的浓烟裹挟着深红色的火馅高高地蹿出了屋面,犹如一条条金红的龙蛇向其他屋面游行而去。
第十七章 流 言(1)
施亚平和施艳林在商会办的食堂里用过中饭后,如同一对情侣似地并肩向宝塔街走来。自徐先生开始跟小文女先生勾勾搭搭后,施艳林就坚决不肯同徐先生一起用餐了,徐先生为了避免这一份尴尬,就换了另外一家食堂去搭伙了。现如今,施艳林有事没事就往施亚平那儿跑。不过,施亚平始终牢牢地守住自己的底线,不越雷池一步。打小,他就发现自己有所谓的处女情结,如若哪个女生同哪个男生要好过,后来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分手了,那种女生要找他,他是断断不肯接受的。当初他就觉得自己不能吃亏,被人用过的东西,终究会带着用过的那个人的痕迹,有些烙印。所以施亚平知道自己不会有事,因而他也不怕同施艳林来往,至于有人要嚼舌头,他是完全无所谓的。
他们也想过去看看那艘被桐镇人传红了的游轮。施亚平一听说桐镇开来了这样一艘豪华游轮和护卫的炮艇,就对施艳林说,这样大的排场,来人非天官莫属。什么省上的客人!
施艳林点点头,对施亚平说:“哎,要我说,如果还要演出,你排的那个什么《狼和猫》的节目,我看就算了,不要寻事。”
施艳林又说起,前两年湖南邵阳中学一个叫李洞天的国文先生,出了一个提倡民权的作文题,就被指为乱党而遭枪击;南京有个妇人在菜市场说了一句“早晚时价不同”的话,就遭逮捕。施亚平有时写了些在她看来有点出格的文字,她就拣这些来劝他。
施亚平坚决地摇摇头。
走在路上,就听见南禅寺方向传来一声声犹如闷雷的巨响,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人群突然像涨潮一样地从他们身后往那儿涌去,而从南禅寺方向冒出来的人群则像落潮一样,一波一波地朝这儿涌来。
施亚平和施艳林就紧贴在人家的屋檐下让人通过。不断地有关于宝塔那儿发生爆炸的各种原因传来,但施亚平还是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个桐镇,这一段时间肯定是出怪了!”施亚平对施艳林说。
哈松、泉福从塔梯上摔下来,摔得七荤八素,再被涌来涌去的人流连踩带撞,已经完全晕头转向了。他俩一脸痴痴傻傻的神情,有气无力地逆着人流,东倒西歪地挤了过来。
施艳林“咦”了一声,放开喉咙喊一声:“哈松!”
哈松和泉福转过脸一看见女施先生和男施先生站在路边,两侧鼻翼迅速地扩张开来。施亚平尽管平时特别讨厌这两个学生,但一见他们咧个大嘴快要哭出的样子,不由得心头一热。他和施艳林挡开七碰八碰的人,伸着手向哈松、泉福走去。
一阵阵凄厉的带着簧音的哨笛一路响将开来,人流纷纷闪开,让出路来。两部载着被桐镇人叫作“洋龙”的抽水机的推车一前一后,横冲直撞地沿街推来。
张屠户的皮围裙外,毛毛糙糙地罩了件印有“洋龙会”标志的马甲,他驾着后边的“洋龙车”双把,一膀子撞开一个挡道的人,张口就骂。他突然看到施亚平了,便扭头大喊一声:“施先生,上!”
施亚平虽然不是张屠户一组,但也在一起操练过多次,听他一叫,便放开哈松,向施艳林一点头,就挽着袖子赶上去推车。施艳林扶着哈松肩胛,怅然若失地看着施亚平的背影消失在人流中。
施艳林还没开口,哈松就站在当街结结巴巴地将汝月芬是人蛇的话,从头至尾地对她说了一遍。
“汝月芬不是个人!”施艳林的眼镜从鼻梁上滑下来了,她难以置信地又问一遍,“你是说汝月芬是条蛇?”
哈松、泉福肯定地点了点头,哈松说虽则蛇郎中他们说话声音又低,塔里的风又大,好些话都没听清,但汝月芬的事,他们可是听得真真切切。
施艳林的目光越过那些争先恐后蜂拥而去的人流,朝天看去,她觉得要么是这两个土头灰脸的孩子,要么是那个她在学堂门口见过的蛇郎中,要么是她自己,或者干脆是这个世界疯了。
“他们藏在宝塔里干什么,你们说的那两个什么郎中?”施艳林觉得自己的脑子不大好使了,她本来想再问点有关汝月芬的事。哈松和泉福大力摇头,他们始终没有搞明白那个蛇郎中为什么要在塔里,他们只听见汝月芬是人蛇这个话,就这个。
哈松和泉福还未完全从汝月芬是人蛇的惊骇和那巨大的爆炸声的惊吓中醒来,他们后面追加的有关那两个郎中的谈话,便显得支离破碎,混乱不堪。施艳林一听,就知道这俩头本来就缺点活的蠢驴,脑子完全乱了。
“哈松同学,还有颜泉福同学,你们两个听好了!”施艳林严肃地把两手分别搭在哈松泉福肩上,推一推他们,盯着他们的眼睛说,“汝月芬是人是蛇的事,绝不能再这么对人瞎讲了,那是要弄出人性命来的!汝月芬回头一有点啥事,我就送你俩去吃官司坐监牢,你们可听见!”
哈松泉福脖梗一缩,不住地点头,一脸的诚惶诚恐。
“那就赶紧回家吧,再不要到处乱跑了!”施艳林轻轻地推了哈松泉福一把。
哈松泉福战战兢兢地走了。
施艳林立在原地发了会儿呆,她记起卞德青同她说过这事,王大毛他们怎么霸着路不让过,汝月芬不依,然后王大毛卡人喉咙,蛇郎中怎么救人。但汝月芬咬伤王大毛,那些杀胚怎么可能会没有一点点反应呢?这王大毛是何许人,桐镇人都知道。至于汝月芬在学堂被毒蛇所伤,包括那什么灵蛇弄塌了汝家屋面,汝月芬用药,又如何反应,她想不能说明什么人呵蛇呵的。施艳林这就想到王大毛家去一趟,看是不是汝月芬咬了人,被咬的人就会中毒。她回头向南禅寺方向看了一眼,那儿有一股股狰狞的浓烟扶摇直上云天。要是施亚平在就好了,她想。
施艳林找了个人问了问王大毛家的住址,一路寻过去。
王大毛的家是一幢石库门房子,门前有一条碎石路,墙门两边晒满了各种布片。施艳林走近屋门口,听见一个老头在喊:“死了也好,活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