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货不是马超-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活不下去了谁还有心思管你将军的闺女上学?
至于后来有人乱传说马超奶奶是羌族女子因此马超有四分之一羌族血统,无视之;甚至还有人扯上了天,也不知道从哪里引的经据的典,考察了半天终于发现:三国名将马超为何威名赫赫?那是因为他手下的精锐兵马都是古罗马那边的残兵败将流窜过来的后裔!他奶奶的,不用这么鄙视中国人吧?我们这边不就是因为水土和中原有些差别,风沙大一点,生活简陋一些,导致大家身材长一些眼睛大一些鼻子高一些皮肤糙一些而已嘛!这就二话不说直接妖魔化俺们?!还有没有天理了啊!
而至于后来我的亲弟弟马铁和马休两个小崽子也跟着我们一起上课,那已是三四年后的事情了。
毕竟转世之后也生活了也好几年了,称得上基本适应了这个时代的生活了,其实谈不上适应不适应的问题,因为远在在上辈子的时候,我到重生为止,都只是大学生而已,对于当时的社会也只有那么一点点了解罢了,要说什么适应社会,根本无从谈起。
上了两三个月的私塾,总算是学会写汉代的破字了,笔画还真是繁琐,有的字倒是一看就认识——毕竟还是有简单字流传下来嘛,俺们汉字说到底还是象形字呵!
话说汉末三国这个时代用什么字体我可不认识,我就只认识最基本的宋体楷体,还有我原来打字时最喜欢用的华文新魏……不知道归不知道,但反正一篇文章,用现在我的水平来看,基本上也能明白大半,因为我所拥有“雄厚”的文字底蕴和强大的识字能力,贾夫子在刚开始教书时经常对我的“聪慧”大加赞赏。庞家兄弟对我屡次受到表扬倒是没什么反应,反而是我的亲亲大姐,竟然也有些嫉妒,这姐姐心高气傲,什么事情都不肯向男子低头呢。
不过我的得意与自豪也就到此为止了,除了这点可以作为炫耀资本外,其它方面也就那一般般水平罢了——当他们都认完字之后,我在这方面再如何“天才”,也没机会吹嘘显露了。而且由于对后世填鸭式教育早已形成可怕的依赖性习惯,我反而受不了这夫子仿佛上大课般的传授,时常感觉我在一间几百人上课的大教室里,听着台上的教授摇头晃脑地讲着马哲毛概邓论三代科发,眼皮已经不是我的了……
还好,由于我早期表现优良,贾夫子对我的印象极好,基本上不管我,对我主观上懈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真是体贴的人性化教学啊!
汉末的教育之中,儒家经典当然是绝对的主流,毕竟汉武帝时期重用董仲儒这厮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家都只好学习孔孟之道了,最初听了本《论语》,只能感觉到孔老爷思想很不错,只是确实没什么用,我来来去去也就只能学会初中时学过的那几句最通俗易懂的子曰云云的,乱世之中,这个重要吗?
我很喜欢它们。
但是我不屑学。
鉴于本人对于儒家经典的不屑一顾,以及对于文学事业的无限爱好,我特意从百忙之中抽出一丝闲暇,除了领着赵承到处横行霸道之外,就是窝在房里写写回忆录、抒发一下心中闷骚的小春情了。
记得最早动笔写出来的是一本挺薄的东西,我管它叫做《三国志》。对,咱文化人可不稀罕什么《三国演义》之类的不入流小说,咱是正儿八经的正经人,就写正儿八经的史书,这本书是四五岁时候写的,当时也不认识几个汉朝字,当然用简体中文写着方便了,于是写出来的百来页东西被其它人看起来就属于天书之类了。
我常常叹息:书到用时方恨少,古人诚不欺我也!
这《三国志》一书其实颇为简陋,因为我所认识而且能写出点东西的人物,来来去去也就那二三十人,而且大半都是受演义影响,有时又受过易中天品三国的熏陶,写出来都很……那个,客观公道。
同时为了丰富其内容,我只好再苦思冥想,将演义中所能回忆起来的经典场面编编改改的填充进去,于是,这本严肃的史书中也夹带了一丝的武侠成分了。
对,我是一直蛮喜欢武侠的。可惜。
然后是伟大的第二部著作了,我构思了很长时间,终于决定写一篇长篇巨著。
这应该是一系列设想宏大的作品,讲述的也是一个末代王朝之中的一群年轻的人们,他们为了保护自己身边之人而挥剑奋斗的故事,老套却感人,之中有热血有温情,有权谋有战争,有兄弟也有组织,有势力间激烈残酷的对抗,也有算计中的默无声息。当时我心中激荡了好久,始终不知道该如何给这部必将会在我的人生中永远熠熠闪光的作品命名。苦思了三个时辰之后,大笔毅然落下,雪白的纸上赫然落下五个大字。
“九州缥缈录”!
第五章 文学少年之烦恼
我当时心情激动难以自制,差点忍不住再提起笔来信手加上几个字:
“By江南”。
我的心,我的身,每每随着下笔而颤抖:这是我最为熟悉的故事,这是我极其深爱的人物,当我掷下第三十管秃掉的羊毫小笔时,终于重重地舒了口气。
“他奶奶的江南,死太监!臭坑王!”我怒骂着,“不知道这几年九州出了多少了?捭阖录出到几了?或者因为挣不到钱而跳到其他坑里去了?”
一坑还有一坑深,《九州缥缈录》一二三四五六之后紧接着就是《九州捭阖录》一二三四五六,然后再接着是《九州往事书》一二三四五六,之后说不定又会蹦出来《九州OOXX录》和《九州XXOO书》一二三四五六……可惜,可惜!可惜这厮挖坑太快,填坑太慢!一年也凑不出一本20来万字的书来!江南爷爷,比起奋战在起点的那些日更三章,单章六千的同志们,你汗不汗颜?
我哀叹了一声:可怜这是部太监文,否则我找人再润色润色,找个出版集团出版了,定然是一部千古流传、文人墨客为之倾倒的佳作,什么四大古典名著都tnnd见鬼去吧!而且我还能顺手将祖国的几项文学作品的记录提前个千儿八百年,为国为民,方才是侠之大者啊。
——很抱歉,这大段的介绍不仅啰嗦,而且越看越像缥缈录的广告了……
其实,这只是我前世积攒下来的多年的抱怨罢了。
这系列确实不短,大约至少也有100万字以上了,零零碎碎碎碎的不相干细节我已经忘得七七八八了,不过比之前面一篇大作《三国志》,由于满是热情,反而创作的速度更快,仅仅用了一年便大功告成了,大概母亲们十月怀胎但是难产的感觉恐怕也不过如此吧。
此时已快八岁,前前后后被我挥霍掉的纸张保守估计也有两三千张了,东汉由于大太监蔡伦将造纸术做出重大改进的原因,造纸技术得到了较大的提高,纸张成本据说也大幅下降,开始渐渐进入一般人家之中了,因而造价也愈趋低廉。
饶是如此,老爹仍是心疼不已,偶尔来我房中看到本来都是一卷一卷上好佳纸上上下下全被我用蹩脚的毛笔字涂满,总是默不作声而后离开,但我从他脸上僵硬的微笑中可以隐约感觉到,此刻他必然恨不得一跃而上将我这不孝子捏死,然后用浪费掉的数千张白纸高高垫起,点火,将这败家子连尸首带作品通通烧成灰算了。
看着老爹难看的脸色,我心中当然极为不屑:不论在哪个年代,文盲都是嫉妒文人的啊!
于是我极为心安理得地继续浪费着纸张,又开始了崭新的创作。
童年时代的我,除了打一打猎遛一遛马,上上破课睡睡小觉,实在找不到可以作为娱乐的项目了,实在无聊的厉害,在这种物质生活极其贫乏的情况下,我苦中作乐,决定从主观上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于是我经常诗兴大发,随时随地都能迸发出创意的灵感火花,于是紧随我的赵承就得多费费心了,笔墨纸砚必须随身携带,以满足我这来自现代的文人骚客创作诗词歌赋的需要。
就在这中极其恶劣的情况之下,我在颠簸的马背上完成了数百首经典诗词,从浅显易懂的《悯农》、《鹅》、《静夜思》之类,经由《观沧海》、《游山西村》、《锦瑟》等过渡,逐渐发展到艰涩精深的《卖炭翁》、《春江秋月夜》、《琵琶行》等等,虽然颇有无耻之嫌,但我从来不会因此而半途而废。如此一来,三百首诗词垒起来也有半尺余高,拍起来沉重厚实,一种成就感也油然而生。
至于为何一直蜗居在西北荒地的我,能够以黄毛小子之躯,吟诵出《蜀道难》之奇险、《梦游天姥吟留别》之飘渺、《观刈麦》之辛酸、《水调歌头》之俊逸、《破阵子》之豪迈,《沁园春·雪》之狂傲,《琵琶行》之幽怨,《长恨歌》之婉转,《木兰辞》之不让须眉……其中缘由,就不足为外人道了。
反正我全用简体中文,在外人看来,也只是小孩子家写字不到家罢了。只是我一直当宝贝似的封存在一只铁箱之内,封皮之上赫然落着:“马超孟起文选”六个汉字。当然七八岁左右的孩童尚未取字,我只不过是先知先觉自己顺手占用了而已,反正这“孟起”的名号迟早也只能是我的。
这创作诗词乃是细活,千万急不得赶不得,而且越是心急,质量就越得不到保障,所以我只能在灵感来临时才兴冲冲找纸找笔匆匆记下,然后细细修饰慢慢润色,最后才能编入《文选》之中。
诗词虽是不多,但所费时日却是最长,直到我十多岁时还偶有所得,所以前前后后一共花费了三四年功夫,才将厚厚的几沓《马超孟起文选》的手稿初具规模,这才感到来到这鬼时代后正式做了一件重大之事。嗯,真可谓煞费苦心。
为了自己能够健康成长,最后成为一名文化之人,我不求能够出口成章七部成诗云云,但求偶尔也能配合着时间地点谈话对象和氛围略略抒发一下下闷骚之情即可,总不能这一生都龟缩在这西北一隅,世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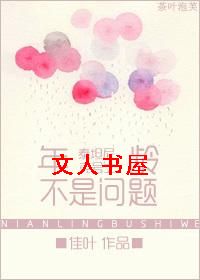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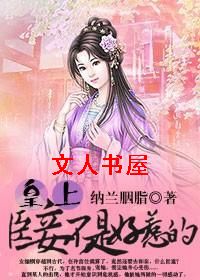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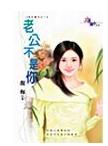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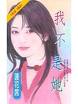
![[火影]悲剧不是你想悲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2/2401.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