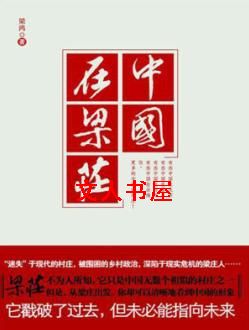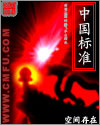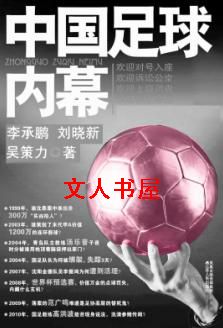中国地脉-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燕赵古风的虎虎生气,但如今却成了一则令人辛酸的历史笑话。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事实是,抗日战争期间,燕赵是狗腿子和汉奸最多的地区之一,惊诧之余,惟一合理的解释是,悲歌慷慨的燕赵古风已经无可奈何地没落了。
但今天的燕赵人仍然敦朴厚实、豪爽重情、正直大度、古道热肠,与此同时他们也较南方人保守老成,安于现状;今天的燕赵人“面瓜”虽不多,但阳刚之气已不能同山东人和东北人相提并论了。
三足鼎立
欧洲著名的教士圣普里安说:“你们必须知道这个时代已经老了。它已经失去了挺立的力量,也失去了使它强壮的精力和体力。”大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在人类曾经创造过的28个文明中,至少有18个已经死亡和消失了。”
作为北温带的历史主角,燕赵人保持了法国人博丁所认为的执著的性格、魁伟的身体和旺盛的精力,然而,由于政治力量的强力介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燕赵文化的核心就在潜移默化之中发生了裂变,它在历史上一体性的文化实体一分为三——北京、天津、河北。
现在看来,“燕赵文化”这几个字多少潜藏着古老的含意了。在今天,谁还能说同样习惯于吃大米白面、喝高粱酒的北京人、天津人、河北人,他们的人文情貌大体上是一回事?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古老的燕赵文化就演出了一幕三足鼎立的历史剧。
河北佬与良民文化(1)
一说到河北,我们就想起了万里长城、北戴河;想起了“邯郸学步”、“黄粱美梦”;想起了少林寺、赵州桥、深州蜜桃、赵县雪梨、保定酱菜、沧州的金丝小枣、铁狮子……
一说到河北人,我们就想起了出没于青纱帐和荷花淀中的敌后武工队,他们腰间扎根灰布条,头上裹块白毛巾,一副敦笃厚道的模样。《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等电影流行的年头,我们充分领教了河北这块土地的情怀,领教了这里人民的宽广无私的奉献
精神。多数河北人是北中国农民中最典型的一个群体,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人传统的东西、传统的美德、传统的弊端,及千百年来所积淀下来的苦难感。
不得不承认进入近代后河北人日益丧失了古代燕赵崇高的尚武精神,除了沧州一带的人们还不时耍弄拳棍、脾气较为火爆之外,大多数河北人已经变成了忠厚老实笑容可掬的良民了,一半是黄种人一半是白种人的辜鸿铭称中国文化是良民文化,这在河北人那儿得到了验证,或许是受到北京这座帝王之都八百年浩大王气的威慑和压制,或许是身处政治权力的漩涡中心被严密看管的缘故,河北人越来越把豪洒威猛的固有禀性深深地掩藏起来,他们整年整月把头埋在土地和热炕窝里温和地打发沉重的人生,除非到了危急的关头,他们勇敢无畏的天性才会显露出来。河北人就像一匹驰骋疆场的刚烈战马,由于不堪承受重压,不堪忍受永无止境的折磨,所以一方面不得不忍辱负重谋求生存和希望,另一方面富有棱角的烈性脾气也变得温和老成、暮气横秋,早年那些英姿飒爽的傲岸英气已经被潜藏起来,成为苦难生涯中吃苦耐劳的老黄牛精神的原动力。我们不大准确地把河北人比喻为迷途知返的老马,然而,河北人已经很少骑马了,“南人乘舟,北人骑马”的古谚在河北消失得无影无踪。
英国人亚当·斯密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最勤勉。然而,很长时间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天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录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关于中国停滞的问题被曾在戴高乐、蓬皮杜、德斯坦时代担任过七任部长的法国人阿兰·佩雷菲特写成了一本书,书的大名就叫《停滞的中国》。
亚当·斯密和阿兰·佩雷菲特所指出的中国文明的停滞性,在河北及中国中西部地区较为显著,放之整个中国则不尽然,进入近代以后,广东、上海等沿海地区及东部许多地区都发生了令人吃惊的深刻变迁。金观涛曾指出,中国文明的停滞性根源于中国传统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超稳定系统。
文明停滞性的主观基因在于人们因循守旧的保守性。清朝灭亡后的一段时期,以河北为中心的北中国地区成为了旧制度旧文化的顽固堡垒,它们是南方革命者批判和发起攻击的对象。
“亲不亲,家乡人,美不美,家乡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河北人就像北温带枝叶茂盛的老槐树一样情愿永远矗立在自己的家乡,他们在这里生生不息,代代繁衍,不论外面的世界多么精彩,也毫不动摇自己的生活方式,毫不为其诱惑而步其后尘。新的思想新的东西要想进入河北显然比其他地方困难得多,因为河北人很固执,他们坚持自己的道理,在他们身上有一种“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的犟劲。河北人的旁边住着一大群素来敏感于政治浪潮、喜好谈论时事的北京人,然而河北人好像被政治整惨了,他们似乎不大关心政治,河北人的旁边盘踞着北中国的一大商业中心天津,那里人的商品经济头脑非常好使,然而德国人利希霍芬在晚清时期考察河北各地后评价说:“河北人缺乏商业精神。”
是不是因为被自己土地上古老的长城压抑得太久了?是不是因为经历了太多金戈铁马的战争创伤?河北人才变得守土重情,成为中国传统良民的衣钵传人。
河北人是重亲的,他们很少有忘本的时候,即使是那些远离家乡的人们也不过是一只只暂时停留异乡的候鸟,他们的心中永远燃烧着一团熊熊大火,永远有一个支撑着他们通向一切的难以解释的梦幻情结,这个情结就是故乡。
河北人对祖先的崇敬和感恩之情难以用文字来描绘,难以用语言来传达。在河北人那里,祖先是人生最大最鲜艳的一面旗帜,是人生行为和方向的指导人。
但是河北人从来不是一些谨小慎微、优柔寡断、精打细算、自私自利的老实人,他们是农业文化的沃土培养起来的天性散漫、大大咧咧、诚实可靠、品质坚毅的“自然之子”,他们使人想到毛主席的那句“吕端大事不糊涂”。这个吕端,就是正宗的河北人,他是北宋宋太宗时期有名的宰相,宋太祖评价他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得吕端真传的河北人,那可就太多了。
河北人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因循守旧、顽固不化的,只要稍微举上几个事例,就不难看出这一点。那位以“胡服骑射”而名留青史的赵武烈王,就是河北人勇于创新的一个典范,他带头脱下宽大厚重的裙裳而改穿细腰精干的胡服,以骑兵代替战车,拉开了战国军事史上伟大改革浪潮的序幕。又如那位被历代怀才不遇的文人墨客所感念吊怀的燕昭王,他为了得到精英人才使国家走向强大,不惜花一大批钱在都城郊外建了一座高大的黄金台,上面堆满了金子,以虔诚的姿态来招揽天下英才,结果很快就有乐毅、辛剧等一大批杰出人才从四面八方赶来,燕国从此走向了强大。又如秦朝时那位河北的著名方士徐福,竟然勇敢地带了一千名童男童女,坐着漂亮的画舫奏着仙乐到茫茫的大海中去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药,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颇有点“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味道,结果搞来搞去徐福竟被一些日本人认作伟大的祖先神武天皇,至今仍有不少日本人到河北来吊怀。上述史实足见河北人并不是保守的“倔驴”。
河北佬与良民文化(2)
尚武精神在河北彻底地没落了,看来河北人是真的不喜欢大刀和枪杆子了,那么他们会在文化方面收拾旗鼓大有作为了吧?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这里的文化水平远赶不上南方各省。就拿科举考试来说吧,作为环拱京师、地位显赫的直隶(即河北)大省,在清代的科举考试中,河北人在总共114名状元中仅占4人,他们是陈德华(雍正甲辰科)、张之万(道光丁未科)、陈冕(光绪癸未科)及末代状元刘春霖(光绪甲辰科)。在科举考试上江苏、浙江、安徽等南方地区独占鳌头,在明清时代出现的224名状元中,他们占去了一大半,整个北方
加起来只有29人。这充分说明五代以后随着整个经济重心的南移,到了明清时期,文化重心也彻底地“孔雀东南飞”了。
北京和天津在河北人心目中有着特殊自豪的意义,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河北的一个部分,只是到了后来才横空出世脱离了出去,正是河北,哺育并滋养了它们,使之成为光耀的明珠。
从地理上看,河北、北京、天津三地就像一个母亲怀抱着自己的两个儿女。翻开一些介绍河北的书籍,开头总是这样的:
“打开祖国的地图,首先收入眼帘的是一颗光芒四射的红五星,她照耀着全国各族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这就是祖国的首都北京。到北京去,不论从椰林葱郁的海南岛,林海雪原的兴安岭,或从牛羊成群的内蒙大草原,都首先要爬上河北的大地。河北位于首都北京的周围,并与天津毗连……”仔细品味一下这些自豪的语句,河北人对北京、天津的亲近之情溢于言表。河北就像个失去了昔时丰神瑰姿的干瘪老母,北京、天津这两个伟岸大器的儿女使她产生出无限欣慰的慰藉之情,而儿女的光环遮掩住了母亲。
北国“恶之花”
在漫长遥远的古代,天津是个被历史遗忘的角落,那些煌煌巨著的史书很少提到过它。那时的天津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是海天一色的万顷碧波,成群结队的灰羽海鸥在宁静的海岸上鸣叫,除此之外,不时来往着一些驾舟到渤海捕鱼捞虾的渔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