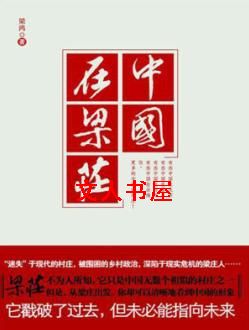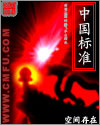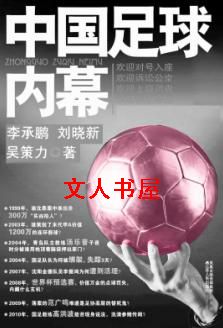中国地脉-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春山如黛,夏山如眠,秋山如霞,冬山如雪。在秋天,燕赵一带的群山,层林尽染,满山红叶与浩瀚蓝天交相辉映,这红色是北中国最为朴素的大观。
秋色弥漫,雄沉辽阔,它使我们作为清醒的梦幻者步入到燕赵博大的深境。掬燕赵篱菊之清花,赏燕赵秋月之高华。林语堂说:“我爱好春,但是春太柔嫩,我爱好夏,但夏太荣夸。因此我爱好秋,因为他的叶子带一些黄色,调子格外柔和,色彩格外浓郁,它又染上一些忧郁的神采和死的预示,它的金黄的浓郁,不是表现春的烂漫,不是表现夏的盛力,而是表现逼近老迈的圆熟与慈和的智慧。它知道人生的有限故知足而乐天。明月辉耀于它的上面,它的颜色好像为了悲愁的回忆而苍白了,但是当与落日余辉接触的时候,它仍能欣然而笑。”
这北国燕赵的秋天,比起南国之秋来,更接近平静、澄明、圆融、智慧的心灵,更具有伟大广泛的激情。“南国之秋,当然也有它的特异的地方,比如廿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四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天来,正像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郁达夫语)
哦,这北国燕赵的秋天,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英雄主义的沃土
元代以来的800百年间,燕赵作为帝王之土长期被笼罩在皇权的辉光里,人性在政治的挤压下日益萎缩内敛。
苍凉的易水愈显枯淡,燕赵的天空已经没有疾劲的大雕。虽然从祖先骨子里遗传下来的
豪放野性仍然潜藏于心,高粱酒和大碗茶仍然醉人,但元代后我们已经难以在这片土地上看到纵横着阳刚血气的激越古风。
李太白在《侠客行》中咏道:“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赢。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煊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英雄何处寻?古风安在哉?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历史上的燕赵曾是奇侠、豪客、英雄、土匪、流氓、大头鬼的乐园,是中国英雄主义的源头和男子汉的降生之地。
燕赵多悲风、多义士。一句“燕赵自古多悲歌慷慨之士”,令我们胸中的块垒沉郁,百感交集。
燕赵蓬勃的英雄主义古风已经成为一种遥远的传说了吗?
古典的铁血(1)
大哲黑格尔对我们说,历史的演进有一个重要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地理,民族精神的许多可能性从中滋生、蔓延出来。同时,地理并不是历史和民族精神的惟一基础,爱奥尼亚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有助于荷马史诗的优美程度,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他指出,人类历史的真正舞台在温带,而且是北温带。
黑格尔说得一点不错,以处于北温带大陆的燕赵文化来看,历史的经验确实如此,从传
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它就一直是产生重大历史事件的中心地区。如果不恰当地把中国比作一个巨人,那么显而易见燕赵就是他宽阔的胸膛,也就是心脏的所在地。这样的地区必然是一个文明所有内在关系的枢纽地带,是王者和霸者必然谋求的领地。
我们不难顺藤摸瓜,理出一些头绪以接近历史的真实。早在黄帝时代,河北就发生了著名的涿鹿之战,战争的一方黄帝部落大约发祥于今天陕西省的北部,后来逐渐向东迁徙,东徙的路线是南下到陕西大荔、朝邑一带,再东渡黄河,顺着中条山和太行山脉向东拓展,最后发展到燕赵地区;炎帝部落大约发祥于今天陕西省的渭水流域,其东迁路线是沿着渭水、黄河东进,一直到达山东一带;而战争的另一方蚩尤部落,史书上又称为“九黎族”,他们主要活动于山东南部、河南东部和安徽北部。这三个当时中国最大部落之间的战争,其原因至今尚未明了,有一种观点认为,当时整个北半球都爆发了可怕的洪水,滔天的洪水淹没了中国的许多地方,平原地区首当其冲,于是,为了争取生存空间,战争爆发了。先是炎帝部落遭到了蚩尤部落的打击,于是炎帝部落被迫投靠黄帝部落,不久以后就发生了涿鹿大战,战争的结果是黄帝和炎帝部落大获全胜,“九黎族”被吞并。后来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之间又在河北爆发了著名的“阪泉之战”,炎帝部落惨遭失败。这两次战争对华夏族(也就是汉族的前身)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那时候开始,连绵的战争在燕赵的土地上再也没有停止过。孟子说:“二百年有一王者兴”,王者常常是从战争中分娩出来的。战争摧毁了原有的一切,使一切面临重新洗牌,开始新的重塑。以有3000年建城史的北京城为例,从战国时期的燕国都城蓟,到后来的渔阳、涿郡、范阳、幽州、幽燕、中都、燕京、大都、北京,名称有如走马灯般不停地转换,而兴建起来的城市,也一次次毁于战乱,再一次次从废墟中矗立起来。其中最为惨痛的有两次,一次是北中国第一形胜之地大金国的燕京,在狂飙突进的蒙古铁骑蹂躏之下被夷为了平地;一次是“聚万国之珍异,选九州之浓芬”的元大都——这座马可·波罗赞叹为当时世界上最宏大壮丽的“汗八里城”,被皇觉寺小和尚出身的朱元璋扫荡得面目全非、满目疮痍。
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说明人类最大的敌人就是人类自己。人类创造了文明,然后又毁弃它,像燕赵这样黄钟大吕的瓦釜雷鸣之地,是不得不产生无数英雄好汉的。
张潮说:“心中小不平,酒可以消之,胸中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血气旺盛的燕赵大地飘满了血腥,那里的人们被迫接受尚武精神。尽管圣明的耶稣在《圣经》中警告说:“血气的东西必亡。”但是燕赵人却只能在血气中谋求一片适合自己生存的夹缝,他们必须使自己的力量更强大,斗志更坚韧;如果不如此的话,他们将很难存在下去。事实上古代土生土长的燕赵人大都在战乱中死于非命,不断出现的自然灾害及异族入侵使这里成为一个祸患绵绵的区域,而每一次大灾难都对人口形成了强有力的“自然淘汰”。
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是,燕赵人中融入了大量骠悍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新鲜血液。那道被当作中国文化象征的万里长城,在燕赵北部的怀来、万全一线一直沿燕山山脉横亘至秦皇岛海滨,远远看去仿佛一条蜿蜒的巨龙。今天,当我们站在被称作燕赵锁钥的山海关下,明代状元萧显徘徊三日后写就的“天下第一关”五个苍劲大字已经引不起我们的陶醉之感。雄阔的万里长城从来就没有成为北中国不可逾越的军事屏障,从战国、西汉到明代,固若金汤般的长城被修了一次又一次,但游牧人的铁骑照样踏破城阙屡屡南进,江山永固、海内晏清的愿望只是不切实际的梦幻空花而已。
地接塞外的燕赵文化面对游牧民族的攻击首当其冲。从遥远的战国甚至更早的时代起,到后来的清朝,我们已经数不清燕赵这块土地到底有多少次当过游牧马队的战利品。没完没了的折腾,直到这块土地也成为入侵者的家园,直到这片辽阔而丰厚的大地以一种张力,将这些桀骛不驯的马上民族驯化成了汉族人中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
在旧兵器时代,不断南下的游牧民族虽然常常赢得战争的胜利,但总是被他们占领的农耕区域所同化,这几乎成了历史游戏的一项法则。
燕赵文化就是一块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通向交汇的前沿阵地。
所以,正宗的燕赵人是血气方刚的自然之子,他们强壮、粗犷、敦厚、老实、直率、鲁莽、义气、勇敢、不拘小节,他们适合于做战场上的征服者,是帝王将相和豪气冲天的壮士土匪的候选人。当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燕赵出现李左车、蒯通、刘秉忠、郭守敬、李春这样巧于机心的人并不值得奇怪。
古典的铁血(2)
另外,燕赵的土地是辽阔的,但也是相对贫瘠的,这个地方的农业在汉代黄河未改道之前曾经一度繁荣,但比不上山东、关中,南北朝以后便不得不依靠运河把南方大量的粮食运过来。五代以后它的经济与南方相比已大为逊色。到了20世纪上半叶,林语堂用“简单的思想和艰苦的生活”来描绘这里的百姓。
在历史上,要适应燕赵寒冷的温带气候和相对艰险的生存环境,人们就必须具备坚强的
体魄和坚毅的品质,正如孟德斯鸠在1748年所指出:“土地贫瘠,使人勤奋、俭朴、耐劳、勇敢和适宜于战争,土地不给与的东西,他们不得不以人力去获得。土地肥沃使人因生活宽裕而柔弱懒惰,贪生怕死。”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北方同南方的战争中南方人常遭失败呢?孟氏的话提醒了我们。
有酒惟浇赵州土(1)
燕赵文化的母胎诞生过中华民族的两大圣人,尧和舜;出过两个了不起的开国皇帝,刘备和赵匡胤;还出过以“半部《论语》打天下”的传奇人物赵普、刚正威严的著名谏臣魏征。
然而真正能够震人心魄,令我们为之击节仰叹的,仍是那慷慨悲歌、充满阳刚之美的群体,他们才是燕赵血脉中的正脉。
伯夷、叔齐,这两位商代末年燕赵北部边境孤竹国国君的王子,本可以继承显赫的国君位置,过金枝玉叶的荣华生活,然而这哥俩的性格也确实奇特,他们不愿蒙受权力之累,于是离开自己的国度,前去投奔素以贤德闻名的周文王,希望到周国养老,过那种与世无争的清静日子。他们在路上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