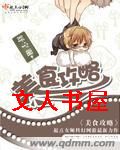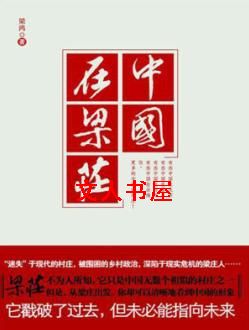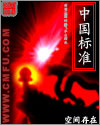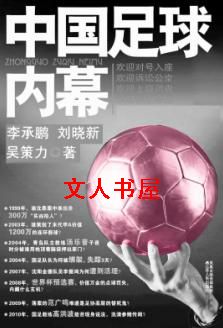闲说中国美食-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肆的山珍海味我吃过不少,却独独怀念着荒村小店的那道无名的乡野菜———没准我的前生就是农夫的命。
我南方的故乡也有一道名菜叫大杂烩,与此较类似。据说是旧社会的餐馆把剩菜残羹收集起来,重新回锅后贱卖给穷人,一个铜板一大海碗。后来的大杂烩模仿其风味,却是精心配料的———内有油炸后的肉皮(俗称皮肚)、剁碎的肉骨头等等。偶尔一吃,确实不同凡响。东北菜中也有一道“乱炖”,名字起得挺好。估计与陕蒙边界的烩菜异曲同工。很遗憾我没有品尝过,尚不敢肯定。人类的食物,不见得非要做得很精致(那太像工艺品了),粗糙点,或许对我们麻木的胃反而是有力的刺激与原始的安慰。
青苔可食
傣族的传统饮食,最令我惊奇的莫过于吃青苔了。这种风俗我在其它地域都很少听说。所以在云南采风的时候,我赞美傣族不仅是以孔雀、大象为吉祥物的民族,而且也是一个热爱青苔的民族———青苔在他们的信仰中或许另有一层涵义?至少,这是最贴近土地与水源的植物了。
傣族是西双版纳的主体民族。西双版纳,傣语原意为十二个田赋单位,后演变为十二个
行政区。“西双”即十二,“版纳”即一千块田(相当于汉语中的千户)。我路过勐腊县勐捧镇的曼哈告,问向导这个地名是什么意思。向导答复:“曼”为寨,“哈”为咬着沙子,“告”为旧,意为“咬着沙子的旧村寨”。封建时代这里是专为召勐捧(勐捧土司)采青苔的奴隶寨。我忙问采青苔作何用?向导说:当然是吃———那时候青苔可是好东西,属于傣家人敬贡贵族和招待客人的上等食品。据说有一次曼哈告的人采摘的青苔没洗干净,土司嚼食时多次咬着沙子,很生气:“你们怎么搞的?青苔都洗不干净,沙子我都咬到了几次。”于是曼哈告这个村寨因而得名。我由这个典故,得知青苔居然是可食用的。
傣族人家大都傍水而居,偏爱水生藻类植物做成的菜肴,傣语称为“改”和“捣”的两种青苔更为其首选———据说这两种藻类植物营养丰富,口味独特,可从水里捞出洗净后,加工成青苔干片食用。估计就像内陆的汉人吃晒干后的紫菜的方式,嗜好那种清香的海味。而且便于贮藏。
“改”指附在江河里鹅卵石上的青苔,草绿色,呈丝状。因为只在阳历的一、二、三月间有,所以需及时打捞出来,制成青苔干片以备全年食用。将洗净的青苔丝拉开,压成直径一尺左右的薄圆饼晒干,叫“改义”。吃法有多种。可以用炭火烘烤,然后用手揉碎在砂锅里,加葱花、油盐烩炒,搭糯米饭吃尤其精彩。还可捣碎后和鸡蛋拌匀,加葱、蒜、芫荽、油、盐等作料放入蒸笼里蒸(青苔鸡蛋羹)。当然,还可以煮入肉汤或鸡蛋汤……将洗净的青苔压成薄饼,洒上加盐的姜汤后再晒干,叫“改英”。吃时用剪刀剪成手掌大小的小块,用竹片夹住,抹上猪油,在炭火上稍加烘烤,即可用来下饭;也可直接在锅里油煎……
“捣”指湖泊、鱼塘里的青苔,估计与江河里的滋味稍有区别———傣家人肯定最清楚。吃法也最有戏剧性。捞出洗净后盛在大海碗里,加姜、葱、蒜、盐等作料,兑上水,随即轻轻放入一块烧红的鹅卵石———伴着汤水沸腾的声音,一股海鲜的香气腾云驾雾。一眨眼青苔就熟了,可用糯米饭团蘸食———此可谓“快餐”也。
以上皆为根据当地人的讲述所做的记录。青苔的菜肴,我并未亲口尝试过。倒是很想尝鲜,可惜没有口福———遍寻版纳的餐馆,没见到这道特色菜。莫非它已退出了当代的宴席?在我生活的都市里,自称美食家的很多,但品尝过青苔的滋味的———恐怕寥寥无几。我至少还算听说过。听说过这道快失传了的美味。记录下来,聊以备忘也。
咸肉
重温生活于江苏老家的那一段童年记忆,最温馨的莫过于和饮食有关的———江苏似乎天生就该是培育美食家的地方。这样自然要想起悬挂在家家户户屋檐下或晒台上的一串串咸肉。江苏的咸肉,远远没有邻近的浙江金华的火腿那样出名,做工上也绝对是两码事;虽然它选择的同样也是上好的猪肉,但不限于腿部,而且系用粗盐在坛坛罐罐里腌制(加少许家常香料),一定时间后取出,穿上线绳后挂在露天里风干。跟其他省份的人讲起吾乡的咸肉,容易造成误会:以为那与湖南的腊肉相似。必须小心地解释,由于没经过那烟熏火燎的系列
工序,咸肉要显得本色一些,吃起来也没有烟火的味道。
我是通过跟火腿与腊肉的比较论述咸肉的。不知是否讲解清楚了?咸肉属于盐水腌制的食品,风干后能看见亮晶晶的盐粒凝结在上面———咸味业已深入进其内部了。因而咸肉便于保存。我祖母家每年初冬都要清洗各种坛罐,用来腌制咸肉,足够吃一年的。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窗台上还悬挂有咸肉,接待客人或亲友团聚就不用发愁了。切一块下来,清水泡一泡,可以切片后在饭锅里蒸熟(油汪汪的),更可以炒菜(咸肉丁)或煲汤。吾乡有一道脍炙人口的河蚌咸肉煲,系用新挖出来的河蚌肉加咸肉片炖汤,其汤白得像牛奶一样,喝一汤匙便发现,鲜美得能透人肺腑。而且鲜中有咸,咸中有鲜。广东人是煲汤的好手,我在广东喝过形形色色的汤,可没有哪种能盖住我在老家时喝过的河蚌咸肉煲的余味。我已好多年疏远了此味。想念一道好汤,有时候就像酒鬼难忘某种佳酿似的。这种馋会使人心痒痒的。
吾乡的咸肉,除了自食,就是馈赠亲友,但似乎不登大雅之堂———至少商店里没有卖的。我父母是读书人,不懂腌制,每年春节给老家的亲友拜年,总能收获几串咸肉。我进而联想,孔子的时代,他门下的弟子敬献的那一串串干肉(作为学费),或许就是这种咸肉吧?实际上咸肉的制作,也是一门平民化的学问呢。这种滋味,在我读好文章时也能找到。忆念中的老家的咸肉,令我咀嚼到某种民间的传统与风俗。
吾乡人还按腌制咸肉的方法,腌制咸鱼,腌制咸板鸭———南京的咸板鸭是一道名吃,据说明清时就有了。每年初冬清洗坛坛罐罐,小瓦罐用来腌制肉类,而大坛子则用来腌制蔬菜(有的人家甚至用半人高的水缸)。腌制的蔬菜主要是青菜或雪里红,俗称腌菜。炖排骨汤时若能加一两棵腌菜头进去,味道更醇厚了,也不再觉得油腻。用切碎的雪里红炒毛豆,最适宜喝粥时佐餐的了。我想,从是否擅长腌制食品,能管窥出一个地方的人民是否会过日子至少,江苏人以会过日子而闻名。在过去的年代,老家的百姓,一生就是在这祖传的坛坛罐罐中间度过的。那里面浸泡着他们的清贫,也浸泡着他们的富有。
冰糖葫芦
我从南方第一次来北京,是八十年代末。当时逛天坛公园,发现鱼贯而入的男女游客均人手一枝串满晶莹剔透的红果的小棒,津津有味地咀嚼着。我猜测那该是大名鼎鼎的冰糖葫芦了。再往周围一看就明白了:公园门前的空地上,站了一溜手持稻草秸捆扎成的“靶子”的摊贩,草靶上一律乱箭穿身般插满了红彤彤的冰糖葫芦(中国式的圣诞树)。当时我想,北京人不怕冷吗,大冬天缩着脖子也敢吃冰糖葫芦?这是冰糖葫芦的名称给我造成的心理错觉。或许也不能算是误会,在零下几度的室外气温中,冰糖葫芦经风一吹,像一张张红扑扑
的小脸蛋———眼泪汪汪,连外面裹着的糖浆都冻成冰棱的模样。咬一下肯定嘎吱作响。你简直分辨不清咀嚼的究竟是冰抑或是糖。你的腮帮子冻得都快麻木了———恰恰这时候,那冰糖包裹的新鲜山楂透人肺腑的酸味,会给你一个强烈的刺激。你无法拒绝它向你揭示的五味俱全的谜底……
这毕竟是苍白枯燥的冬季硕果仅存的一份诗意。即使从视觉上的效果来说,颇印证了鲁迅一首散文诗的标题:火的冰。一枝独放的火焰,正炫耀地炽烈着,忽然,仿佛服从冥冥之中的符咒,它被冰封存了、冻僵了,进入一个无声且没有意念的世界。即使在冬眠之中,它仍然保持着火的原型、火的颜色以及性格。你咀嚼着冰的同时实际上在吞食着火。它的双重性格很快把你给感染了……我为什么要做这么多诗化的联想呢?难道最最平民化的冰糖葫芦真的存在什么精神内核?这还得感谢我八年前在北京露天街道上品尝到的第一根冰糖葫芦。是那根用五毛钱购买的冰糖葫芦给了我价值连城的灵感。北京城里的冰糖葫芦哟,从此进入了一位外乡人的视野。
冰糖葫芦是很有北京特色的一种食品。从某种程度上说:它甚至可能代表某种朴素安祥而又不乏历史感的市井生活。林语堂在一部回忆清末民初北京历史文化的专著里,也未能忽略它的存在,仿佛信笔提及:“不管白天还是晚上都会听到小贩们叫卖甘美圆润的冻柿子的吆喝声,还有孩子们喜欢吃的冰糖葫芦,裹着糖的小果,五六个串成一串,染上红色招徕顾客……”这部书是他后来在大洋彼岸用英文写作的。可见冰糖葫芦的造型,已深深镶嵌进他的记忆里了。冰糖葫芦,仿佛也构成一位读书人对老北京城的回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了。
能够代表那种古朴的老北京生活的当然不仅是冰糖葫芦,还包括其它当地小吃:豆汁、油茶、灌肠、卤煮火烧、豌豆黄、艾窝窝、褡裢火烧、炒肝、焦圈、酸梅汤、扒糕、羊头肉、驴打滚……甚至有些估计快失传了。作为一个迟到者,我真恨不得一一品尝它们或记录它们。但在这篇短文中,我只能举冰糖葫芦为例了。
冰糖葫芦堪称最原始也最传统的糖果了。和后来商店里零售的各种用塑料纸或锡箔包装的水果糖存在着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