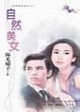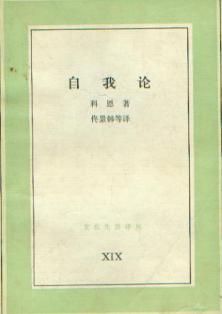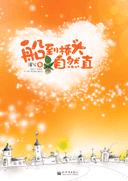人与自然 系列丛书-第6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而带得最多的是水。
尽管带了这么多的生活用品和装置,但菲利普·弗雷仍然估计这次冒险不会是天天令人快活的,肯定会遇到许多想到的和想不到的困难。因为他选择的路线,从埃及往南,恰好就是撒哈拉大沙漠的南段。要经过苏丹、乍得、尼日尔、马里,然后抵达毛里塔尼亚的西边港口。这是他自己向大自然的挑战,也是向一种超出常人能力的挑战。菲利普·弗雷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身体的不适应。炙热难忍,不到半个月几乎脱了一层皮。每天走50~60公里,相当于骆驼最快的脚程。体力消耗很大,常感到非常疲累。实在不行就爬到骆驼背上,有好几次差点摔了下来。在整个行程中,先后有12峰骆驼被累垮了,其中有两头累死在沙丘里。
最困扰人的还是水的问题。菲利普几乎一路都在为水而奋斗。有一次,他为了找一个名叫宰维纳的水井,竟背着30升水徒步走了100里路。但当他终于找到那口有水的井时,身上的水只剩3升了。为了找水,他多次摔倒在枯井边上,险些死在那里。还有一次,在马里境内,一帮游牧民抢走了他储备的所有的水和食品。等那些家伙离开后,他在没有一滴水的情况下,走了36个小时,才发现一口井。当时,他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事实,总以为自己的旅行和生命都要到此结束了。他一直认为这是侥幸。
不仅如此,一些国家断然拒绝他穿越它们的边境。埃及人禁止他越过苏丹边界,雇请的一名“向导”,实际是在监视他的行动。后来在一天夜里,他巧妙地甩掉了那个陪同,进入了苏丹境内。有一次,他看了几眼乍得境内被地雷炸毁的车队,被哈布雷的士兵当成是来侦探军事设施的法国间谍,把他抓去关押起来。在离关押他的小屋约有10米远的地方,士兵们枪杀了350名反政府俘虏。当时他最怕他们把他押到一个秘密地方去处死。他倒不是怕死,而是不愿意做一个无辜的牺牲品。可是,关押了1个月以后,大概是没有审查出什么问题,就又把他放了。
乍得的士兵们是用汽车把菲利普·弗雷押解到尼日尔边界的。这对菲利普来说,却是无法忍受的。因为他曾发誓要徒步走完撒哈拉的全程,而乘车违背了他的誓愿,等于中断了他的考察,这使他十分懊恼。为此,他在尼日尔又买了两峰骆驼,再次越过乍得边界,返回到一个月前被乍得士兵抓起来的地方,继续着前段的旅行和考察。
经过8个多月的艰难跋涉,菲利普·弗雷最后到了毛里塔尼亚。
在这他遇到了一个最糟糕的天气,沙暴卷走了他的地图。这意味着他随时都有迷失方向的危险,幸亏他还模模糊糊地记得要去的目的地。沙暴过后,他只好用头巾蒙在眼睛上继续前进。就这样,菲利普·弗雷以他超人的顽强毅力,战胜了重重险阻,终于实现了他的宏愿。
沙漠历险记
科莱特一家都是法国人。父亲是一位工程师,母亲和哥哥让·米歇尔也都工作,她和15岁的妹妹正在上学,应该说,他们这一家是非常幸福的。前几年,他们曾几次作过横贯撒哈拉大沙漠的度假旅行,大家每谈起来气氛总是很热烈的。所以他们一直向往着重游大沙漠,并打算利用她和妹妹玛丽放寒假期间,实施这一计划。1983年12月18日出发的前夕,让·米歇尔突然有事不能去了,特地赶来为他们送行。
12月24日,他们就发现迷路了,到了晚上,汽车又因汽油告罄而抛锚,把他们扔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一片旷无人烟的荒漠里,一望无际的沙丘又无情地横在他们面前。这时,科莱特和她的父亲才意识到他们是走投无路了,迫切希望有人来找他们。为了这个缘故,他们在沙地上划了不少特大的“SOS”字样,从汽车的每一侧写开去,一直到6公里左右。但是3天过去了,5天过去了,一个星期过去了,他们除了29日那天夜幕降临时,先后发现3架飞机一晃而过外,其他什么都没看到。他们不得不作着最坏的打算。他们先是把食物和水采取了定量供应,其次是坚持在附近走动,借以锻炼身体,增强适应能力,而更多的时间则是躺在睡袋里。这是一种设计精细的、衬有薄金属片的鸭绒睡袋。躺在里边有助于防止脱水,夜间还可以御寒。
撒哈拉地区昼夜温差很大,白天非常燥热,气温常在22℃左右,夜里则猛降到零度以下。空气异常干燥,地面没有一点水,也没有一棵植物含有水份。事实上,在他们焦急等待的同时,让·米歇尔正在向法国外交部告急求援,向塔曼腊塞特呼救,但得不到任何消息。1月6日,米歇尔又登上去塔曼腊塞特的班机,以便亲自组织搜索营救,其结果也只是徒劳往返。
食物和水已经少得可怜了。每个人都开始出现脱水的征兆:个个瘦骨嶙峋,形骸可怖;头昏眼花,开始痉挛;吃东西不敢咀嚼,囫囵吞咽下去。。。在这种极端痛苦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紧紧地挨在一起,或者躺在汽车底下的睡袋里,除了说话、睡觉,别的什么都不干。他们谈话可真是天南地北、海阔天空,而且全是逗人发笑的故事。这样可以使他们暂时忘记痛苦,感到轻松。另一方面,他们还谈论明天,谈论重返法国,谈论着今后各种各样的打算,说些互相鼓舞的话。据科莱特小姐后来回忆说,她从未感到过家人如此亲近体贴,互相关怀;从未感到过父母对她和妹妹这样深切的爱,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每天还能优先保证她和妹妹的一份吃的和饮水,这是一种伟大的爱。一天夜里,忽然听见几声枪响,虽然无法辨别方向,但他们明显感到有人就在附近。他们以为是营救的人来了,但嗓门已干得无法叫喊。科莱特的父亲急忙冲到汽车跟前按喇叭,还开足了收音机的音量。枪声却很快停止了,随后就没有了一点动静。直到营救人员于1月13日找到他们时,57岁的父亲和15岁的妹妹已经死去,54岁的母亲第二天凌晨两点也咽了气。
科莱特算是幸存了下来,被急救飞机运往巴黎医院,在昏迷中度过了7个昼夜,一个半月后才恢复了说话能力。但她仍然很顽强,除了对死去亲人表示悲伤外,又和看护她的哥哥商量着重建新生活,以及完全康复后有机会再横跨撒哈拉。
他们穿过了“死亡之海”
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世界第二大沙漠,东西长,南北宽。近100年来,虽然有过从南到北横穿的先例,但东西纵穿沙漠全境没有过。19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瑞典著名的探险家斯文·赫定曾雄心勃勃地试图从西向东进行徒步穿越,但没有成功。后来,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就把塔克拉玛干沙漠称为“死亡之海”,沙漠由此而扬名天下。
1993年9月下旬,中国探险史上忽然闪出一道奇光。经过有关部门4年多的筹划准备,由中英组成的联合探险队,终于向这个“死亡之海”挑战了。
9月24日,他们从沙漠西部南端的麦盖提县城正式出发,向着东方,向着沙漠的纵深开进。
这一消息,震憾了世界。中国的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上海《新民晚报》、新疆乌鲁木齐经济广播电台,以及英国有关新闻单位,都先后派记者,通过种种方式进入沙漠,进入现场采访拍摄,及时向国内外报道探险实况。
头几天,他们翻越的还都是50米以下的沙丘,越往前沙丘越高,有的竟高达100多米到200米,被称为沙山。这些大大小小的沙丘和沙山,从空中往下看,十分壮观,一般都是新月形的,纵横走向的大都比较整齐。但随着风向、风力和地形的变化,有时也不规则。那干涸的河床,往往是貌似忠厚,却暗藏杀机。有的地段表层干硬,底下松软;有的地段下面还有水。这些不仅使人畜、车辆和行走变得异常艰难,弄不好还会陷车、迷失方向,或者被流沙吞没。当探险第二阶段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的3名记者搭乘支援队的车,于10月7日进入沙漠拍摄探险情况。由于连绵不断的沙丘阻隔,车开起来十分吃力,差不多每过10分钟,发动机就要开锅一次,加上多次陷车,只得走走停停。一不留神,中途竟迷失了方向。直到9日,记者们才被过路的石油物探局的车搭救,并把他们送到探险队的第一接应营地——麻扎塔格山东麓。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气候,就像疯子的脸,变幻多端,喜怒无常,令人讨厌而又害怕。探险队刚进沙漠时,还是夏天的气候,但早晚温差很大。白天像火球一样的太阳,把地面的沙子烤得滚烫,地表温度甚至高达80℃。人走在上面就像踏进了烧干的锅,全身都感到烘烤,沙子灌进鞋里,脚都感觉出烫来。一到夜晚,太阳落下地平线,气温就急剧下降,一般都在零下几摄氏度,队员们钻进睡袋里还冻得瑟瑟发抖,半夜里常常被冻醒。
就在他们进入沙漠400公里,快到第一个接应营地时,美国摄影师萨特和英方队员葛利亨,因中暑虚脱终于被拖垮了,以致到了第二阶段,不得不遗憾地挥泪向同伴们告别。
在炎热的沙漠里长途跋涉,人畜的体力消耗很大,水就成了大问题。然而没过几天,水井竟神奇般地不出水了。他们计算了一下,9天当中挖了8眼井,只有1天打出了水。
被誉为“沙漠之舟”的骆驼,面对“死亡之海”的干涸,也居然失去了耐性,竟乱跑起来,还踢伤了人。到了11月初,有的骆驼终于因缺水和过度劳累而死亡。
在探险进入后一阶段时,有一天他们忽然遇上了沙暴。狂风卷着黄沙,遮天蔽日,有如8级大风之猛。单个人是绝对无法行走的。飞沙不只是硬梆梆地打在脸上,而是从头到脚往下灌,幸亏他们还有经验,在沙暴没到之前,人马就簇拥到一起,顶着猛烈的风沙,慢慢前进。这次沙暴他们虽然没遭受什么损失,但原计划到达终点的日期,不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