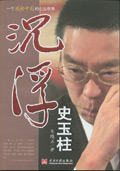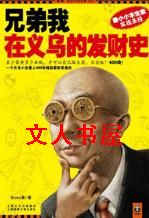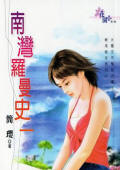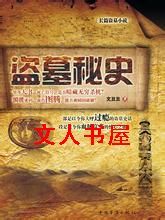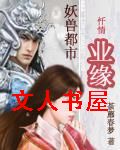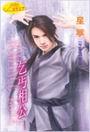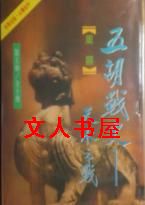乞丐的历史-第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际,乞丐往往成为隐士的托系之所,乞丐生涯遂成为“英雄失足的退步,好汉落魄的后门”。(李笠翁语)
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历程中,由于吏治的腐败、制度的偏失、文网的严酷,致使隐士不断涌现,代代不绝。失势的官僚,落魄的文人、狂生异徒构成隐士的主体,他们寄寓于乞丐中间,使乞丐文化呈现出良莠相杂、雅俗互补的景象。隐士们的所作所为给乞丐文化以重要影响,他们逍遥超然的处世哲学,放荡不羁、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愤世嫉俗、淡泊名节的人格特征,善良正直的秉性,极大地丰富了乞丐的精神世界,隐士的风格不啻是飘荡在混浊不堪的乞丐世界上空的几缕清风,是闪烁在漆黑一团的乞丐王国中的几道亮点。
隐士行乞活动的最大特点在于他们不改故态,绝少乞丐的庸劣之气。他们虽饥寒交迫,却从不强索强讨,更不会厚颜取媚、巧言逢迎,而是不卑不亢,取食有道,取食有度。如《新五代史》载,李蜒本为以文章知名的士人,唐末举进士及第,官至监察御史,一生清廉,家无所积,后遭父母之丧,贫无以葬,只好乞食而后葬。隐士的乞讨不仅是出自有因,而且他们乞食从不贪多,足食充饥而已。如《说邪》上记载:“泉州有贫士行乞,得钱,尽买花麻饼食之”,自己吃一些,余皆分给儿童,以至孩童们呼之为“饼道人”。《清稗类钞》所载“永光寺前之丐”也属此类人物。该书记载:清道光年间,北京海岱门内永光寺前,有一位乞丐,其行为举止也颇奇异。此丐年约40,长杖击善说笑话,每每以俗语随口编成小曲吟娥咏唱,市民争相施舍钱物。此丐也不贪,将钱买一顿酒饭,余钱尽散于他人,一个子儿也不留。据传此丐本是世家贵胄,已经袭了侯爵,尝持戟于清门。后来厌倦寻常生活,弃家出走,混迹于乞丐者流,时而也回家看看,有时则终年浪迹在外,逍遥游乐,他家人多次苦劝他回去,尽以锦衣珍食满足他,但他不以为意,住上三五日,乘家人不备,又换上破衣去游荡,于此终了一生。
隐士的行乞活动往往呈现出放浪不羁之状,以至他们的行为举止,常人难以理喻。此中典型事例就是裴休行乞。裴休是唐代文人,以书法、文章名世,他中年时常常身着袈裟,托钵乞食于妓院,引为人生乐事。苏轼有诗专论其事,其诗曰:
病骨难堪玉带围,钝银仍落箭锋机;
欲教乞食歌妓院,故与云山旧衲衣。
落魄文人虽沦为乞丐,但他们往往不改文人本色,行乞之途,吟诗不辍。据《涌幢小品》记载,明朝成化年间,有一位叫李兴生的乞丐,年67,患有风瘫病,手、口、眼俱惊挛。但颇能作诗。进士董时望喜欢他的才华,想“养丐于官”,但李兴生坚持不肯,董时望只好“礼而厚道遣之”。
又据《清稗类钞·乞丐类》载:
清代福州西市有一奇丐,衣衫褴褛,每日手提一只布口袋行乞于市,布袋里鼓鼓囊囊不知装是何物,边行边吟,路人怪之,有好事者尾随其后,这丐来到一处空地,把口袋摊放地上,从衣中取出纸,铺在地上,纸上书有“四海散人痛苦”六个端楷大字,下面有数行小字,叙其由浙入闽寻亲不遇,流落至此,已经饿了三天,请求各位解囊相助云尔。颇有告地状的味道,观者怜之,纷纷投以铜贝。这位乞丐并不理睬,慢慢从布袋里取出一部书卷,高声朗读,声音嘹响,并含许多隐语。久之,他才俯身从地上拾起别人扔下的铜钱,昂然走进一家书店,把所有的钱都买了书。将书绑在腰间,仍然行乞市中。有人好奇地问他:“你怎么还有闲钱买书?”他却哂然答道:“你等并非鸿鹄,又怎知我之志向!”说罢便拂袖而去。后来,人们再也没见到他。这显然是一位落魄为丐而故态不改的文人。
隐士行乞不仅大多保持着文士的本色,或行吟道上或歌咏市中,而且言谈玄妙、行迹放逸,颇有道骨仙风之态。据传光绪丁西年(1897),北京城中有个乞丐,年逾花甲,满头银发,他的行止与一般乞丐大不相同,如果讨得较多的钱,就随手散给更穷的人,或者就去买爆竹放。无论是酷暑或严冬,他总是只穿件葛布单衣,光头赤足,往来市中,如狂似癫,时人呼之曰“糊涂叟”。
“糊涂叟”常携一葫芦到处游荡,自称“葫芦老儿”。有人认为他是铁拐李之类的仙流,争着向他问道求法,“糊涂叟”却说:“我不是仙人,而且从古至今也根本没有仙人。说仙道神都是自欺欺人的谎言!”有人又说他当年曾长山西某县,因刚直不阿而遭上司嫉恨,差点丢掉性命,他就离家逃难,以至于此。“糊涂叟”听了后喃喃自语道:“丢弃骨肉而谋自保,我干不出这种事!”还有人说他原籍山东某镇,少年即负才名,但科场不利,屡试不售,愤而出走为丐。“糊涂叟”听后,不以为然地说:“我本来无才,即使是怀才不遇,也是平常之事,世间类此者多的是,我有什么好愤恨的!”有人问他为什么总放爆竹,“糊涂叟”答曰:“聊以警醒世人。”又有人问他睡在何处,答曰:“此是个闷葫芦,你等不必知晓!”一些好事者有时特意多给些钱他,他每每辞谢,只取几文钱,余者或退还施主,或尽数散给乞丐及路上的幼童。世人都对“糊涂叟”的举止捉摸不透,对他的身世也打听不出个究竟来。后数年,清廷政局紊乱,内外交困,“糊涂叟”感叹道:“天下看样子要大乱了,此地再不可逗留了。”从此,京城中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了,不久,庚子之役爆发,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糊涂叟”一点也不糊涂,他的行止大有“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味道,这是隐于乞丐行列的文士的典型风格。乞丐中这种似癫似狂,半人半仙的隐士大多行止狂狷、言语怪异,秉性既有侠士之风,又有仙道之气,谯陵张乞儿即是这种类型。据说张乞儿在雍正八年(1703)行乞至鄂省周家口,当地人见他跛足而行、衣衫褴褛,却气度不凡,独自一人在村北坟地里挖个洞,不论酷暑寒冬,枯坐洞内,闭目瞑思,三五天出洞行乞一次。有一次大雪覆地,村民们以为他要冻死了,纷纷跑去观看,扒开雪一看,张乞儿正呼呼大睡。众人大为惊诧,从此以奇人视之,远近村民争相施舍食物,他只是偶尔领受,余皆退还。好心人专门为他在洞上搭个棚子,他旋即将它拆掉,说是天地为屋,大伙不必操心。后三年,张乞儿突然离开了周家口,行前留下一句话:“谢谢众位,此地不可久留。”众皆不以为意,不多久,太平天国战事爆发,周家口成为交战地,霎时间成为一片焦土,劫后余生的村民们这才悟到张乞儿行前留言的用意。(引自《中国丐帮》,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98、199页)
四隐士风格(2)
《清稗类钞》“乞丐类”搜罗许多这类隐士型乞丐,例如该书记载清代吴中洞庭山有一乞丐,不知名姓,行迹狂狷放逸,日间沿途行乞,夜宿庙宇之中,行乞之暇,每有诗作佳构。清代著名的文人汪碗曾收集到他写的数首诗,如“不信乾坤大,超然世莫群。口吐三峡水,脚踏万方云”。“一杖穿云到上方,湖光山色总茫茫。乾坤有无能担担,明月清风底大忙。”其诗气势宏大,寓意深刻,毫无颓废、自报自弃的心理,显示了这位文人乞丐的超群脱俗的思想境界和文学造诣。又据《三借庐笔谈》卷六记载,有一南来之丐,白天行于街市,夜间宿于破寺,不言不笑,人合则取之。一日狂歌于市上,被一文人丁小舟看见,甚奇之。便在夜深人静之时,到破寺去拜访他,不想未见其人,却见其诗,曰:“怕作人间公与侯,风尘落拓试庸流,果然大地无青眼,要去乘槎上头牛。雄心磊磊总难平,匣里龙泉入夜鸣,只有小舟能识我,他年书记要留卿。”后来,小舟又几次前往,终未能相遇,方知此丐是在有意回避他。
在隐逸型乞丐中,除落魂之人、失意士子、专制政治的不合执行者,还有一些家道破落的世家子弟,性情怪异的文人雅士,放荡不羁的自由主义者,等等,落魄文人、各种类型的隐士组成乞丐群体中一个亚种,应该说,他们的人生态度、行为取向与上面所论及的乞丐行为文化的诸种形态是迥乎有别的。落魄文人、隐士的贫困无聊之状与乞丐无异,但他们绝少普通乞丐所带有的那种庸劣习性、江湖习气,更无流氓痞棍的作派。文人隐士们沦落为丐并甘愿为丐,主要在于他们向慕乞丐生活无拘无束的超然状态,在这种超然放逸的生活中,他们尽情感受着的心灵的自由和人生的洒脱,体味着生命价值的另一种实现方式。
沟通雅俗 整合民俗
一 寓雅于俗的街头演艺(1)
乞丐的文化媒介作用与社会职事
社会,作为一个要素众多、结构复杂、功能多样的大系统,其
运行发展与变迁进化乃是结构分化、功能整合的过程。按功能主义和文化学派的观点,社会的每一结构要素分别承担着特定的功能,以满足社会生存发展的需要,社会系统内各要素的结构分化与功能整合实为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机制。
社会的结构要素,诸如制度、规范、组织、设施、风俗、习惯、信仰、传说、阶层、群体、个人等等,在社会系统中各有所能,也各有所需,它们都承担着某种特定的功能,并与其他要素的功能互为关联、互为耦合。社会系统内结构要素的功能往往通过其特定的社会职事(职业、行为、活动)表现出来。人们通常所谓的士农工商各有所职、各有所专即是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问题的。它表明:各个阶层、各个群体都是一个具体的功能载体,都满足着一定的社会需求,若此,社会才能互相关联,互为补充,才会呈现出协调稳定的运行状态。
对于士、农、工、商以及主流社会的各个阶层和群体的功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