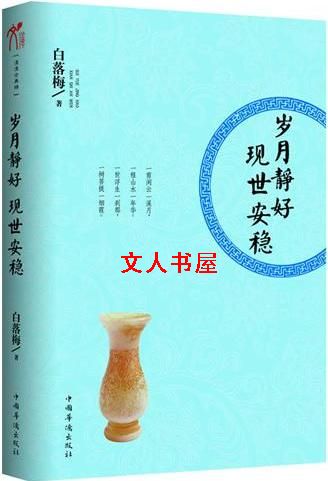流金岁月-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南孙用手指印去眼角泪痕。
“只可惜你父亲那里要伤伤脑筋,”锁锁歉意地说:“美金暴起,我劝老太太趁好价放手,不知她肯不肯。”
南孙说;“那是她的棺材本。”
“南孙,我知道你脾气,但或许你可以找章安仁谈谈。”
“这一提,”南孙黯然,“我在他们家再难抬头。”
朱锁锁“嗤”一声笑出来,“书读的多了,人就迂腐,你看得起你自己就好,管谁看不起你,肯帮固然好,不帮拉倒。”
这一番话说得黑是黑,白是白,刮辣松脆,绝非普通女子可以讲得出来。
锁锁随即给南孙留个面子,“当然,我是江湖客,身份不同,为着方便行事,细节条款一节蠲免。”
南孙觉得这次真得硬着头皮上。
“说些开心的事,南孙,你开听听,胎儿开始踢动。”
南孙轻轻把耳朵贴着锁锁腹部,猛不防一下颇为强烈的震动,吓得她跳起来。
锁锁大笑。
南孙略觉松弛。
到了中午,事情急转直下。
南孙正在啃三文治,章安仁忽然推门进来,本来伏在桌上休息的女同事只得避出去。
南孙还来不及开口,小章已在她面前坐下,劈头便说:“你父亲问我们借钱,你可知道?”
南孙呆了,他声音中充满蔑视、鄙夷,以及愤怒。她认为他至少应该表示同情关心,了解一下事实。
“他怎么可以上门来借?我们根本同他不熟,南孙,你应当说说他,他这样做,会连累到你,还有,影响到我,我父母为这件事很不愉快,你父亲太胆大妄为了。”
听到这样的话,南孙只觉浑身发麻,隔了很久,胸口才有一点暖和,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地问:“那你们借还是不借?”
章安仁飞快地答:“家父即时告诉他爱莫能助。”像是对他父亲的英明决定十分满意。
“这么说来,既然一点损失也没有,何必大兴问罪之师?”
小章一呆。
“是他不好,他对朋友估计错误,我父亲是一个略为天真的人,有时想法十分幼稚,情多多包涵。”
小章犹自咬住不放,“可是他……”
不知是什么地方来的气力,南孙“霍”一声站起来,拉开事务所玻璃门,“我们要办公了。”
章安仁瞪大眼睛,“这是你的态度?我们五年的交情,就因为借贷不遂……”
南孙没有再听下去,她的双耳已经停止操作,只看见章安仁嘴唇动了一会二,怒气冲冲地走掉。
南孙精疲力竭坐下来,伏在办公桌上,她愿意哭,但不知恁地,浑身水分像是已被残酷现实榨干,一点儿眼泪也无。
回到家中,朱锁锁先到了。
谁是朋友谁不是,一目了然,但南孙觉得无人有资格叫朋友两肋插刀,更加心如刀割。
只听得老太太开口说:“朱小姐,施比受有福,这次实在多亏你。”
还是由祖母出来主持大局,姜是老的辣。
她说下去:“没想到南孙招待你几个月,为我们带来一位大恩人。”
锁锁听不下去,“老太太,这只是一项投资,任何生意都要冒风险,我们说别的吧,南孙回来,我同她聊聊,你也要休息了。”
南孙看着母亲扶老太太进房。
蒋先生把握机会发作,“南孙,这些年来,你原来没有带眼识人,你知道章家怎么抢白我?”
他滔滔不绝开始倾诉其不愉快的经验,说到激动之处,大力拍这大腿桌子,面皮胀得像紫姜,连脖子都红壮起来,额角青筋涌现。
把他一番话浓缩,不外是慨叹不幸生了一个蠢女,白陪人玩了这么久,要紧关头,不见半点好处,他不敢怪旁人,只是这个女儿未免也太令他失望。
南孙待他讲完,喝茶解渴时,才站起来离开现场。
锁锁知道她脾气,也不安慰她。
过了很久,她轻轻自嘲:“猪八戒照镜子,两边不是人。”
锁锁却只问:“老太太今天吃什么宵夜?偷些出来。”
只有她,天掉下来当被子盖,是应该这样。
“现在可上了岸了。”南孙说。
“你想听我的烦恼?别后悔啊。”锁锁笑吟吟。
南孙看着她:“朱锁锁,我爱你。”
美元升到一元对九元八角港元的时候,人人抢购,老太太却全部卖掉,用来替儿子赎身。
押出去的房子早已到期,银行限他们一个月内搬出,蒋先生终于崩溃下来,号啕大哭,家里三代女人,只能呆呆地看着他。
南孙收拾杂物,其中有章安仁的球拍、外套、零零碎碎的东西,光明正大打电话叫他来取回,几次留言,如同石沉大海,分明避而不见。
南孙觉得她父亲说得对,世上不是没有情深如海的男人,她没有本事,一个也逮不到。
一颗心从那个时候开始灰。
也有点明白,为何阿姨情愿一个人与一条狗同住。
南孙双目中再也没有锐气,嘴角老挂着一个恍惚的微笑,这种略为厌世的,无可奈何的神情,感动不少异性,生意上往来的老中青男人,都喜欢蒋南孙,她多多少少得到一些方便。
南孙知道,命运大手开始把她推向阿姨那条路走。
也不是一条坏路,虽然寂寞清苦,但是高贵。
南孙把家里的情形写了封长信,大约有短篇小说长短,寄去给阿姨。
她盼望有回音,但是没有。
蒋太太知道了,同南孙说:“我们没有为她做过什么,故此也不能期望什么,她只得她自己,小心点是应该的,与其作出空泛的应允,不如保持缄默。”
南孙恨母亲,因为她不恨任何人。
她千方百计找出理由替人开脱,每个人都有不得已的苦衷,都有委屈,独独轮到她自己的时候,一点借口都没有了。
当下南孙说:“不会的,阿姨断然不会撇下我们。”蒋太太不出声,但是这下南孙却看对了人,阿姨没有回信,是因为她已动身回来。
南孙接到电话,她已在酒店里,两母女赶去同她会面,酒店房门一开南孙又闻到那股英国烟草混着玲兰香味的特殊气息。
阿姨身上大衣还未除下,她站在窗前,黑色打扮使她看上去孤傲、高贵、冷僻。
“南孙。”她张开双手。
南孙熬到这样一刻,眼泪汩汩涌出,抬不起头来。
阿姨简单地说:“我来带你们母女走。”
蒋太太问:“他们呢?”
“他们是谁?”
“我的丈夫,我的婆婆。”
阿姨沉默一会儿,“我帮不了他们。”
蒋太太不出声,坐下来。
阿姨问:“你还没有受够?”
蒋太太凄然地,用一只手不住抚摸另一只手臂,像是怕冷。
“那样的一家人,你还想留下来?”
蒋太太不愿意作答。
阿姨仰起头,轻轻冷笑一声。
终于,蒋太太用细微的声音说:“我不能在此刻离开他,我们曾经有过好时光,现在他需要我。”
阿姨说:“他一生中从没扮演过丈夫的角色,他是你的大儿子,你一辈子宝贵的时光精血,就是用来服侍照顾他。”
蒋太太忽然笑了。
过一会儿她说:“是我情愿的。”
“你这可怜的女人,南孙,”她转过头来,“你马上跟我走。”
南孙吞一口涏沫。
阿姨鹰般目光注视她,讪笑起来,“你也挨义气?”
蒋太太连忙说:“南孙,你要走的话尽管走,家里的事,也搞的七七八八了。”
南孙缓缓摇头,“现在还不是时候,父母皆要我照顾。”
阿姨不置信地看着她们母女,隔了一会儿她说:“好,好。”
南孙有点歉意。
“蒋某是个幸运的人。”阿姨说。
蒋太太对她说:“我知道你看不起他,但他不是一个坏人,这些年来,也只有他给过我一点点安慰。”
阿姨走到窗口,背着南孙母女,唏嘘地说:“我细微我也可以那么说。”
南孙忍不住在心中加一句,我也是。
“那我这趟是白来了。”
“不不不不不,”南孙回复一点神采,“我们需要你支持。”
“你们要搬到什么地方去?”
南孙答:“我的家。”
“有多大?”
南孙用手指做个豆腐干样子。
“一家四口,熬得下去吗?”
南孙摊摊手。
蒋太太长长叹了口气。
阿姨背着南孙,把一个装着现钞的信封递给姐姐。
“有什么事,同我联络。”
阿姨来了又去了。
蒋家搬到南孙狭窄的小公寓,家私杂物丢了十之八九,仍然无法安置。
老太太有十来只自内地带出来的老皮箱子,年纪肯鼻笛南孙大,一只不肯丢掉,里面装的东西,包括五十年前的褂袍,三十年前照相架子,二十年前的皮草……
南孙趁老太太往礼拜堂,花了好几百块钱,雇人抬走扔掉。
老太太回来,骂个贼死,咒的南孙几乎没即时罚落十八层地狱。
锁锁本想帮蒋家弄个舒服点的地方,被南孙铁青着面孔坚拒。
欠朱锁锁一辈子也够了,三辈子未免离谱。
上房让出来给祖母,父母占一间,南孙只得睡沙发,厅堂窄小,只能摆两座沙发,南孙每夜蜷腿睡,朱锁锁看了大怒,问她苦肉计施给啥人看。
最大的难题是厨房,每日要做出三顿饭菜来,一煎一炒,满屋子是烟,渐渐人人身上一股油烟味,个个似灶火丫头。
蒋先生喃喃自语:“献世,献世。”
蒋太太自然戒掉麻将牌,成日张罗吃,蓬头垢面之余,和乐观地说:“他会习惯的。”
蒋先生没有习惯。
事发时南孙在公司里,前一日比较忙,她搭了床在办公室胡乱睡了几个小时,一清早电话响,她以为锁锁生养了,满心喜悦接过听筒。
电话是母亲打来的。
蒋先生在浴室滑了一跤,昏迷不醒,已送到医院。
南孙赶着去,只见父亲躺在病床上,面孔似蜡像。
发生得太快,祖孙都来不及悲恸,似别人的事,新闻看得多,知道确有这种悲剧,但震惊过度,又得忙着应变,竟无人哭天喊地。
三日后,蒋氏死于脑溢血。
同事帮了南孙好大的忙,连日奔走,南孙没把事情告诉锁锁,怕她担心。
日以继夜,南孙咬紧牙关


![[网王]岁月如歌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2/234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