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御医作者:舞绫飞雪-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聪明的孩子。「杜衡,你说说看呢?」
提到「临」字,杜衡第一个蹦到脑海里的是「君临天下」,但即便对得宠的皇子而言此名也未免太过霸气张扬,几可招致祸端。除此以外便是──
「回夫子,」杜衡站起身乖巧的一拱小手,道:「学生记得《古今乐录》有言道『洛阳之水,其色苍苍。祠祭大泽,倏忽南临。洛滨醊祷,色连三光。』讲秦始皇祠祭洛水出现吉兆天宝,此处『临』有天降吉兆的意味,不知和六皇子之名有无关联?」
听闻此言,秃半截几乎想要慨叹了。这杜衡不过一个七岁小娃便有如此心智学识,长大不知会怎生了得。只怕是……比那六皇子也不差。
他点点头:「不错,这『临』字取的正是天降吉兆之意。据说六皇子诞生之时紫云笼罩天际,连日骤雪都停了片刻,华荣宫顶上镶嵌的宝珠流光闪耀,泛出异彩。」
「还紫云呢,这麽神奇?」、「假的嘛,怎麽可能!」孩子们你一嘴我一嘴又热闹的议论开了。
「传有道士说此子乃灵宝天尊的白玉如意转世下凡,所以民间都称他为『白玉天家郎』。圣上信道,以此子为道尊恩赐,象征我朝百代盛世,宠爱非常。」秃半截捋捋下颌几根草似的胡须:「这六皇子也确是人中龙凤,才四岁的年纪据说就能背诵道经和德经,相貌更比道观里老君座前的护法童子还要端正,极为聪明伶俐……」
玉如意转世下凡?杜衡抿嘴笑了,神话志怪之类的书他看得多了,却不信道也不信神。上清灵宝天尊是三清尊神之一,传说纳玉晨之精气,九庆之紫烟育形为人,总是手持一柄镶金嵌碧的白玉如意。那如意虽美也不过是块石头,若真能化身为人杜衡倒想见识见识。可若说四岁便会背道经,实是不简单,那东西乏味又晦涩,他都没能记得很熟悉。
那天晚上,杜衡做了个梦,梦里一个全身玉白,小手小脚嫩如藕段的娃儿,坐在莲花池里对他笑。醒来时好像听到那孩子叫了声他的名字,却是记不真切了。
那之後过了四年,杜衡已辗转两所书院,而秃半截口中集万千宠爱於一身的华妃也殁了。
父亲原本便是少言寡语的人,这势头日甚一日,近来常入夜了才满身酒气的回家。虽然他每天都很疲惫,眸子却越发凌厉,那野心勃勃又充满疑虑惊怕的神情让杜衡觉得陌生而疏远。
从母亲那杜衡听说了父亲即将被任命为六皇子主治太医的事,据说会官进两阶升为左院判,旨意不日就会下了。
「下月和为父进宫受赏吧。」一天用晚饭时,杜廷修突然对杜衡说道:「我想让你习医,去太医院和主事大臣打好招呼,入官学就容易了。」
不止杜衡,两个哥哥还有三房妻妾都惊呆了。杜衡只道父亲对自己并无偏爱,从未料到竟想让他继承衣钵。莫非,他知道自己偷看了书房里的医书?
「父亲,您、您要让三弟……」一向沈不住气的大哥杜睿撂下筷子便喊了出声。他说过很多次想要习医,但从没得到过父亲肯定的回答。
见杜衡呆愣著没回话,杜廷修问道:「你们三个说说看,『风』为何?」
风?一下子,刚才还气势汹汹的长子和满脸愤懑的次子都不说话了。好半晌,次子杜钧犹豫著开口道:「是指风邪吧,还是伤寒?」
杜廷修没点头也没摇头,只看向小儿子。杜衡为难了好久,还是回答了:「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有言,风者,乃八方之虚风也。八方之风,皆能为邪。人以身内血气为正,外风气为邪。凡癞病,皆是恶风及犯触忌害得之。」
「你如何看?」杜廷修面上仍旧淡淡的,在座诸人却被方才杜衡那番听不懂的话惊呆了。
「言过其实罢了。」杜衡拧著眉头说得认真,语气里透出十分的笃定与自信:「风是四时之气,分布八方,主长养万物。患病岂会都由风邪引起?五藏处於内而气行於外,反是心藏神主血脉,心为手少阴之经,心气血气两虚时最易生病,但主导病因需分内外。血系亲族多人罹患同一病症者众,可见并非单是受了邪风的害。」
好半晌的静默,一向不苟言笑的杜廷修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两个哥哥露出得意神色,听他说得头头是道,还不是满口胡言贻笑大方?
不多时,杜廷修敛起笑容,庄肃道:「这番话,不要再在人前说。想进官家地方安身立命绝不可挑战经典。但你说的没错,我从医二十余年才敢得出你方才言论。」
「习医吧。」最後,杜廷修只是这麽说道。
临入宫前两天却生了变故。那天傍晚杜衡正在院子池塘边喂金鱼,就见父亲满脸忧怖的走过来,看了他良久,才开口。
「好好念书,参加文试。十一岁还太小,四年後那届就去吧。是你的话定能给杜家光耀门楣,位列三甲也不出奇。」杜廷修用手拂去飘落在杜衡肩头的柳叶,苍白的面庞似隐忍著很大苦楚:「不要习医,过安心的日子。」
杜衡不知道发生了什麽,但他原本并没执著要做御医,便点点头。事後听母亲说,那天父亲正式升为了六皇子的主治太医,去东篱宫为他诊病开了方。
就是那个玉如意转世下凡的小皇子啊,想起梦中嬉戏莲叶间白玉似的孩子,杜衡微微笑起。突然很想见他一面,不知真人怎生模样,父亲一个字也不曾提到过。
自那之後又是四载光阴疾如逝水,礼部流出消息已内定取杜衡为新科状元,一石激起千层浪,年仅十五岁的惊世英才名动朝野。彼时正逢腊月新年,昭贵妃於华荣宫广宴百官,杜衡也被指名在内。
皇宫果然是赊丽繁华到极致,雕梁画栋,朱漆顶檐,幽深曲折的长廊稍不留神便会迷了路。华荣宫中歌舞管弦片时不歇,喧嚣直入尘上。大臣们寒暄客套满脸的喜悦热络,眼中却个个透出虚伪的算计与防备。不停有人凑过来给父亲敬酒道喜,说些虎父无犬子、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之类真真假假难於分辨的恭维话。
真是个可怕的地方,而且,好冷。
杜衡揉搓著有些笑木的脸,借了出恭的由头溜了出来。要到哪儿去呢?这偌大的皇宫里,想去的地方想见的人只有一个。不知他现在醒著还是睡著,又在做些什麽呢?东篱宫中……应该比较暖和吧?
进宫大半天,杜衡第一次发自真心绽出抹笑来。
连续三天两夜,崇临的病却反复难愈。人不曾醒来,烧得迷迷糊糊,不时喘咳著,药吃不进,水也喝不下。杜衡衣不解带守在病榻前,为他施针、更换额上湿帕,已是两夜未合眼了。
「爷,觉不睡,饭总得吃啊。」小荻捧著碗饭好说歹说才劝得自家爷动动筷子,但没吃两口又撂下了。
外边天色已渐暗沈,执事太监开始在阶兰宫各处廊檐掌灯,猩红灯光透进窗纸,屋内一瞬间仿佛浸染了血的殷红。
「快入夜了,点上灯烛吧。还有,你该去睡了。」杜衡疲惫得连笑容都难以撑持。
小荻拿他没办法,点燃了烛台又仔细关好门窗,便拉著小安到隔壁偏房去休息。临走时小安回头看了眼,那杜太医的手又不安分的抚上了主子的脸,指尖动作却放得极轻柔。这三天来,几乎没见他的视线从主子身上移开过。
小安这辈子自是没福分谈情说爱,但想象著再恩爱的情侣也不过如此吧。跟随崇临这几年,小安自认很了解杜太医是个怎样的家夥,凌傲不逊、目中无人,风流浪荡,缺点怎麽都数不完。主子也极讨厌他,平日相处表面平静暗潮汹涌。但这两天见到的杜太医,真是他所熟悉的那个人吗?想到主子昏倒前还拼命叮嘱不要他来为自己诊病,小安都不由觉得好一阵酸楚。
「崇临,你什麽时候才会醒?」看著病榻上越发苍白的脸,杜衡心中只浮现出『药石枉救』四个字。这样的病势,若持续昏迷不醒,恐有性命之危。
──为何总皱著眉头,做了什麽噩梦吗?
杜衡抚平崇临眉间的褶皱,紧了紧被盖,发现他的左手不知何时露在了外面,便轻轻执起想放回被子里。
「啊!这伤是?!」杜衡惊得叫出声来。
崇临左手手背上居然有一大片灼伤,似是伤了些日子了。没敷药包扎,泛黑的伤口已在化脓,倔强的不肯结疤,还有血丝渗出。因著他的左手在床里侧又被衣袖遮住,一直都没能发现。这麽重的伤,难怪烧迟迟不退。
小心翼翼清洗了伤口,上药包扎,杜衡面上忧色又重了几分。怎会这麽不懂得照顾自己?到底因何竟伤成这样?现在才处理已经太迟了,丑陋疮疤必会伴随一辈子。
他的左手托著他受伤的左手,两手手心交叠,掌心覆盖和煦的温暖。
杜衡凝视著崇临伤口包裹的纱布发呆,突然脸上传来微热触感。难以置信的抬眸,竟看见床上的人在对著自己笑,目光有些迷离,右手抚上他唇边、面颊青紫的瘀伤,一遍遍,似在描画一般。
「伤了……疼吗?」他轻问,许是太久没说话,声音低哑得几乎听不清。虽然伤的是杜衡,那神色却像疼的是自己,满溢著怜惜。
「啊……不疼了,一点都不疼了。你……疼吗?」下意识握紧崇临灼伤的左手,杜衡颤抖著肩哭了出来,视线也变得模糊。
奇怪,从小就不曾有过哭泣的记忆,但只要遇上这个人,眼泪就好像生长在自己体内,可以源源不竭的打心底眼底涌出。
崇临又笑了,手疲惫的落下,触到杜衡衣襟,撒娇一般紧紧揪住:「我想你。」话音极轻,又低低重复了一遍,「……我好想你。」随後骤然沈入了睡眠,仿佛方才种种都是一场幻梦,只嘴角犹带笑容。
听著胸中响如擂鼓的心跳,杜衡几乎以为自己疯了。探探崇临耳後,烫得要命,烧还未退。他素来面子极薄,便是从前两人交好时也不曾说过如此直白大胆的言语,若非烧得神志不清,怎会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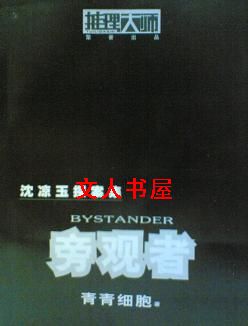



作者:安南一隅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