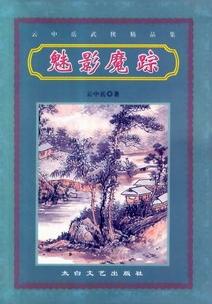九幽魅-第4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出来。清明谷雨一过,白昼明显的长了起来。大家收拾着东西,准备回到石门村去。
这一宿每个人都没有睡好,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家都是睡意全无。樊厨子的伤并不严重,搀扶着就可以行走,我们在镇上一家包子店吃了早饭,三叔找了辆面包车,拉着我们往回走。小车在崎岖的山路上摇晃,颠簸得人心头发毛,我们怕动着樊厨子的伤口,争相的去扶持他。这四个轮胎的铁家伙,机械化的东西,怎么也比得人的两条腿。从罗江镇出发,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回到了石门村。赖端公扶着樊厨子送他回去,莫端公,相木匠和赵矮子三个老头一同走了,说是要去相老头家打长牌。我和三叔同他们告别,径直往家里走去。
老太太不在家,一进屋,三叔就钻到他的暗室里面去了。让我自己看会电视,说他有事情要办。我猜想他这是要去处理伤口,或许还要运转一下内丹通通经络。看了一会电视,肚皮咕噜噜的叫个不停,走了这么多的山路,几个包子如同打了狗,一点也不管用。我跑到厨房去找东西,老太太可能没有料到我们早上要回来,就剩下一碗饭在锅里,桌子上面还有半盘的野葱炒青菜。我不管多少,反正是饿了,囫囵的吞咽着。自己都是二十七岁的人,感觉怎么跟个小孩子一样爱吃剩饭。这四五月的野葱,刚长出来不久,在山里挖来,加一点在菜里,香气扑鼻,味道立马就变了。吃完饭,我又看了一会电视,三叔从里面走了出来,拿着毛巾擦脸,看来他也是饿了,跑到厨房去找吃的。看到没有可以吃的,便生火说要煮点面条吃,我们刚往锅里掺水,老太太就进门来了,问我外面好不好耍,又忙着上来给我们煮面条。
吃完面条,三叔给老太太说我们要去外面办点事情,便提了一个小布袋子,喊我一同往外走。路上他告诉我我们要去樊厨子家,他带了一瓶活血化淤的药丸过去看望,毕竟人家救了他一条命,再怎么也得表示一下谢意。我也觉得应该好好的去看看他,我想如果他不把“五毒肚兜”送给我,或许这次他就不会受伤了。
于是到了村口小卖店的时候,我又买了一袋苹果提在手上。三叔住在村里偏南面,而樊厨子却住在北面伏龙山的脚下,我们基本是对穿了整个村子才到了他住的地方。樊厨子是两代单传,听三叔说他母亲也是个神婆子,不过早死了。他一个人又没有结婚,现在和老父亲相依为命。他家住的房子还是以前祖上留下来的木结构房屋,这种房子在乡下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外表看上去很过时,但住起来却还是舒服的,冬暖夏凉,采光通风也不差。他的父亲,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老汉,忙着把我们引进屋去。
樊厨子半躺在床上歇息,手里拿了一本书,见我们来了,连忙要起身下床,被三叔一把按住,喊他不要起来。通过这些日子的接触,我发现这人虽然模样怪异,脾气却是很好的,心地也善良,知道为别人着想。我们正在闲谈的时候,他父亲提来一竹篮子去年存放的桔子让我们吃,这个月份的桔子,水分少所以很甜,吃在口里也比较化渣。三叔突然喊我出去耍会,他和樊厨子有事情要说。于是我便来到他们家的堂屋,樊老汉在用竹篾条编簸箕,我陪着他瞎聊起来。这老头子看上去很木讷,但一打开话匣子,便滔滔不绝的和我谈论着东西南北。半个多小时过去,我见到三叔大汗淋漓的走了出来,说樊厨子吃了他带来的药,现在睡了,很快就没有事情。樊老汉欢天喜地的道着谢,我们陪他闲聊了一会,便起身告辞。从樊厨子家出来,三叔一直沉默寡言,看样子很累似的。我突然想到他这次可能是给樊厨子治疗来的,刚才在里面一定是关着门运内丹疗伤。我没有问他,我想他想说的,一定会主动的告诉我,不想说的,我又何必去问。
路过我们家老宅的时候,我和三叔偷偷的去土室检查了一下,见里面的油灯还亮着,才放心的离去。我一个人,不想住在这边,吃喝都不方便,也不想住在幺叔家去,不说别的,幺婶那张嘴,是男人都会讨厌,所以我还是喜欢住三叔家去。他没意见,老太太自然的没有话说。
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我又突然的感觉手痒的出奇,原本愈合的伤口,最近总是流淌着黄色的液体,叫人身心都烦。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把手给三叔看,他看了有些吃惊,连忙问我怎么回事情。于是我把被阿黑咬了的经过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他,三叔听完后,沉思了片刻,然后去密室里找了一个小瓷瓶出来,倒出了些黄色的粉末撒在我的伤口上。刚一撒上去,觉得锥心的痛,但很快就过去了,停止了痒,伤口也停止了溃淌。
一连的几天,我都脚不出户的呆在三叔的家里,陪着老太太喂喂鸡鸭,倘若是不看电视,这里仿佛是与世隔绝。城市的喧哗与热闹如同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疲惫的心,最适合在这些地方疗养,但一时间一久了,我想我们恐怕又要向往那些噪音充斥的地方。人啊!天生的就是群居动物。所谓的隐士,那不过也是学着贞女一样的压制摧残着人性,他们骨子深处想要的,并非如此!三叔这两天比较忙,邻村有人建房打地基,他要忙着过去给别人指点。我手背上的这几个黑洞,已经溃烂,不停的渗出来黄色的液体,三叔的药,仿佛一点效果也没有。老姑婆很着急,每天都要熬桑叶艾水给我洗。我嘴里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内心却也觉得烦,别说恶心,光是晚上的痒痛,就让人伤透脑筋。
这天晚上三叔很晚才回来,回来后却又一言不发的坐在那里看电视。我看他的样子,根本就没有关注电视,紧锁的眉头表示他在想着其他的事情。我不知道他怎么了,也不好主动问他,老太太端来饭菜,他说他已经吃了,然后还是一言不发的坐在那里。过了一会,三叔徐徐的说道:
“赵矮子死了。”
我们听后都吃了一惊,忙问着原因,原来中午的时候,相木匠突然给三叔打电话,说赵矮子死了,喊他一同过去看看。于是他约着莫端公,三人一同来到赵矮子的家里,还没有进院子,便听到了哭天呛地的叫唤。赵驼背的尸体停在堂屋的两条长板凳上,白衣白裤的穿着。他脸色有些发白,嘴唇乌黑乌黑的,眼珠子挣得大大的,模样很吓人。一问才知道,前天他出门去临近的几个村卖东西,但昨天晚上没有回来,家人以为他到什么老朋友家住去了,也没有多在意。哪知道今天早上一个熟人来报信,说是离这里十多里的墩子河淹死了一个人,很像是赵矮子。他家人听后惊慌起来,他的儿子连忙赶了过去,果然是赵矮子,已经淹死在河里面了。货物担子已不知道漂到何处去了,河水里四处撒了一些他卖的零碎东西……
“老天爷,墩子河有多深哟!也能把人淹死?”三叔还没有说完,老太太便喊了起来。
“是啊。我们也觉得奇怪,大家都猜测他可能是在哪家熟人的地方酒喝多了,回来不小心跌到河里淹死了。要是清醒的人,就那么一瓢瓜的水,抱鸡婆都淹不死,何况一个大男人!”三叔一说完,老太太又跟着叹息了起来。
我也觉得纳闷,这墩子河的情况我是清楚的。从石门村这里去县城就要经过那里,不过是十来米宽的一条小河罢了,河里的水少的可怜。以前上面并没有桥,为了过河方便,村民们便找来石匠打了些一米多高的石墩子立在河里,行人就采着石凳子过河。我想它的名称可能也是因此而来的,冬季水枯的时候,常常看到些小孩子在里面摸着鱼虾螃蟹。理说这个季节并不是洪水期,河里最深的坑,也不过是一米多的深度,怎么就能淹死一个成年人呢!所以说这赵矮子的死,大家都觉得奇怪。
第二天我和三叔去村口买了一些纸钱,一同去给赵矮子进香。相老头和赵矮子感情最好,他自然要去的,就连樊厨子也去了。他的伤口已经愈合得差不多了,但还是不能使力亲自去操办饮食,只能指点着些农村大妈们办饮食。赵矮子的丧事由莫端公负责,他一个人忙不过来,又带了两个徒弟,一个是赖端公,还有一个年龄不大的男子,我不认识,好象叫狗子什么的,一同在院坝里扎着花圈。
这个亡人躺在堂屋的棺材内,挣开的眼珠子已经被人抹得微闭了,嘴巴半张,露出几颗残缺的牙齿。因为他人的矮小,所以着棺材也不大,比寻常的棺材短了很多。吃完午饭,左邻右舍的人都回家喂养猪牛去了,院子除了死者的亲人朋友,并没有多少人打堆。我觉得没有意思,便起身回去,三叔在忙着帮赵矮子看坟穴,今天恐怕要在这里过夜,我给他打了声招呼,就往石门村走去。
乡村的小路上很静谧,一路走来,偶尔见到一两个老农在田里寻稗草。这些人见你走近,原本躬着的腰身立马直了起来,对着你打量半天,诧异的目光如同要透视你的身子,让你有一种在台上唱戏被人时刻盯着的感觉。只是我不是演员,不喜欢这样被人莫名其妙的观望,于是底下头,急冲冲的顾着赶路。
乡下人见到城里人,就如同城里人见到外国人一样,尽管知道和我们是同类,却也总要拿眼睛扫视一番。这些皮粗肉糙的庄稼人,大多一辈子呆在乡下,所以对于任何的外来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他们的衣着,大多还是六七十年代的款式,一年里换洗的,也就这一两件衣服。这些人,神态胆怯、木讷、俗气、目光无神短浅,言行举止甚至有些粗鄙浅陋。倘若和他们讲话,张口便是喋喋不休却又语无伦次。他们只要一进城,便是城里人鄙夷的对象。西方有位哲人说过,人的容貌,三十岁之前父母负责,三十岁以后自己负责!意思很简单,遗传决定相貌,修养决定气质。老农民和大学教授站在一起,谁是种庄稼的谁是做学问的,傻子都能分辨。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