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油孩子-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级台阶下到第二间厨房,那儿存放着食物,装配得像餐馆的厨房。
在第一间厨房里,西德尼正在阳光中咕哝:〃空调装在小屋,可是住宅里却一个没有。我敢发誓,全都是因为钱。〃
吉丁舔着指尖上的甜汁:〃我喜欢这样。使得夜晚好多了。反正太阳一落下去就凉快了。〃
〃我可是白天干活的,姑娘。〃
〃我也是。〃
〃你还管那个叫干活?〃
〃那是工作。〃
西德尼嘬着牙:〃运动。从杂志上剪下画片。逛商店。〃
〃我还打字,〃她说,〃去商店要乘二十三英里的船,此前还要开车穿过丛林、沼泽……〃
〃你最好别让他听见你把这岛上的什么东西叫做丛林。〃
①法国巴黎的旧王宫,始建于1564年,1871年焚毁后成为花园……译注。〃好吧,他是怎么叫的?杜伊勒利花园①吗?〃
〃你知道他怎么叫的,〃西德尼边说边在背心口袋里找牙签,〃十字树林。〃〃我希望他错了。〃吉丁大笑着说。
昂丁进来了,跨了几级台阶有点一瘸一拐,还皱起了眉头。〃这房子里有些东西喜欢又苦又甜的巧克力。我有六块八盎司的巧克力,现在只有两块了。〃
〃是老鼠吗?〃西德尼问道。他的样子挺关心。斯特利特先生和其他几家人凑钱买了猫鼬,用船运到岛上,以消灭蛇和老鼠。
〃要是老鼠会叠包装纸,那就不是老鼠了。〃
〃嗯,那又是谁呢?全岛不超过十五个人。瓦特一家已经走了;希鲁顿一家也走了。〃西德尼说。
〃也许是丢维尔那边新来的人吧。我听说又都用上菲律宾人了。一共四个。〃
〃算啦,纳纳丁。他们干吗要走那么远的路到这儿来偷一块巧克力呢?〃她甥女在手指上转着一只餐巾环。
昂丁往一只深平底锅里倒了一点水,放进一方块巧克力。〃唉,反正有人。还不光是巧克力呢。还有伊维昂牌矿泉水呢。半箱都没了。〃
〃准是勤杂工,〃西德尼说,〃要不就是这里的某个土著女孩。〃
〃不可能。勤杂工不会走进宅子,除非我跟在他身后,而那些土著女孩,我是不会让她们进到屏风门之内的。〃
〃你不知道的,昂丁,〃西德尼说,〃你不是每分钟都在这儿。〃
〃我就是知道,我了解我的厨房,比对我的脸还清楚。〃
吉丁解开了她的三角背心的绒绳,扇着脖颈,〃哈,我来告诉你吧,你的脸可比你的厨房好看。〃
昂丁笑了:〃瞧瞧谁在说话。是给凯伦公司当模特的姑娘。〃
〃是卡伦,纳纳丁,不是凯伦。〃
〃管它呢。我的脸可没印在巴黎的每本杂志里。你的才是呢。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了。让那些白人姑娘都不见了。从杂志上不见了。〃她把牛奶搅进巧克力糊,笑着说,〃你妈会爱看那个呢。〃
〃你觉得你还会再干那一行吗?〃西德尼问她。
〃也许吧,不过一次就够了。我现在想做自己的生意了。〃
他们又一次看着,脸上放着兴奋的光彩。昂丁端过巧克力,放到桌上。她摸着吉丁的头发,柔声对她说:〃你还会离开我们吗,宝贝?你是我们的惟一了。〃
〃奶昔?〃吉丁笑着问道,〃有奶昔吗?〃
昂丁在电冰箱中找奶油,而西德尼和吉丁则转向窗口,因为他们听到砾石小路上有脚步声。
每逢星期六,勤杂工都会用自己的桨划着自己那艘船头上印着褪色的蓝字〃法国价值〃号的泥色小艇独自过来。今天是星期六,又没有晚餐聚会和特殊工作,他就没有带上一个当地女人……用西德尼的话说,那女人可能是他老婆、他妈妈、他女儿、他姐妹、他情妇、他婶婶,甚至他的隔壁邻居。那女人在住十字树林的人们的眼中每次都稍有不同,只是那顶嘉宝①的帽子始终如一。他们把那女人一概称作〃玛丽〃,而且绝不会叫错,因为这岛上凡是受洗的黑人妇女都叫玛丽。偶尔一次,勤杂工也会带来一个骨骼瘦小的女孩。根据她选择的给眼睛化妆的方式来判断,她可能是十四岁,也许是二十岁。
①葛丽泰·嘉宝(1905…1990),美国著名女影星……译注。西德尼会乘威利斯吉普到小码头上去,把全船的人都接上,一言不发地驶过美丽的平川,然后穿过〃夜胸〃……基德维沼泽,因为他宁肯由他妻子对他们发号施令。勤杂工有时会大着胆子评论上一两句,但玛丽和小骨骼的女孩从来不说一句话。她们只是安静地坐在吉普车里,用头发遮着脸,躲开凶狠的陌生人的目光。西德尼可能保持一种高雅的沉默,但昂丁却对他们说个不停。勤杂工回答她,而〃玛丽〃除去在逼得太紧的时候用法语说一声〃是,夫人〃之外,则从不吭声。昂丁接连在几个月内想找个肯干室内杂活的玛丽,却未能成功。既没有明确的拒绝,也没有一般性的解释,每个玛丽都把土豆、锅、纸袋和削皮刀拿到户外,就是厨房门外的院子里去干活。这事让昂丁恼火,因为这样一来,院子看着脏脏的没有特色了。但是在她的坚持下勤杂工带来另一个玛丽时,那个玛丽还是拿着虾桶到屋外去剥皮、抽线。其中一个甚至拖着熨衣板和一篮衬衫到外面去熨烫。昂丁让她把东西全都拿回屋里,从那以后,她们便到法兰西王后岛上与细布衣服一起熨亚麻布衣服了。
不过,勤杂工倒是很随和。他不仅在城里为他们跑腿,还在家里清扫、拖地、剪枝、修花、移植、搬石、拖走落叶败枝、喷水、栽桩,以及擦洗窗户、整修瓦片、平整路面、装锁、抓老鼠……总之是各种杂活。专业维修工一年来两次。他们是四个年轻人和一个年纪大些的,都是白人,乘着一艘工具船来。他们清理下水道,磨地板并打蜡,擦洗墙面和屋瓦,检查管道和线路,给百叶窗上漆和封装,清理明沟和出水口。单单从岛上十五户人家赚的钱就足以使他们的生意兴旺发达了,何况他们在一年之内还要为其他私有和半私有的小岛干活,所以能够在法兰西王后岛上驾驶着奔驰车或雅玛哈摩托车到处跑。
第一部分第10节:提及火鸡
此时,三个人全都望着窗外那个老年人,仿佛他们要用自己的眼睛从他的眼中发现对巧克力和瓶装水的难以遏制的渴望。勤杂工的面孔没什么可欣赏的,但他的牙齿却令人赏心悦目,不但如玉石般洁白,还像药店里摆的牙齿模型那样排列整齐。
昂丁大声叹了口气,向门口走去。她巴不得他识字,那样的话,她就不必把需要干的杂活的清单背上三遍以防他忘掉了:一只红色的脚锁箱,一瓶玛洛克斯,圣诞树,萨洛迈德,取下砖头……但她觉得要是提及火鸡,简直该挨骂。
○第二章与《堂吉诃德》同归森林■第二章
一个睡人的宅子既封闭着又敞开着。如同耳朵似的,可以抵制轻易的穿透,却无法应付攻击。在加勒比地区是同样没有恐惧可言的。盯视睡眠人的没有眼眶的眼睛是算不上威胁的……那不过是一种警觉,这是随便哪个人都清楚的,因为那样的眼睛没有眼睑,而且不会放大或缩小。在加勒比,没人谈起弦月或半月。月亮总是圆的。总在漂泊和好奇。月亮对它看到的东西从不惊异,更绝不厌烦:一对结了婚的仆人背对背睡觉。男人不穿睡衣只穿睡裤来抵御热气;他妻子则穿着高级密布衣裤,连脖子都不露,表示对热气毫不在乎。他们的后背里有安全感。双方觉得到对方散出的体温,知道只要转过身去,就是其配偶的稳定又能干的脊柱所在之处。所以他们的睡眠是平静的,相互支持的,不像楼上那个穿着一身棉布睡衣裤的老人的睡眠。他白天在花房不时打盹,以致晚上难以入睡。有时他需要半球形杯的白兰地才能成眠,即使如此,他仍会成夜地闲言碎语;先是对着手腕悄悄聊天,然后把听到的消息需要说出的再告诉天花板。一旦他说痛快了……用词准确,甚至拼出了一些关键词……就会像个可爱的小男孩一样兴高采烈,轻声发笑。睡在另一间卧室的妻子已经小心地爬上楼梯走上床,她拿着装好并锁上的行李箱来到门边:她的指甲已涂过油,皮肤轻轻擦过油,头发卡好,牙也刷过了……满口牙齿都闪光而整齐。她的呼吸依然很快,因为她刚刚做完十二分钟的加拿大空军的体操。后来她的呼吸减缓了,在她的睡觉面罩下是紧贴眼皮的两颗在榛壳中泡湿的棉球。她对睡觉抱着很大希望,因为今晚她可能会做个该做的梦。由一扇门相联的她的卧室的隔壁(她已有一年没在这栋宅子中居住,特意选了一间客房而非主人的卧室供她自己使用),一个年仅二十五岁的年轻女人还大睁着眼。又是这样。她刚躺下时立即就睡着了,但一小时后就被梦中的一顶大帽子惊醒,一下子明明白白的了。那是女式的漂亮的大帽子,就是诺尔玛·谢拉、梅·威斯特和简妮特·麦克唐纳戴的那种,尽管她年纪太轻,没看过她们演的电影,即使看过,也不会记得。羽毛。面罩。花朵。檐是扁平的,下垂的,卷起的和圆的。那些帽子一阵飘忽忽后包围了她,把她惊醒了。她躺在那里,上面是月亮的目光,不明白那些帽子何以对她如此不耻和拒斥。她刚刚不再寻觅恐惧的中心,便又想起了并非梦境的另一个画面。两个月之前在巴黎,有一天她去买吃的。那是她一生中的一个最幸福的日子……天气十分晴和,又有好消息,她决定办个聚会来庆贺一番。她给她喜欢的所有的人还有一些不太喜欢的人都打了电话,然后驾车一路驶向十九区的那家超市。她的清单上列出的东西一定应有尽有,而且不必考虑替代品和折中物。格雷少校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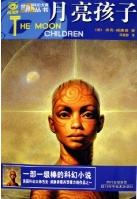



![[综]熊孩子的熊爸妈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6/6158.jpg)
![[综]熊孩子拯救世界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8/827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