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油孩子-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玛格丽特既没有做梦也没有睡熟,尽管偷窥她面孔的月亮相信她已入睡,她正经历着失眠症的可怕折磨……没有醒来,却在本属睡眠的地方充满了些单调的念头。破烂布头,堵下水管的布和团皱的纸餐巾。旧日的悲伤和窘迫,嫉妒与冒犯。都是些不光彩的片断,既没有深到会梦见,也没有浅到会忘却。不过她还抱着仍能入睡的希望,可能会做该做的梦,或许可以借以驱散她忘记东西的名称及用途时折磨着她的偶尔的失忆症状。那种症状多半发生在吃饭的时候,若干年前有一次她用公主牌电话时她手拿着听筒还有她的汽车钥匙和通讯录,却想把这些东西全都塞进她的钱包。这种情况很少,但那种受惊的阴沉感觉却足以持续好久。与朋友共进午餐后,你可能走进女卫生间,把唇膏从管中旋出来,却突然想不出那是用来舔的还是写名字的。而由于你从不知晓这种毛病什么时候会犯,就总感到有一种淡淡的恐惧纠缠着你……只有睡眠中除外。可是这位美妇带着平和及希望的脸蛋,却遗传自两个长相平常的人:约瑟夫和利昂诺拉罗迪,他们曾经用惊奇的目光看着他们的漂亮的红发孩子。当然没想过通奸(利昂诺拉在六十岁以后才让人们看到她光着腿),但那头发使乔乔为约瑟夫的昵称。心烦……在餐桌上吸引了他的目光,结果连饭也吃不好。他看着小玛格丽特的皮肤像知更鸟的蛋壳一样细润,简直有些发蓝,便搓起大拇指。利昂诺拉耸耸肩,用比缅因州的历史还要古老的缎带罩着头。她和丈夫一样不解,但没有那么大惊小怪,虽说在九点半的弥撒时看着有点可笑:玛格丽特的头在她的其余孩子煤黑的头巾间如余火般闪光。她解释不出原因,也不想解释,但乔却不停地搓拇指,一边盯着他小女儿男孩般蓝的眼睛。他把拇指搓来搓去,直到用拳头猛敲太阳穴,一下子想起来布法罗。住在布法罗的姑太太塞莱斯蒂娜和艾丽莎……有着藏红色头发和北方人白皮肤的一对双胞胎。他大呼小叫,开始对人讲他那对布法罗的姑太太,其实从他六岁起就再没见过她们了。在他提及她们时,虽说他的兄弟们连连高声称是,但他觉得他从朋友们的眼光中看出了怀疑。于是他动手接二连三地写信到布法罗,邀请那对双胞胎姑太太到南苏珊娜来。她们接到他的信受宠若惊,但对于这位已经记不起的曾侄孙的突发的亲情不明所以。在一年之中,她们都借口年事已高没有来访,直到乔提出由他来付公共汽车费。〃在哪儿?〃利昂诺拉问道,〃让她们睡在哪儿?〃而乔则扳起手指:阿道尔夫、坎皮、埃斯特拉、塞萨尔尼克、努齐奥、米克莉娜或任何散居在县境之内的罗迪家人。利昂诺拉抬起她罩着比缅因还老的缎带的头,看着天花板,随后便去望弥撒,求圣母保佑她家里平安。
姑太太们来了,乔到车站接她们的时候看到藏红花色的头发已经变成了大蒜色,就又敲起自己的太阳穴。不过,寥胜于无的是,他在众人面前款待她们时提起她们失去了火红的头发,她们笑着承认,当然已经没有了……这就足以向大家证实,那样的发色和那样的皮肤曾经一度存在,因此经过四代之后在玛格丽特·莱诺尔的小脑袋上再现,完全是正统的。在她身上仍然留下了痕迹……有那样的颜色才那样漂亮。布法罗的姑太太们回家之后,乔和利昂诺拉便不再理会她了。或许是她的美貌让他们有点畏惧;或许他们只是觉得,唉,至少她还长得漂亮。用不着为她担心了。他们退在一旁由她去了。他们对她照顾,但收回了目不转睛的盯视。他们把力气花在不漂亮的别的子女身上;他们已有的知识和消息不再只给这个漂亮孩子了。他们把知识存储下来分给了那些需要培养性格的孩子。他们把余下的精力用来解决在一个不想收留他们的县境内生存的问题上。在土地开冻之后的月份里,乔和他的兄弟们在地上打了一个洞。他们用煤渣块砌墙,封顶,设了一个厕所和一条煤气管道。罗迪家人一点一点地从院子对面的拖车中搬进煤渣围墙的地窖中。考虑到缅因的冬天之酷寒,全家人挤在里面就算相当暖和了。随后,乔又起造第一层的墙壁,到一九三五年,一家六口已经住在罗迪兄弟们用自己的双手建起的七间屋的住房里了。利昂诺拉把拖车租了出去,但是留下了后院种植她不分季节都喜欢的辣椒、玉米、大倭瓜和耧斗菜。但玛格丽特总对那拖车情有独钟,因为她觉得那里的隔断有较少的生长空间。在徒手建造的住宅中,以及后来在切斯塔街上的大砖房里,在她父亲和叔父们购进两部卡车成立了罗迪兄弟公司之后,孤独感只在叔父们和姑婶们的眼神中部分地流露了出来。而大部分孤独感则存在于利昂诺拉和约瑟夫·罗迪的头脑中(并非心灵中)而难以接近。因此在她高中毕业八个月后出嫁时,她已经不必离家,她早就走了;她不必离开家人;他们早已撇下了她。除去她给他们的财礼和简短的电话,她仍是离家在外的。事情始终是这样:她离家出走,而别人则待在他们所属的地方。她在上下楼梯;而别人似乎却固定在什么地方了。她在拖车的两级水泥台阶上;在手建的住宅的六级木梯上;在被戴上美女桂冠时,她在运动场的三十七级看台阶梯上;在瓦利连·斯特利特住宅极宽的台阶上。她幸运地爱上并嫁给了一个拥有比她的小学还大的住宅的男人。那栋住宅有三层,到处都有珠灰色的代表姓氏字头的S字母……杯子上、托盘上、玻璃杯上、银器上,甚至在他们的床上。当她和瓦利连舒适地躺在床上,面面相觑,脚趾相触时,被子折边和枕套上的珠灰色S字母环绕着她,使她像电影《蝴蝶梦》中的琼·方丹一样感到窒息。直到她听丈夫说,他的前妻与此无关,是他祖母制作了一些花押字母,并由他母亲把剩下的完成的,玛格丽特这才感到踏实。但当他不在这栋空旷的大宅子里,只有一对黑人夫妇满脸不友好地服伺她时,她仍无法摆脱那种被淹没的感觉。独处宅中时,窥视一个房间,看来还可以,但就在她转身的瞬间,却听到身后有隆隆声,而她又能对谁讲这些呢?当然不能对那两个黑人说。她只有十七岁,甚至不能像主妇那样吩咐他们。她想,大概像是客房服务吧,于是就叫他们把她的东西拿进来,他们照做了,但在她喝着可口可乐说谢谢时,他们偷偷地笑了,这让她很恼恨。那个叫昂丁的女人做饭和打扫;那男人也干,还要在早晨陪瓦利连聊天,掸刷他的衣服,送一些去洗衣店,送一些去干洗店,有些也就彻底不见了。在家里她无事可做,只有在孤寂中自娱,这已经够糟的了,而与瓦利连的朋友一起吃饭就更糟了。在那种场合,男人们谈论音乐、金钱和马歇尔计划(二战后美国支持欧洲的一项计划)。她对这些都一无所知,但她从不傻到假装她懂或者想加入谈话。太太们围着这些题目的外圈聊着,或者插进去说两句笑话,就像奶油甜馅煎饼的馅里有了绿斑点。一次,她指给一位太太看楼下的女卫生间,那人问她在哪儿上的学,她说在南苏珊娜。那女人又问那儿有什么。玛格丽特说南苏珊娜高中。那女人对她开怀大笑了好久,然后拍拍玛格丽特的肚子:〃上班去吧,快点,亲爱的。〃
第一部分第14节:喜惧参半
玛格丽特的生活就是由瓦利连带她去听音乐会,两个人去饭店就餐,甚至独自在家待着。要不就是孤身独处,由着那对黑人夫妇神秘地在宅子里飘来飘去。在她婚后第四个月里,她坐在了纱门的前廊里听《寻找明白》,这时昂丁拿着一罐亚麻子油走过,说道:〃劳您驾,他们已经抓住琼·巴伦了吗?〃玛格丽特答说还没有,但应该就要下手了。〃噢,〃昂丁说着,便开始给她提供一系列人物的情况。玛格丽特虽然不是乖乖地听人叙说的人,但在昂丁面前却是例外,于是主仆之间的友情便发展起来。玛格丽特不再害怕了(不过又过了一些时候西德尼才在面前毕恭毕敬)。她期待着与昂丁的聊天。昂丁的头发当时还是漆黑的,用她的话说,每月做一次。她们谈论瓦利连的家庭,南苏珊娜和巴尔的摩,那是昂丁的家乡。昂丁正要示范给她怎么做干面包片(当时玛格丽特已经知道这是一种荣幸,因为昂丁不喜欢和别人分享她的烹调秘方或者厨房的地盘),瓦利连却打断了,说是她应该指导仆人,而不是与他们做伴。你知道,下一件事就是和她们一起去看电影,这句话大大伤害了玛特丽特,因为和昂丁一起看一场电影确实是她的想法。夫妻俩为此吵了一架。倒不是因为玛格丽特认为瓦利连不对:她从不了解他是什么人,而且不相信他可能会在什么地方出错。他无可指责,就凭他那双平和的眼睛或者又干脆又平静的嗓音……同时让你既放心又开心。虽然她在争辩中防卫的主题是,昂丁(即使不是所有的黑人)和他们这些做主人的一样好,可她自己却不自信,何况那反正不是分歧的焦点。瓦利连对昂丁或西德尼从不粗暴,事实上他还惯着他们。不,焦点不在于与黑人为伍,而在于她的无知和她的血统。那是一场令人生厌的争吵,是他俩第一次彼此说了些悔恨的话,结果是夜里脚趾不相触碰。这可把玛格丽特吓坏了……害怕可能失去他。虽说她放弃了看电影的想法,而且还在下午偷偷溜进昂丁的厨房,但她接受那位夫人在卫生间给她的忠告,〃上班去吧,快点。〃孩子出生以后,一切都改变了,只是那个身后的隆隆声却越来越大了,甚至在她抱着孩子穿过房间时,只要她一转身,背后就出现那隆隆声响。用带孩子走上那些宽大和如同键盘的白亮台阶来教他数数真是喜惧参半。一、二、三……他的小手握在她的手中,一边登上一级级梯面,一边重复着那些数目。没人会相信她爱他。没人会相信她是《国家调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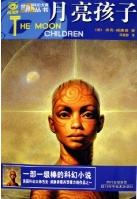



![[综]熊孩子的熊爸妈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6/6158.jpg)
![[综]熊孩子拯救世界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8/827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