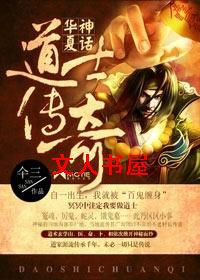王石:道路与梦想-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衩捉⒚梗蟛糠质呛玫模褪欠⒚沟囊部梢晕褂恪3杀炯�4万块,起价2万块,有人要吗?”没人应价。“1万8。”“3 000。”一位鱼塘佬举手应价。
“你说的是美金吧?”众笑。
“1万7”,我故作镇静,心口却一阵痉挛,好似被捅了一刀。
“1万6”,我仍固执地每一叫价只降低1 000块钱。
“5 000”,第二个应价。叫价应价几轮下来,30吨玉米1万2成交,相当于每吨400块。接着第二堆、第三堆、第四堆……
下午接着一堆一堆拍卖,拍卖一直持续到夕阳染红笋岗北站,那似乎是鲜血的颜色……
一天下来,拍卖出400吨,明天继续淌血,无论如何后天要清理干净仓库和站台。
当天晚上,东门宿舍来了几位不速之客。自报是深圳华侨光明农场的,听说这里有大量便宜的玉米出手。来主介绍:光明农场饲养奶牛,为香港维它奶提供鲜奶,价钱合适,数量不限,希望有长期合作关系。“每吨700元,全部扫光。怎么样,王经理?”
“这是卖麻袋!你们是趁火打劫呀。”我脸上很不情愿的样子,心里却盘算着:同鱼塘佬接受的价格相比,每吨多卖了300块,仅此一项,少损失近100万元。问题是从未同光明农场打过交道,是实盘吗?
“OK!”我伸出手表示接受买价。
第二天,聚集在笋岗北站的鱼塘老板们得知没有便宜玉米拍卖了,痛心得直嘬牙花子。
港人不吃鸡,我就认栽!
整个一役下来,赔了110万,把白手起家赚的40万搭进去,还有负资产70万。只要供货方催逼货款,我随时可能破产。怎么办?
足足睡了24小时。我起来打点行装,踏上北去的火车,再从广州搭上飞大连的航班,找到大连粮油进出口公司,询问对方还有多少库存玉米?
“1。5万吨。”
“全收了,我派船,在当地港口交货,付款条件是到达目的地深圳蛇口100天再付。”我清楚,外贸急于出手积压的库存,再苛刻的条件也会接受。第二站天津,第三站青岛,把外贸库存的玉米全买下来,总共3万多吨。
我不相信香港人从此之后不再吃鸡。只要吃鸡就得养鸡,就得消耗大量的玉米,而玉米只有我王石手中有现货。现在谁都不要玉米,市场价是最低的。问题的要点不在香港人是否吃鸡,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要点是,香港人什么时候开始吃鸡?如果玉米运到深圳,香港人还没有唤起吃鸡的热情,就会造成更大量的玉米积压;如果玉米到了深圳100天后香港人仍然固执地“以鸽代鸡”,那我只有彻底认输。
第一条万吨散装船在大连装载了7 000吨玉米,启程经渤海过黄海向南海驶过来。随着海轮距深圳的路程缩短,我也开始紧张起来,天天盯着报纸电视,“香港人啊,你们吃鸡啊吃鸡啊……”
1983年的夏天,台风来得特别频繁。7 000吨玉米船却没有误期,按时抵达南海海域,并向珠江口进发。
还没有香港人开始吃鸡的消息,7 000吨的玉米船却距离深圳越来越近。夜深人静,我在莫扎特《弥撒曲》声中默念:台风啊,南海的台风,你刮吧,刮吧,阻滞这条船,最好能把它打沉。反正船运合同保了自然灾害险。
差两天,7 000吨船就要停靠蛇口赤湾码头了。香港报纸刊登了一条消息:之前的报道有误,饲料中不存在致癌物质。
这消息如同及时雨!香港人再次开始享受吃白斩鸡、盐鸡的快乐!
来到皇岗村,找到发仔,预订20台8吨翻斗卡车,装卸7 000吨玉米。
来到赤湾港。我站在一个高台上。看着万吨巨轮耸立眼前,载重翻斗车一辆接一辆。起重门吊上的吊网一兜是8吨玉米包,轻轻抓起,滑轮滑动到停车的位置,一松网兜,100多包玉米落进翻斗,卡车启动,后面一辆轰隆隆补上位等待装包。向正大康地、远东金钱驶去的装载卡车队掀起尘烟滚滚。我双手叉腰仰望天空,天空是那么的蓝,云朵是那么的白……
第二役,我不仅补回赔掉的钱,还赚了300多万元。
玉米变成了金豆子。深圳的许多企业纷纷派业务员到北方收购玉米。来自北方的玉米从港口、铁路、公路源源流入深圳,流入珠江三角洲。蛇口港露天货场堆满了玉米包,还有大大小小待卸的玉米船。供需失衡,11月份,玉米真的过剩了。
此时,特发贸易部升格为贸易公司,原来贸易一科孵化出单璇领导的医疗器械科、张西甫任科长的科学仪器科,饲料组跟着水涨船高也升格为饲料科。
某天一上班,我被陆总一个电话叫进他的办公室。
“怎么回事?”编辑出身的陆总将一摞报纸递过来。
我瞥了一眼手中的《深圳特区报》,一篇评论员文章在赫然的位置,批评特区企业盲目进玉米造成的大量积压和浪费,还点了特发贸易公司的名。进陆总办公室之前我已经看到这篇评论。
“什么怎么回事?”我平静地反问。
“大量积压玉米损失严重,尤其是特发贸易部在蛇口码头的积压,一上班孙总就交代秘书追问此事,要我立即写出书面材料。这篓子捅大了。”
“蛇口码头积压玉米?不知道啊。”
“都上报啦,还打马虎眼。我现在就去蛇口,你跟我一起去!”
去就去。
坐上陆总的丰田皇冠,风驰般到了蛇口码头。
好家伙,满眼全都是帆布盖着的玉米堆。玉米垛的上部被帆布遮盖得严严实实,下部分露出一溜黄麻袋,因为潮湿和气温,玉米发出的嫩芽已经顽强地钻出麻袋缝隙,齐唰唰蹿出绿油油的玉米苗。
指着玉米苗,这位当年东江纵队的红小鬼发火了:“你如何解释?”
我只是淡淡说了句“这不是我的”,心里却有种莫名快感。
“那是谁的?”
“现在几乎所有的公司都在买进玉米,不大清楚是哪家的。饲料科已经停止从北方进货一个月了。我们现在的做法是拉着正大康地的买手在珠三角采购现货,中间倒一下手,赚得少一些,但是没有风险。”
“为什么正大康地不直接自己做?”
“相信王石嘛。这种做法符合‘走正道、靠大树、傍财神’的九字经。”
“咳,呵呵……”陆总眉头舒展,开心地笑了。
小小的风波过去了。饲料生意的前景引起陆总的关注,他在特发公司的办公会议上建议成立饲料公司。
此时,我已在激流勇退。我不认为饲料行业在中国能够成为一个有前途的行业,见好就收吧。我的兴趣转移到科学仪器科,协助西甫做电脑、复印机进口业务。
我退出饲料行业5年之后,1989年,四川新津的刘永行、刘永好几兄弟决定进入饲料行业。到90年代中期,刘氏兄弟的希望集团成为仅次于泰国正大集团的大陆第二大饲料生产厂家,亦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
我曾同刘永行、刘永好先生半开玩笑地说:“如果当年坚持做饲料生意,中国的饲料大王应该是我啊。”其实,放弃饲料业务,除了不看好饲料行业的前景外,还觉得这门生意风险大利润薄,忒辛苦。然而,刘氏兄弟顺应饲料行业兴起的大势,兴趣不在“买卖”的倒货盈利上,而是脚踏实地建起饲料厂,并凭着走实业的道路成为90年代民营企业的佼佼者。
小平访问深圳的那一年
1984年1月24日。
我骑着自行车从特发总部出来返东门。途经国贸大厦:警车、警察,还有聚集的人群。这情形引起了我的好奇。人群中晃动着一个高个头的身形……那不是特发的高林副总经理吗?便凑前问:“什么事情啊?”
高林把我招呼到一边,低声说:“小平同志在深圳。市委通知清理现场,准备让中央首长到国贸顶层俯瞰特区全貌。我正在陪公安局的同志检查安全措施。小王,不要对外说啊。”
“噢。”我继续骑上自行车返回东门。
几天后,《深圳特区报》头版报道:邓小平在王震、杨尚昆等中央首长陪同下首次视察深圳,受到特区建设者的热烈欢迎。视察中,邓小平听取了深圳市委领导的汇报,登上20层高的国际商业大厦,眺望正在建设中的新城区市容,参观了一家电子厂,访问了渔民村,了解企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的确,短短几年里,深圳已由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了有40万人的新型中等城市。
特区经济蒸蒸日上,孙凯峰、高林率领的特发集团功不可没。从西部宝安县城进入管理线开始,路边的加油站,蛇口的赤湾码头,进入市区前的香蜜湖度假村,特区第一座高尔夫球场,东门老街开发的新华城、水贝工业区,沿盘山公路绕到沙头角、小梅沙度假村,一路向东直至出二线关口的背山面海陵园都和特发有关系,可谓业务无所不包。
不甘特发之后的市属企业还有深圳贸易进出口集团、深圳进出口贸易服务集团、深圳友谊集团、深圳免税公司、深圳物资总公司。
按照特区政策,进口特区的国外产品不能销售到特区外,但不限制特区外客户在特区内购买的商品运出特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应运而生。
1984年5月,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筹建,选址在建设路1号,展销进口办公设备、视频器材。由陈露任经理,蔡作幸任副经理。陈露女士是“文革”前的大学生,与先生一起从韶关移民深圳,外贸业务能力强,性格倔强,筹建还不到一个月,在展厅的装修风格上她就同我争执起来。两人互不相让,争着争着,陈露从经理椅站起来,将一串钥匙往桌子上一放,“经理我不当了!”推门走了。
第二天,张西甫找到我摊开双手,“彻底撂挑子了,怎么办?同陆经理商量了,你当法人代表。”
“我属于省外经委的人,帮忙筹办没有问题,但是兼任经理就涉及到了分成问题。”
“饲料科的利润分成不变,展销中心广东省外经委不用投一分钱,三七成,但亏损也要按比例分担,怎么样?”
“很合理啊,我马上向省里汇报。”
然而省外经委的主管领导另有考虑,认为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