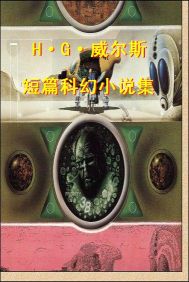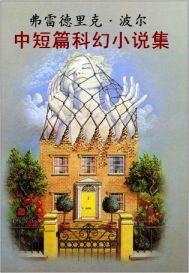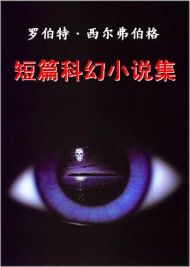小说月报 2013年第10期-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下偎到了“见风倒”的怀里,羊高高地抬起了头。
我们一齐伏在沙子上,抬眼去看——沙地上的月光像浅浅流水,使人觉得有无数小鱼在上面游动,如果有一只大水鸟来啄食一点都不奇怪——正这样想着,真的有一只大鸟来了!瞧它两只又粗又壮的长腿吧,吧哒吧哒踩着浅水,得意洋洋地来了!
虎头躺在旁边,我能感到他激动得全身打颤。我大气不喘,顺着那只“涉禽”——书上这样叫它们——往上看,刚刚定神就惊得闭不上嘴了!老天爷啊,这哪里是什么大鸟啊,这家伙长得多怪啊,它像人一样长了两条腿,可是上半身又像鸟,因为有双翅;不过双翅上方有窄窄的肩膀,有脖子,上面长了比常人略小一些的头颅……我紧紧盯着,发现它有一张小娃娃似的小圆脸,额头可真不小,鼓着,大眼睛上方是一溜整齐的刘海……
“见风倒”呼一下坐起,他大概吓坏了。这人又一次被证明有点痴,因为他竟然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暴露了自己。
结果糟透了——那个怪物听到声音立刻止步,圆脸一抖一缩,瞬间缩成了拳头那么大。接着双翅一张,几乎毫无声息地飘离了地面——我敢说自己盯得仔细,那简直不是飞,而是像跳高运动员那样轻轻一弹,就稳稳地落在了一棵大树梢顶上。它只在这棵树梢停留了一秒,又连弹几次,在几棵大树上方选择一圈,最终不知落在哪一棵上了。
我们一起追寻,可惜连个影子都没有发现。正在我们发呆的时候,园子深处却传来了嘻嘻的声音。这种细小的发声以前听过,那显然是对我们的嘲弄,而且分明透着得意。
大家争论这是一种什么动物,争执最大的是走兽还是飞禽,因为这是不可混淆的一个原则。谁也无法作出结论。统一的看法是,这不是一般的大鸟,因为它有人一样的头脸,似乎还有手。不过它离地的那一刻又像鸟——好像它的双臂随时都可以当成一对翅膀来用。
“见风倒”只是听着我们的议论,并不加入讨论。他在月光明亮的夜晚敞着怀,露着一只大肚脐,长了鳞的脖颈就像胳膊一样细。我这会儿有一个奇怪的念头,觉得这个护园人也是一个妖怪。
我们身边这个“妖怪”的不同之处,是一点都不让人恐惧。他和我们躺在一起,无论是在沙滩树下还是在小土屋里,时不时就要紧紧地搂一下左右的人,包括猫和羊。有时候他真是激动啊,紧绷着嘴,猛地一下咧开又像要哭出来。我知道他是激动了。我心里承认,他是最能激动的一个人。关于他的身世没人了解,只知道他是一个身带重病的人,随时都能离开人世。就是说我们面前的这个嘴唇发青的细高个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在一阵风里倒下,然后再也不会爬起来。
大概由于时时面对死亡,所以他才有那样阴沉的神色,他害怕啊,他不高兴啊。也同样因为这个,他才要紧紧地搂住我们,那是他舍不得与我们分别啊。我发现每一次大家离开时,他都要狠狠地盯一会儿——不是恨我们,而是恨又剩下了独自一人。
老万说“见风倒”所有的亲人都因为害心口痛过世了,只剩下这根独苗,“独苗命苦,人长得痴,娶不上媳妇。”他警觉地盯我一眼,接着说,“小心一点吧!”
我问为什么?
“不为什么,反正小心一点吧!”老万不怀好意地笑,往地上吐口水,“这是个不男不女的东西。”
我立刻争辩:“不,他是男子汉,这是真的。”
老万摇头:“什么男子汉,一个废人。打鱼不行,推车不行,护园子也不行——有一年秋天被几个偷苹果的老娘儿们按住打了一顿,还把他的裤子脱下来扔到了树上。那天正好起风了,他吓得跌跌撞撞往回跑,光着腚,鞋子也掉了。”
我可怜起小土屋里的人了。
一连好多天,我一想起老万的话就为护园人难过。我和伙伴们更多地去园子里,带去好吃的东西。当然,我们最好奇的还是那个来去无踪的妖怪。
秋天来了,果子挂在树上,不久就要成熟了。半熟的果子格外馋人。
小双和虎头都发现,随着果子一天天长大,“见风倒”就变得不那么友好了。这家伙的一对眼睛泛着瓷亮,就像鱼眼,这是大家刚刚发现的。鱼眼圆圆的,很拗,一动不动地盯过来,会让人心慌。
我们爬树时,他一定要上前拦住,还扳锈住的枪栓。这家伙吃了我们多少巧饼和花生,一转眼就翻脸不认人了。他大概担心我们将果子碰掉。其实我们想摘下果子。杏子和苹果只有指甲大时就吞下肚了,它们真酸。不过对付再酸的果子都有办法,那就是嚼的时候闭上右眼,这样也就可以忍得住了。
而“见风倒”闭上一只眼睛时,那就是在端枪瞄准。树上的鸟、爬到树上的猫,被他瞄住时全不介意,因为它们都知道这是一支放不响的枪。
如果不能爬树,只在地上呆着,那就没有多少意思了。一年里,除了北风呼啸的冬天,我们一直在树上攀爬,摘果子逮鸟,闭着眼想心事,这些都要在树上才行。“见风倒”终于露出了护园人的本来面目,他原来像那个传说中的老哑巴和矮子一样,天生就是我们的对头。他竟然用枪向我们瞄准,这是多么可怕啊,这枪如果能够打响,他真的敢扣响扳机吗?
果子眼看熟了,满园香气让人心痒,鼻子发酸,走路就像坐船——飘飘悠悠的。一开始我还以为只有自己这样,问了问小双和虎头,他们也差不多。只要我们进了园子,“见风倒”就会跟上,寸步不离。他解溲的时候我们就往林子深处钻,这时他就提着裤子追赶。
虎头有一次背着手走出林子,可能藏了什么,“见风倒”转到身后,虎头就随着他打旋。虎头越旋越快,弄得“见风倒”头晕,一下栽倒在沙地上。我们趁机爬到树上,每人都找到了最甜的果子。
起风的日子最好了,这时候护园人就不敢走出小土屋了,只趴着北窗往外瞭望。可惜有时风刮起来,却偏偏不是星期天;放学回家了,风又停下来。
老万从园边走过时身上背个帆布褡子,看到“见风倒”过来,就让我们往另一边跑。我们后面紧跟着“见风倒”,那边的老万就动手摘果子,直到把布褡子装满。
我们从园里跑出来,在通海小路上与老万会合时,他正笑嘻嘻地啃果子。可是这家伙太吝啬了,每人只分给一个苹果,而且还专挑小的。他咔嚓咔嚓咬着大苹果,果汁四溅,说:“对付这家伙还不容易?赶明儿让海上渔老大娶了去。”
我们都不吃苹果了,盯着老万。
老万吃过苹果又抽烟,两撇黄胡须翘起来:“海上老大早没老伴了,正找家口哩,我看‘见风倒’就合适。”
小双惊呼:“可他是个男的啊!”
老万笑了:“我们老大是女的,这不正好吗?”
海上老大是指挥打鱼的把头,怎么会是女的?这玩笑开得也太大了。我们全都不信。老万使劲吸一口烟说:“老大过去是男的,他天天喝酒,天天喝,一天这个数儿,”他伸出三根手指,“三碗。这就喝死了。老大没了,打鱼的就得散摊子,因为大伙儿谁的话也不听,只听老大的。上级一看实在没辙,就让老大家里那个老娘儿们来管咱们了。”
虎头听得入迷,头快探到老万怀里了。老万用烟卷火头触一下虎头的鼻子,虎头猛地缩回来。老万继续说:“这娘儿们比我还高,腰粗肚大,大脚丫子跺地噗哧噗哧响,还会抽烟,喝酒也在这个数儿上。”老万又伸出了三根手指。
大家哄笑。
“你们也不用笑。俺们那一伙都听她的,为啥哩?就因为她是师母辈的,等着我们孝敬她哩。她辈分高,可惜年纪不太大,也就四十一二岁吧。夜里她和大伙一块儿挤在渔铺里睡,当老大嘛,就得和大伙同吃同住。半夜里她一声连一声叹气,坐起又趴下,一双大手捂着胸口。开头大伙以为她病了,心口疼,后来才知道是另一回事。”
老万说到这里卖个关子,不吭声了。
我们都急了,逼他快说怎么回事?他又吃苹果又抽烟,半晌才说下去:“老大是想师傅了,想重新找一个男人过日子。本来这事儿好办,睡在一个铺子里的打鱼人这么多,可惜不行啊,全都不行!”
“为什么不行?”小双问。
“因为咱一伙里尽管有不少光棍汉,可大伙都叫她老大,她是师母啊!”
这回我们都听懂了。虎头搓手,望向果园的方向。他在想什么。
“如果老大把那个人,”老万夹烟的手往南挥动一下,“把‘见风倒’娶了去,那园里的果子还不成了咱大伙的?咱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可是,可是,”小双像憋气一样,鼻子上出了一层汗粒,“我想他不敢的,不敢的……”
“怎么就不敢了?”老万盯住小双,因为过于专注,似乎有点斗鸡眼。
我替小双答了,说:“那人见风就往屋里跑,胆子特小!”
老万拍掌大笑:“这你们小孩子就不懂了!那是因为他一个人老要闷在屋里,没有摔打出来!只要有了家口,这个人也就‘皮实’了!”
“‘皮实’是什么意思?”虎头问。
“就是耐折腾的意思,”老万扔了烟蒂,“就说我吧,别看娶来的是不男不女的一个物件,几年下来再也不管什么天气——以前不行,淋一场雨就得赶紧喝酒,生怕寒气扎到骨缝里。娶了家口,热汤热水吃喝,身子骨也就壮起来了。男人女人全一样,得有人疼,在他(她)耳朵边哈着气说话,一边说一边用小手摸摸他(她),他就一天天皮实起来了。”
大家都听得出神。我心里想,老万这个人懂得可真多。
最后分手时老万下了决心,说:“这事就这么定了,等个好月亮天,我拉上俺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