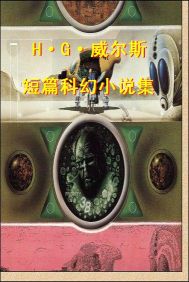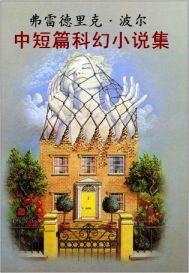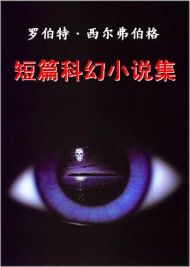小说月报 2013年第10期-第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叫杜月出来,有重要的事告诉她。杜月仍然值班,出不来。我央求,十分钟,就十分钟好吗?我在医院门口等你。没等她再说什么,我把电话挂了。电话里说不清。
杜月很快出来了。保安紧紧盯着我和杜月。我拽杜月往旁边走了数十步。杜月没有我想象得惊喜,眼神反而怪怪的,怎么能这样?我说安定是很普通的药,许多人都吃,除了助眠,还能治疗恐惧。你应该知道呀,再说,又不是天天吃,需要才吃。杜月当然明白需要是什么意思。她思忖一会儿,问,睡着了?我说摇都摇不醒。杜月说,你想过没有,这不是长久的办法。我说总归要试试才知道。杜月忽然往街道对面扫一眼,脸上掠过一丝惊恐,你确信他睡着了?我说我敢保……证,天晓得,我为什么会磕绊一下。鬼使神差地,我如她那样朝对面瞅去。
返回的路上,我不时回头。真被王大乐骗了?药对他不起作用?我的头皮阵阵抽紧。和一个骑三轮车的后生撞上,他倒了,我也倒了。我说着对不起,他还未反应过来,我已经跳开。
王大乐仍在沉睡,仍是那个姿势。我吁口气,给杜月发了信息。一对惊弓之鸟。
我坐在王大乐对面,像画师端详刚刚完成的作品,只是没有得意。我想起几年前看过的一则案子,丈夫借助安眠药谋杀妻子,不是让妻子一次吃掉,而是每天放她水杯里,逐渐加量,不露痕迹。我没有谋杀王大乐的企图,也不会让他每天吃。某个时间段,他必须忘记过去,忘记现在,忘记我。他需要这样,我更需要他这样。我又看看说明书。很多人都在服用,王大乐为什么不可以?或许还有奇迹。王大乐听不到,我必须说服自己。紧张加上隐隐的愧疚,我口干舌燥的。我往前探探,摸摸他光秃的头顶,眼睛湿了。
次日清早,我醒来的同时,王大乐睁开眼。我和他睡的时间不同,但醒的步调一致。我不知他是怎么做到的,这样,他就不必因早醒而打扰我。他服了药,为什么仍然醒得恰到好处?我有些纳闷。我等待他问我,他是怎么到床上去的,他没问。我出门的时候,他还在寻找袜子。我忘记塞哪儿了。
晚上,我又做了一次试验,没有任何问题。
两天后,我在医院附近开了两小时钟点房。杜月甚为紧张。我再三说王大乐睡得正香,她的脸仍是扭向门的方向。我扳过来,她又扭过去。两小时过去,没听到敲门声。
王大乐给我制造的障碍除掉了,至少,暂时不复存在。我和王大乐的关系也得到缓解。我仍然去槐北公园,号叫的力量弱下去许多。这种轻松当然要说带有谋杀意味也未尝不可,能持续多久,我没有想,即使想也没结果。
不是每晚都给王大乐吃,不吃的时候居多。王大乐没什么怀疑,或者怀疑过,但想不到我做了手脚。他的思维终究别于常人,有特别,就有盲点。总之,他没问过。
那个晚上,我把杜月约到租住处。以前,我和她就在这简陋的蜜巢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王大乐睡着了,缩在墙角,像极了一个标本。杜月不敢靠近,似乎王大乐随时会弹起来。为打消杜月的紧张和疑虑,我哼了两支曲子。王大乐纹丝不动,我又朝王大乐脸上吹气,演示给杜月看。我和杜月挣的钱都有限,因为王大乐,额外花了很多钱。这个账,我不说杜月也会算。杜月似乎踏实了一些。我抱着她上床,她的头竭力从我肩膀往后探。我说没事,杜月说感觉王大乐在看。我松开她,拎了毛巾将王大乐的头脸严严实实盖住。杜月问,不会蒙坏吧?我说,怎么可能,又不是湿毛巾,呼吸没有问题。
杜月把裤子拉到一半,可怜兮兮地看着我,就这样吧?我说,这怎么行,你搞得我也紧张了。我要的不是过程,她要的也不是。杜月吃力地拽拽,说什么也不动了。她做着防备,我明白的。我咽口唾沫,没再说什么。杜月挺配合,但我们的动作笨拙而别扭。她的注意力在王大乐那边,我的心思也在他那儿。这样,就彻底变成针对王大乐的试验。
杜月迅速拉起裤子,说对不起。我苦苦一笑。很久,我俩静静坐着,似乎等待王大乐醒来。慢慢地,她的头靠过来,我搂了搂她的腰。再后来,我吻她,几乎同时,我们剥光。
艰难的一步跨过去,后面简单了许多。隔几天,我就把杜月带过来,只是,杜月不能和我住在一起,无论多晚,我都得把她送走。每次进行完秘密活动,我会给王大乐买些好吃的,猪耳、辣鸡翅什么的。有时,杜月也带一些过来。算补偿吧。我不认为是赎罪。我和杜月有什么罪?如果这是罪,那么,王大乐对我做的一切又是什么?我大概知道王大乐对别人做了什么,但不知道别人对王大乐做了什么,又是怎么做的。王大乐变了,原因成谜。
七月的一个晚上,石城闷得几乎不透气,西北的夜空黑沉沉的,似乎要下雨。我接了杜月,中途买了半个西瓜。西瓜像蒸过的蛋,热乎乎的。走了一段,杜月忽然说,卖瓜的没找钱。我问多少,杜月说三块多。我说算了吧。杜月说怎么可以算了?于是,我俩抱着半个西瓜返回去。
那个晚上,我有些兴奋,也有些不安。我准备再次求婚。王大乐不再是障碍,杜月应该没顾虑了吧?至于她的前夫,真的不是问题。一个人是一张纸,俩人合力就是一堵墙。我不知杜月会不会应,脑里反复推敲着要说的话。
王大乐在梦乡中,看不清他的脸。我照例把毛巾搭过去。我想在活动开始前求婚,那样,行动会有不寻常的意义。
杜月说出汗了,让我替她擦背。我一只手擦背,另一只手绕过去攥住她的乳房。杜月说弄疼她了,呻吟着转过来,我迅速抱住她。猝不及防,活动提前了。我没来得及说。王大乐不再是威胁,我和杜月都很放松,当然,也很放肆。
我和杜月躺了一会儿,听到雨滴敲打玻璃的声音。杜月呀一声,我握住她的手,不要紧,咱有伞。杜月说还是早点回去。我鼓捣了一天的话还未说出。我让她稍歇会儿,吃块西瓜。我也想吃,从嗓子眼儿往外干。我跳下地,忽然感觉不对劲儿,愣了愣,目光扑向角落。空空荡荡,王大乐消失了。我有些蒙,慢慢扭转脖子,搜寻所有的角落。没有王大乐的影子。随后,我听到杜月的尖叫。她的目光如我一样惊恐。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无法回答她,我也不知怎么回事。直到杜月提醒,我才些许明白过来,王大乐可能已经离开屋子。我奔到门口,门从外面锁了,拉不开。药失效了,还是王大乐装睡?我想不明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没有沉睡,没有喊。他离开了,无声无息。
我和杜月面面相觑。杜月再次追问怎么回事,我终于清醒。无论怎么回事,当紧的是,必须出去。可是,门反锁着,窗外安着拇指粗的护栏。等待,还是……我和杜月的目光再次聚到一起。雨更大了,我和她蠕着嘴,却听不清彼此说了些什么。
老桂家的鱼
南翔
入冬以后,老桂知晓自己病了,或许,病得不轻。
下半年以来,他就明显感到头晕,全身乏力,身体虚胖。从小船上到大船,原先拽住船柱的绳索,一纵身就能够跃然而上;现在非要等到后头的老伴或者儿子,收拾完鱼舱、渔具,趋前,肩住他的屁股,嘿哟起身,才能将他一身的蠢重,连同喘息一道送上去。老伴已经行年五十有五,早已是一头白发,腰粗如桶,白日劳作一天,夜里鼾声如雷,依然是兴兴头头,甚至,风风火火。越发将萎顿的老桂比得如同霜打的秋茄子,蔫没声响。
一个半百的船上男人,晓得自己得病,还不是体力减了,口味淡了,最早的感觉,是不想吃酒。先前无论早晚,无论寒热,只要擒起那只扁扁的挎了背带的铝酒壶,拧开黑色的塑料盖,一股沁人心脾的酒香就如同馋虫探头探脑,飘逸而出,直接钻进他的肠胃。连带得没酒吃的日子,隔壁船上严瘫子缩在舱里吃酒,他就站在船边,定定吸气,分辨与捕捉在微腥江面上飘散的几丝酒气。
是没吃酒的缘故吗?虚胖的身子却是越发有点畏冷了。岭南的冬天,年终岁尾,早晚有几天扑面的冷峻,哪里就能冷得像模像样!阿勇收了鱼回来,就是一领霸王横条的T恤,额头上还滴滴沁出汗珠子。老伴在船厅,脱下水淋淋的胶鞋,解下一身笨重的雨裤,居然热气氤氲,索性连同一条单裤也剐了,露出两筒滚圆糙白的大腿。
这几天一直将养没去收放渔网的老桂,静静地坐在一张绑了条木腿的塑料藤椅上,借着阳光的熏蒸,驱除彻骨的寒气,那是经年在水上讨营生的积攒吧?瞥见老伴几乎是肆无忌惮地脱了裤子,再脱上衣,一件男式汗衫裹着满怀的肥硕,蹦跳两下便无可奈何地垂了下来。
老桂便把眼睛移开去。
大船十年前就报废了,形同一条废弃不用的趸船泊在岸边。建筑工地陆续偷拣来的竹板、木块,将一家老小的容身之所,隔成饭厅、客厅、厨房和须得低头才能进入的厕所。
都讲女人老得早,老桂没有比她大太多,却是两三年前就独宿了。一是大船空间逼仄,床位紧张;二是老伴越来越肆无忌惮的鼻鼾,常常震得一张马粪纸隔开的儿子、媳妇半夜叹气;还有三,他害怕跟老伴睡在一起,她似有似无的粗糙的撩拨,是一种欲望的无声挑战。
只有蜷缩在小船里。这条小船是十二年前花了八千块买的二手机动船,老桂及儿女一番装饰,长不过三米,宽才可错身的小船,居然钉了一张铭牌,命名“大岭山号”——大岭山是东莞下属的一个镇,是桂家人生的出发地。其实,往祖上讲,他家属于长江两岸迁徙岭南的客家。上个世纪70年代,老桂是上浦人民公社高中毕业的回乡知青,兼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