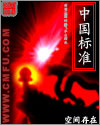剑桥中国明代史-第1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开创东林运动的人是地位低下的年轻官员们。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以这
种身份公然反对皇帝的权威,并因这种反对遭受酷烈的惩罚而赢得了正直的
名声。快到明末时,在押的和被放逐的东林支持者比在职的多。因为他们把
个人品德置于其他一切事物之上,他们也就容易因个人的行为而出名。作为
一个集团,他们逐渐在攻击下互相援助,并在任职时采取一致行动清洗官僚
机构中的他们的敌人。由于这个缘故,对有些人来说,他们显得好争论和起
破坏性作用。张居正预料到他们的敌对行动,于 1579 年 2 月 17 日发布命令
关闭所有私人书院。万历皇帝本人对东林党人强烈反感。当东林支持者的朋
友上疏皇帝为他们辩护时,他照例将给予他们的不重的惩罚改成较重的惩
罚。皇帝一点也不了解,他自己感情上的憎恶有助于激起这场运动的狂潮,
而不是使它平息下去。
东林运动的成员有一种共同的思想上的假定:一个学者-官员真正的毕生
事业是修养他的品性。简洁地表现这种观点的《大学》的教导,在个人道德
和公共道德之间没有做出区分。自我修养始于自心,扩大到家庭,然后到社
会交往,最后到公共事业。这种生活方式由高攀龙(1562—1626 年)作出了
最好的范例。在禅宗式的顿悟中找到一种个人自由(如许多著名的明代新儒
家那样)之后,高从未期待一种平静的退隐生活。几十年中无论在职或去职,
他始终都深深地卷入了北京的朝廷政治斗争中。东林党人在被放逐中从来没
有想组织一个“忠君的反对党”。正是他们被迫去职的事实意味着邪恶势力
在进行统治,他们必须想办法通过谋略和发表议论以“救正”局势和恢复职
位。这种不实际的态度使他们不能被叫做“自由主义者”(他们有时被贴以
这样的标签),当然,他们也不是革命者。
尽管对政府机构中的合乎道德的行为的宣扬代替了任何特定的政治原理
本身,东林运动在比较实际的一些问题上并不是完全没有影响。东林的代言
人有力地说出了关于内阁机构中“擅权”的担扰。徐阶和高拱的不法行为以
及张居正的失败无疑加强了这种确信。为了抵消内阁的权势,他们维护科道
人员的独立性,科道人员能够抑制政府中的编撰-教育人员的势力和吏部的自
主权,并对太监的活动限制在宫廷范围进行检查。从他们的观点看,这些制
约的实现将意味着一种“清明”之治,比较接近于王朝建立时所树立的榜样。
这些改革的方案并不图谋改进帝国行政的体制或改变其权力的结构;它
们完全是以道德的考虑为基础。新近的经验使他们确信,以集权机构(如张
居正当政时的内阁)的命令为基础的行政管理,没有以牺牲正直的人为代价
而使无节操的投机分子得利的卑劣的个人行为,是不能实现的。
他们向往一种组织上松散的政府(具有向皇帝直接报告的各自独立的各
种机关,并具有独立的报告途径),有时达到了不切实际的程度。1583 年,
后来都和东林发生了联系的魏允贞和李三才,冒着触怒皇帝的风险争论说,
应当规定大学士们的儿子没有资格参加文官考试。这个建议的两个发起人想
使内阁这个机构减少吸引力而降低其权势。10 年以后,东林运动的主要创始
人顾宪成(1550—1612 年),作为吏部的高级官员,成功地阻挠了任命一个
翰林学士来领导他自己的部,理由是,所有大学士已是翰林成员,由这样一
个排他的内廷集团控制外廷的一些主要职位将有损于健全的政府的利益。
东林党人保持一种组织相对松散的文职官僚等级制度的倾向,对现代的
读者来说是不易看出的。了解这一点的关键在于这样的事实:16 世纪晚期,
帝国的官僚机构已经用尽它的技术能量通过系统的、有条不紊的方法以解决
行政问题。它对太大的领土和太多的人民负有责任;它的活动太程式化,也
太表面。此外,东林支持者抵制任何基本制度上的或财政上的改革观点:他
们认为技术性的解决办法过去不成功,也不可能成功。因为他们偏爱行政改
革的空想,他们的运动在体制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倒退了一大步,是从高拱
和张居正所采取的立场的重大的退却。
但是在 16 世纪晚期,正统的儒家道德价值具有的吸引力比我们可能或乐
意了解的要大得多。在注重实行方面,它们弥补了体制上的缺陷。孔子本人
曾经详细阐明这样的原则,一个有修养的君子应当为了仁爱随时准备献出生
命。孟子曾经要求个人放弃自身利益以服从公共福利。经史中不懈地提出的、
农村塾师和更高层次的学官不断重复的对于自我牺牲和坚毅的号召,被这些
正统的儒家认为提供了令人畏惧的蓄积起来的精神力量,比任何体制的或正
在使用的力量都强。热心公益的精神,当其由承担了领导任务的学者-官员的
核心指导时,就会做出惊人的成就。它保证黄河溃决的堤堰将被修复,边境
游牧部落的入侵将被击退,无论有无所需的人力和财政资源。在皇帝面前苦
谏的官员们的拚死的正直,是明代所特有的,表明了对人生目的的同样理想
化了的态度。宋代的新儒家学者已经解释过,所有这种道德上的训导和实践
都和他们所认为的天理是一致的。赴义所隐含的吸引力满足了那些东林追随
者,他们喜欢这个在失败和挫折的时代不公正地被迫害的高尚的运动。
此外,儒家对亲属关系和家长权威的崇敬已被吸收进法典,把明代的国
家和社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东林支持者对这些原则的紧密依附,带来了这
样的希望:统治方式的实践和理论彼此可能更接近一些——这种一致是张居
正执政以来所缺少的。地方政府直到这时是作为间接的、防范性的管理机构
而发挥作用。农村精英在引导未受教育的群众在社会习俗的范围内谋生方
面,其有效性对于这种最低限度的管理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样一种体
制下,技术的效力是不相干的;法律和命令必须置根于男人的无上权威、对
长者的尊敬,以及对社会差别的严格遵守。整个行政机构都建立在这些前提
上。当中央政府将其重点转移到征税和刑事诉讼时,它造成了一种不能再被
简单地叫做儒家和法家之间的学术争论的局面;倒不如说是,上层建筑以一
种下部基础不能跟上的方式重新认定它的活动方向。农村村社从来不能提供
所需人员和专门技术的支持来实现像张居正当政时所宣布的那种改革。
张试图严格管理帝国的徒劳无益,东林领袖们甚至在他们把注意力转向
道德和精神问题之前已经预见到。1581 年,当仍在张的管理之下时,户部尚
书张学颜曾上呈皇帝《万历会计录》,这是到那为止关于帝国资源的最全面
的会计概要,编辑这部概要占用了 14 个工作人员,费时两年多。可是它表明,
承认了很多有所改变的财务单位和特殊的会计手续,暴露出可悲的现实,即
整个帝国普遍存在的差异决不可能全部并入一种统一的管理制度。这一著作
的编辑者中有顾宪成、赵南星和李三才,他们当时都是户部资历不深的成员,
但后来都是著名的东林党人。在他们生涯的这样一个早期阶段曾被给予这样
一个少有的观察高层管理的机会,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他们在后来的年代里
行事如此不同。看来他们似乎已经确信,通过抽象的道德劝勉比依靠所有层
次上的查账,更能符合帝国的利益。①
从 1953 年京察到东林书院的建立
研究这段时期的学者面临难以克服的困难,因为这个范围的原始资料都
偏向东林集团。道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同时代作者的观察力,以致他
们的记述变成了为各自的目的而利用事实和争端的评论、辩解和攻击。在这
些记述中能够发现某些错误和矛盾。例如,《实录》无疑认定万历皇帝大约
在 1587 年之前曾试图实施他的个人统治;朝廷那时做出的重大决定都出自他
自己,包括贬谪未来的东林创始人顾宪成在内。但是《明史》却明确地谴责
申时行干了这件事。据说这位大学士让他个人的好恶支配朝廷的选择。
把个人道德等同于行政才能的习惯,由于过分强调官吏的品性而流行开
来。赞成这种看法的较早的历史学家们,倾向于把那些比关心道德的纯洁性
更关心政府正常发挥作用的人评述为品格低下,乃至邪恶和无耻。大学士王
锡爵当他断言后来成为东林集团一个最受尊崇的领导人邹元标是“朴愿书
生,无他奇略”时,无疑损害了他在道德方面的名声。①同样,给事中刘道隆
(1586 年前后)不能洗清他那谄媚者的形象,因为他讥讽地评论说,靠反对
首辅(张居正)可以博得盛名和令誉;靠拥护他,即使他说的只是不加渲染
的实情,也会赢得不朽的恶名。①
当东林运动的成员决意卷入朝廷的人员考核过程时,他们明显地暴露了
他们运动的狭隘而有偏见的性质。他们只希望除去那些在他们心目中品性有
缺陷的官员。张居正早已利用考核过程来实现他的个人目的。1557 年,由于
① 关于鄂尔多斯军事行动的更充分的说明,见阿瑟?N。沃尔德伦:《鄂尔多斯的收复:明代的一次战略争
论》'530'。学位论文,哈佛,1981 年。
① 对这个时期财政管理问题的全面讨论,见黄仁宇:《16 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剑桥,英国,
1974 年),第 44—81 页。
①15世纪期间每石米用银两计算的平均价格在 0。4 至 0。5 两之间。在 16 世纪前半叶,平均价格稍有提高,
约为每石 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