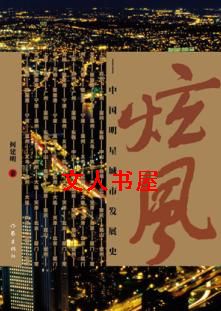炫风-第9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展模式为何如此吻合!
常熟人自然不会想到,或许他们根本就不会这么想、这么比较。但有一点他们应当明白,他们今天在走有自己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探索中,萌生的许多追求、许多举措、许多创新,实质上都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这就是从实际出发,抓住当地当时自身优势,把握机宜,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对自我价值与自我财富及自我发展所抱有的创造天性、本能追求,并使之成为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动力源。
就其形式而言,今天的常熟人与当年工业起步时的英国人在生产力发展现象上十分地相似。但就其本质而言,则十分地不同。当年的英国人运用纺织机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而常熟人运用纺织机则是生产关系出现改变时的一种有序进步。但对两种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同一现象我们可以用同一种结论,那就是不管是昨天的英国人,还是今天的常熟人,他们从自我发展的自我条件出发,同样依靠一台纺织机的最终目的是一样的,即为了改变自己的落后,增加自己的财富,从而实现社会的整体进步。
虽然我们不能预计常熟人今天手擎一台纺织机,是否也能像昨天的英国人一样后来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世界命运那样,激动人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常熟人今天手擎纺织机,终有一天也会让世人所惊叹!事实上,这种强大的工业化、商品化、资源化、财富化、实力化,已经从他们身上显示了出来。只是过去没有人这么讲,没有人这么去想而已。任何一场深刻的革命都是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被人们有所认识。常熟人的经验,或许在更长一些时间后,更能让人从本质上理解和认识到它对我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所起的某种不可小视的影响力。暂时让我放弃这种预言,带着读者们一起去看一看常熟人今天手擎一台纺织机而带来的那场正在涌动的波澜壮阔的革命吧。
常熟这场革命的产生,首先与当年英国工业革命始于棉纺业的历史,有惊人的相似。常熟这个地名始于宋代,当时的官人取名这块“土壤膏沃,岁无水旱”之地为“常熟”,可谓聪明备至。常熟常熟,常种常熟。常熟常熟,种什么熟什么。常熟人富裕首先要感谢先圣虞仲开垦出来的那片让老天爷都无法拒绝不熟的肥沃土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阶段,中国的民族工业开始出现,而早期的中国民族工业,又都以与人们生计十分紧密的日用品工业生产为起点。常熟作为粮棉产地,又近靠上海、苏州等城市,这时期便出现了一批商人到这里办厂的浪潮。如江西籍盐商独资27万两银元,于光绪三十年在常熟支塘镇建的“裕泰纱厂”便是一例。此厂占地200亩,所引进的设备都是1888年英国“道勃生”和“汉斯顿”制造的纺织机,其生产规模在中国早期纺织工业可算非同一般。20世纪20年代,又有一批上海、无锡商人到常熟开厂,形成了常熟纺织工业第二个发展阶段。之后是抗日战争开始,上海、无锡等城市的工厂又为免受日军飞机的轰炸而纷纷搬到离城不远的常熟乡村,这客观上又使常熟纺织工业朝前迈进了一大步。
其实上述原因还远非常熟纺织业发展的根本因素。常熟纺织业之所以今天能成为当地人民走向市场经济的“火车头”,主要还是常熟人自身的条件在起作用。
在常熟的浒浦镇,人们告诉我一个很有点像18世纪中叶的那个发明了“珍妮纺纱机”的大胡子哈格里夫斯式的人物,不过这个人物是位女性,她叫季根仙。不知是因为她的祖先季陵是宋代名将之故,还是她生来就有灵仙之气,父母给她起了如此一个名字。根仙生于1884年,卒于1978年,是位有94岁高龄的老寿星。在她的家乡浒浦镇大居家宅基,乡亲们为她塑了一尊像,这是常熟土地上唯一一尊老乡们自发地为一位平民农妇塑的像。在常熟市内,政府也为季根仙塑过像。这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上点年岁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出口创汇产品中有一样就是在世界手工艺界也享有盛名的“常熟花边”。而中国的“常熟花边”的开山鼻祖,便是季根仙这位活了近一个世纪的农妇。
1919年,家境贫困的青年妇女季根仙去上海徐家汇投亲,经妹夫介绍,受洗礼加入天主教,后跟教堂一位外国修女学手绣花边,时约半年。因季根仙心灵手巧,所绣的花边不但超众,且在工艺上既承外国之技术,又融中国传统手工之精华,在质量上堪称开辟花边之一代先河。后季根仙回故里浒浦便开始以刺绣花边为业,这时总有邻近姑嫂姐妹结群前来观赏。因当时刺绣花边工价较高,且又是手头针线活,学起来也并不费劲,所以每当季根仙做活时就四周拥满学艺者。为了让众农家姐妹们也能学到刺绣花边的技术,次年春,季根仙租下白宕桥居氏一大厅开始正式传授刺绣花边技术兼营发放业务。由于绣花边能使妇女们不仅更加心灵手巧,而且有了一门其收入远超于其他农家副业的本领,所以到季根仙那儿学艺的人蜂拥而至,后又一传十,十传百,到20年代初常熟一带农村,数以千计的农家妇女都学会了“做花边”。妇女们农闲在家做,农忙带到田头做,也可以在给孩子喂奶时剌上几针,也可以在做饭等火时绣上几行。等一张花边做完交活后,就可以换回数元数十元现钱。那些手巧的姑娘们三年五载下来由绣花边得来的私房钱,就足够办嫁妆用的了。刺绣花边的这种效应,使得后来常熟一带的民间流传着一种风俗:哪家的姑娘小姐不会“做花边”,就找不到好的婆家,而“做花边”快的姑娘小姐则当然成了婚嫁娶亲的抢手对象。如此的风俗反过来又大大刺激了花边业的发展。至解放前,常熟的花边商行多达300余家,而在常熟周边的县市也出现了数以百家的花边商行。解放后,由于常熟城内有了独立的花边出口业务,乡乡镇镇也都设立了花边收购发放站,所以农家妇女们的这种手工艺,便完全形成了一种地方产业,县里乡里还办了几家专门的花边厂,“常熟花边”也因此成了国家的一个著名的地方出口产品而享誉世界。
1978年,94岁高龄的“花边皇后”谢世,两年之后由她自成一派的“常熟花边”,荣获国家金质奖。
季根仙的“花边传播现象”,看起来似乎很寻常,其实却深刻地揭示了当地人心灵手巧的天性和特有的商业敏锐性。说到常熟季根仙的“花边现象”,我不能不在这儿说一说常熟市场经济中的另一个独一无二的“小裁缝现象”。所谓的“小裁缝”,在当地是人们对那些靠做衣服为生的手艺人群体的一种称呼。你可千万别小看了常熟“小裁缝”。读者知道北京有个“红都”服装店,它生产中国乃至世界一流的服装。然而“红都”的“第一把剪刀”是谁,也许没有人说得上来。常熟人却可以明白地告诉你:那就是他们的“小裁缝”——田阿桐。
常熟是著名的棉花产区,从明代开始这里就有了农民自产自用的土布纺织业。土布纺织业日趋成熟后,便出现了一大批与木匠、泥瓦匠并称当地“三仙”之一的“小裁缝”。特别是20世纪初至解放后,随着脚踩的“洋机”越来越多地替代手工缝剪之后,江南特别是像常熟这样的棉区,几乎村村有一个或几个这样的小裁缝。在尚未有市场经济时,小裁缝完全是一群个体手工业劳动者,他们靠自己的劳动,走东家串西村地为近邻远亲裁衣缝裤,一天最多能挣得养家糊口的微薄报酬。然而尽管得的是微利,可比起纯靠干农活为生的“田匠”,用今天的话说,那小裁缝就算是“白领人”了。因为他不用晒太阳,不用抓粪灰,而且还能又吃又拿(客家得管饭付工钱)。所以,小裁缝在六七十年代之前的苏南一带非常吃香,不管是男是女,找个小裁缝做对象在当地可算一门“高攀”的亲事了。在这种风俗的影响下,小裁缝就遍地皆是——尽管有的一个月接不上一两桩活,但这并不影响学裁缝这门手艺的人越来越多。然而到了70年代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江南一带广大农民先是有了较好的吃,后来又家家户户住进了楼房。人生“吃、住、穿”三件事,到再后来,穿好就成人们生活中的大事了。于是江南一带的小裁缝,便有了从未有过的大发展和用武之地。
1991年秋,在华东地区爆出了一个令中国纺织业同行们震惊的新闻:常熟小镇王市在自己的小镇上举办了一个“农民时装节”。此事在当时不仅引起国内强烈反响,就连外国数家报纸都相继报道。在人们的印象中,像时装节这样极为高雅的服饰艺术的专业盛会,只有那些高雅人才欣赏得了,非一定水准的大中城市不能举办。那些脚上带泥的“土包子”怎么可能搞这样的活动呢?确实,据说当时有不少人对这样一个几乎全是在种棉花的地里、卖棉花的路上、织棉花做服装的厂里举办由清一色种棉花的人、卖棉花的人、织棉布做服装的人唱主角的“农民时装节”,抱有怀疑。但后来人们发现自己错了,就像上海大明星张瑞芳所说,她开始便是考虑农民兄弟的面子才接受邀请的,可到了常熟王市小镇后这位大明星激动得直掉眼泪。她说她从50年代开始一直演了几十年的农村妇女,以前一演这种角色,导演就让穿有补丁的衣服,好像越破就越像农村妇女似的。可今天到了常熟小镇参加农民时装节一看,她们人人穿得那么漂漂亮亮的,我以后再演农村妇女时就可以对导演说,我也要穿漂漂亮亮的衣服上台了。
王市小镇的时装节如今已办了好几届,且办出了名。费孝通先生曾对小镇时装节给予高度评价,并写下“王市小镇,衣被天下”的题词。说到王市的农民时装节,就不能不说支撑这个时装节的“秋艳”服装了。而今驰名中外的“秋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