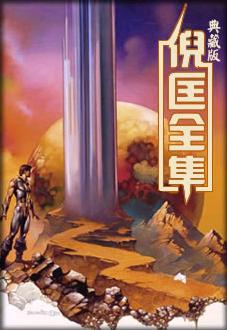梦里废墟-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宣慧好奇的问:“这是什么?”
纯雯将绿芽放在桌中央说:“这是秋天的绿芽”。说着她转问莫桐说:“刚才我们在废墟里游玩那里的景色怎么样?”。
莫桐不明白纯雯为什么会这样问,他就回答:“叶子黄了,花败了,夏未秋初的野外就是这样。”
“是的”纯雯接着说:“这就是快入秋的天气了,漫漫夏季行将结束,万物都在随着季节的转替而变化,对此大家都适应了毫不奇怪,就象对这常见的普通绿芽,谁也不曾在意,但是你们只要把两者联系在一起,就会发现在你们所熟悉的环境中,很难看到常见的绿芽。这就是自然法则的残酷,然而我却在无意间发现竟然有这么一株小草在向它抗争,悄悄的抽出新芽。虽然在风里它是显得那么的弱小无助,瑟瑟而抖但那片绿仍让我心喜不已,就像沙漠中的行人看见绿洲般,一时间让我联想起很多很多-----人要是也能象小草般不断地发出新芽替代已经枯黄的旧叶,不停地从旧的自我中走出来成为新的自我,这就是更实在新生。”
祝牟慈听得纯雯娓娓道完就问:“纯雯这就是你的新生”。
纯雯自信的点点头:“在困境中就是希望,有希望就有一切”。
崔卫回感叹说:“我们都是纸上谈兵,那及得纯雯现身说法的好”。
伊震风说:“是啊!我们几个人都是想摧毁一个,再诞生一个,而纯雯却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出发点以在纯雯之下”。
宣慧拍手笑着说:“我可不想跟纯雯争什么社长不社长的,我只不过也想在这里证明一下我人生观点”。说着她从身后拿出张画纸上面是素描,仍可看见涂改后的草迹。崔卫回朝那画‘噫’了声,宣慧懊恼的望了一下坐在椅子上掩嘴偷笑的崔卫回,说:“我知道你笑什么,我这刚学画的人画的是不太好看。但你毫无理由对一个初学者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更不该把自己的快意放在人家不足之上”。
崔卫回被她一说,张着半开半闭的嘴再也不好意思笑出来,只得老老实实的听她说下去。宣慧把话锋一转:“在这里想告诉你们,那就是我想学画画这并不是我一时心血来潮,早在以前我就很羡慕你们可以将所想所爱的挥豪泼墨于纸,留作日后的纪念,所以心中也希望象你们一样,也许我没有你们对画画那么痴迷,将它视作人生的第二生命,但我只是想能在空闲的时间里,有种可以陶冶情操的娱乐,难道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新生不是指精神上的一种寄托和升华吗,既然如此那我把画画作为点缀个人生活空间的一种方式,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就不强求自己成为毕加索,高更之类的名家,你说是吗?纯雯社长!”她临说完时调皮的向纯雯笑笑。
祝牟慈说;“宣慧的话毫无造作矫饰,坦白真实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伊震风说:“宣慧为我们的笔聊书社锦上添花,我真的很不得有那么个象记载历史的史官般的人,好把我们今天所谈论的一切详详细细的记载下来”。
莫桐接着说:“阿风虽然我们没有给我们写传记的史官,但这里的每一片瓦,每一片砖,每一栋梁和楼外的山风修竹青天白云都会欣然作证,有我们这一群人曾经谈论过一个这么有趣的话题……”。
五 小笨伯初登大雅堂 火焚情惊煞众小子
九月莫桐真的进了报社,而纯雯和祝牟慈他们也开学了,并且就在一个班上。莫桐和他们一直遵守着他们六人之间那个神圣的契约,每周在废墟相聚一次。余下的时间就是在报社里和家中。
进入报社后莫桐才发现校对这份工作却是这么的清闲,本来他还担心自己什么也不懂会搞的手忙脚乱的,不想报社里的庄老很是热情的指教他,几乎包揽了他所应作的事情倒让他袖手旁观了起来,报社里两个老头韩有为和莫子琪,一个言语不多,一个整天笑嘻嘻似个小孩般。唯有副社长贾奉贤让他感到生疏,贾奉贤不常对他开口说话,加上他自己又口拙得很。因此两人一天也说不上五六句话,贾奉贤对其他三人倒是健谈的很,但言语间又有一种逼人的锋利,莫桐感觉到其他三人都对贾奉贤有些惧意,言谈之间都不想与他争锋。
这天莫子琪用力地摔了摔手中的钢笔,在纸上写不了几个字又没有墨汁了,心中不由恨起这支笔,他刚好写在兴头上手中的笔却又偏偏不凑巧的断了墨汁。他窝着气狠狠地在纸上写了几个带白痕的字迹,差点把纸面都给戳破了,这才放下笔对着对面的韩有为说:“老韩麻烦你把旁边的墨汁瓶拿过来,韩有为听到叫声一侧首,眼睛从镜片后面瞟了瞟向莫子琪,他有些耳背一下子没有听清莫子琪的话,莫子琪见韩有为这个样子,也只好无可奈何的摇摇头,就用笔尖指了指墨水瓶,另一手指指笔一字一字地说:“我-笔-没有墨汁了,你—给我把墨汁拿来好不好”。
韩有为这才听明白连点点头把墨瓶给移过去,莫子琪把笔帽脱了,注满汁水后把笔从瓶子里取出来,他见笔头还有些汁水沫,便想从前面的那堆本子中撕下张白纸来檫干净。不料刚抬起手,衣袖口却挂在忘了拧盖的墨水瓶上,一用力就带倒了那瓶墨水,顿时黑黑的浓汁从瓶口流出。莫子琪见状大吃一惊忙伸手扶正瓶子,对面的韩有为此刻眼睛却特别的尖,远远的便瞧见一股汁水悄无声息的向自己这边流来,急得也来不及去挪那边上的书本,大叫一声:“喂!老莫你怎么把墨水弄得一桌子都是,还到处流起来。”他这一叫倒让莫子琪更加的慌乱了,两人七手八脚的又要挪东西又要檫桌子,转来转去的忙得团团转。
庄老看见了忍不住的笑出声来,这场面煞是难见,他说:“那里来的水满金山,慌得你们俩象两只螃蟹一样手忙脚乱。”
贾奉贤坐得远远的笑呵呵的看着。莫子琪也不答理,急切间又不敢乱撕纸张,也就顾不得许多了抽出自己的手帕用力的檫桌面,不想那桌面是太滑了手帕一抹东桌面就印出一串向东的墨迹,手帕一抹向西桌面就印出一串向西的墨迹,结果是越檫桌面上的脏迹反而越大了。倒是莫桐想起角落里的废纸篓里有一块海绵,忙取了过来递给莫子琪。莫子琪欢喜得连忙伸手接过将那桌面的水珠一一吸干,弄了好一会儿,韩有为才松了一口气坐在位子上继续手中原先的活,莫子琪却依旧苦着脸,原来他刚才写的稿件已经被墨汁污了一大团,里面的字迹模糊不清,就叹了口气把它扔到纸篓里重新写过。对面的韩有为此时口中还兀自念叨着不停,莫子琪耷拉着脑袋无心搭理他。
庄老就说:“老韩你念叨起来跟老妈妈唱家常一样没完没了”。
贾奉贤见方才的闹戏收场了,也就懒得再评论了什么,他顺手把桌上的一张揉成一团向窗外一扔,恰在这时楼下一声警笛响起来一下又一下。他不由吓了一跳自言自语地开起玩笑来:“莫非我扔的纸团扔到交警的头上不成,怎么会这么巧”。他向窗口一探首一下子被下面的景象给看住了,忙向庄老招手唤道:“庄老你过来看一下,这街上要开车展了”。
庄老也就走到窗口向下一看,果真下面的街面有十几辆小车花花绿绿的挂着彩带,从头接到尾在慢慢的挪动,四周的行人都停下来驻足观看,这人流一停就把各种车辆给塞住了去路,只有少数骑技精湛的年轻人骑着自行车在人群中见缝插针的骑来骑去。韩有为见他们都靠在窗前就问:“是什么东西那么好看,把你们都给吸引住了”。庄老返回位子说:“也不知是谁家死了人,还是在娶亲,办的排场好大有那么多的公家车在街游行”。
贾奉贤说:“庄老好没有水平,这肯定是迎亲的如果是送葬的队伍会有花圈之类的东西”。
韩有为点头说:“看来也应该是迎亲的人家,只是把交通给堵了,不知是车里的人看外面热闹还是路边的人看车里的好奇,唉!人有时也真可笑”。
莫子琪凭着记忆继续写了一会儿,就写不下去不是忘了这个词就是忘了那个字。索性就停下了笔插上话说:“县里不是三申五令的禁止这类游行吗?那一次好象还是胡社亲自主笔写了一篇抨击这种现象的文章”。
贾奉贤嗤笑了声说:“规定是规定,遵不遵守又是一回事,在社会风俗的万有引力影响下,胡社写了一篇文章就可以移风易俗吗!再说能请得来那么多公家车的人家也不是等闲的,哪个警察会发神经真的管起这种事情,就算真计较起来你是扣车还是留人,理论起来还是办事的人缺德,人家娶亲办喜事也要管”。
庄老笑了说:“还是奉贤说得好,分析的精辟,我们国家是的礼仪之邦,每个人都经过几千年文化的熏化都不会做令人令己忌讳的事情,有两句话不是说娶亲和死人的吗----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亲和人死比天大”。
贾奉贤恩恩连声:“到底是庄老多读了几本道家的书,对世情多一份了解”。
莫子琪说:“都有理,就是出风头的人没有理”。
几人谈得热热闹闹,莫桐却一句话也插不上,他坐在角落里又没有事情可干,只好静静地听他们的话声,翻翻手中的旧报纸,渐渐地他觉得自己就象似个隐形人般,空留个人在这里别人却看不见他,而自己却能听见他们在说话,他听久了心里就希望报社楼顶的那个大挂钟能早点响起下班的铃声。
傍晚,张曼文和丈夫,儿子一起用餐时忽然放下筷子叹了口气。胡自牧闻声抬头一看妻子一副孤孤郁郁的样子就问:“你怎么了?是不是今晚的饭菜不合口?”
张曼文摇摇说:“自牧,我想给我们家请个人,你看好不好”。
“请人-----”胡自牧想了下说:“这样也好,省得你忙家里的事情”。
“自牧,我没有那么的娇贵,这个家里的事情也不怎么多,还忙不倒我,我只是想家里能多个人在你们走后,我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