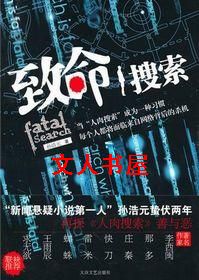致命追杀-第7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们很少交流,倒也相安无事,可是,可是……”
医生的遗孀说到这里浑身颤抖起来,几乎说不下去了,我赶紧安慰她,为她冲了一杯热茶,又用其他问题帮助她放松。过了好一会,她才能继续讲下去。
七
儿子,我在想,如果你长大了,想知道爸爸是什么样的,怎么办呢?我把自己的几根发夹在家庭相片夹,也许等你长大的时候,人们已经可以随意克隆失去的爱人和亲人……
以下是医生的遗孀那天继续告诉我的故事。
“那克隆的婴儿的身体很快发育达到十岁儿童的标准,,我丈夫也就更忙了。那些美国人,也就是中央情报局的人严格规定我的丈夫可以和克隆人讲些什么,不可以讲什么。据我丈夫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已经感觉到中央情报局不是在做医学实验或者想提前取得人类克隆的科学突破这么简单。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让他这个华人和这个克隆人讲什么中文……我丈夫说到这里的时候,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把我吓坏了。他说,那孩子过了十岁后,中央情报局的一些中文专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定时来看他,给他上课,和他交谈,并神秘地把他带出去几天,而我丈夫作为克隆人的医生和他接触时,竟然需要按照中央情报局那些人事先挑选草列的语句一字不差地进行……那克隆孩子很善良,长得也很英俊,但我丈夫心里却越来越不是滋味。因为他感觉到,中央情报局是在把这克隆人有意培养成被克隆人……
“我丈夫解释说,所谓克隆一个人,是从身体上克隆复制,从你的细胞克隆出来的人,长相绝对和你一模一样,就好像照镜子一样。当然在成长的过程中,人的身体因为接触外界的差异,因为锻炼的强度不同,也许生出差异,但这些可以适当调整,甚至通过外科手术调整。然而,有一个难关却无法克服,那就是你可以不折不扣地克隆一个人的身体,却无法复制一个人的大脑。这不是说克隆人和被克隆人的大脑结构有什么不同,实际上,两人的大脑的重量、质量和DNA排列组合完全一样。问题是,大脑的形成是两方面决定的。一是自身细胞构造、DNA排列,所为先天决定;另一种就是接触外界受到影响,受到不同教育等形成的不同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大脑才可以思考。如果克隆一个人,这个克隆人长大后,只要有一些经历和被克隆人有所不同,那么他们的大脑所想所思就可能千差万别,判若两人。我丈夫说,这才是克隆技术永远无法克服的难关。否则,爱因斯坦的大脑现在还完整地保存在那里,为什么不早克隆,让他为人类继续做贡献?”所以,当我丈夫看出中央情报局克隆这个人的目的是为了制造一个和被克隆的人一样的人时,心中的不安更甚。但他能够干什么呢?那神秘人显然是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级别的高官,当时找他的时候,就明确说过,这是为了美国国家利益,为了世界和平,为了……好在这时,那孩子也渐渐长大,我丈夫就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那孩子身上,他想,只要不是克隆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这样的人间魔鬼,一个被克隆的个体又能干什么呢?何况眼前的孩子很面善,于是他乘机和那个孩子多交谈几句,当然都得小心翼翼,那孩子是在完全与世隔绝的透明房间里生活,二十四小时几乎都有七八个人在同时观察他、研究他。我丈夫感到浑身不舒服。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那孩子生活在无菌的玻璃房中,很健康,五官端正,耳聪目明……有一天中央情报局的医生走过来,说要给孩子进行眼睛激光手术,我丈夫很吃惊,说这孩子的眼睛没有问题,一点也不近视,为什么要做激光校正手术?那人笑笑,说不是激光校正,而是要用激光把他眼睛弄近视……作为治病救人的医生,我丈夫当时的震惊可想而知。但他什么也不能做,这里根本没有他说话的地方。等到那孩子眼睛被弄近视后,有一天,另外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医生走进来,把一副眼镜交给我丈夫。我丈夫拿出那副显然是中国制造的眼镜,小心地给孩子戴上……
“那孩子——当时虽然只过了九个月,但其实已经有十七八岁的样子了——戴上了眼镜,又看得见东西了,很高兴,把手举起来摇了摇,随即扶了下眼镜——戴上眼镜的孩子一连串的几个手势动作看得我丈夫愣住了,他觉得这个动作很熟悉,从这个熟悉的动作,他第一次发现眼前的人也有些面熟。
“从那一天之后,我丈夫多长了个心眼,注意观察这个克隆小伙子像谁,当然,两三个月过去了,他还是没有头绪,毕竟这个克隆人才十七八岁,还是使用催长药物,听那负责人的口气是要让他在两年后长到五十多岁。这期间的相貌差别还是很大的。我丈夫也曾经根据中央情报局那些人露出的口风来猜测,既然此人要保卫美国安全,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维护世界和平,那会不会是什么超人、蜘蛛侠、蝙蝠侠什么的,当然他自己一一否定了这些猜测,我丈夫毕竟在美国长大,在美国受教育,对中国的事情并不十分了解。后来,也就是他发现真相的前一个星期左右,我丈夫发现中央情报局那些人对这个克隆人越来越尊重,而那个克隆人也越来越有架子,不但与我丈夫慢慢疏远,而且开始颐指气使,说话越来越像中国领导人作报告那样装腔作势……我丈夫说,这让他想起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人……但他还不能确定。有一天,那克隆人被神秘带走了三天,回来后,我丈夫去看他。我丈夫推门进去,突然呆住了。你知道,这个克隆人一直以来都穿着医院的病人制服,可是那天,我丈夫推开房门后,发现那小伙子西装笔挺,头发梳得油光铮亮——我丈夫突然看出了这个人是谁,也就是这瞬间,他惊呆了,他差一点当场昏过去,他说自己没有当场倒下去的唯一原因是他知道外面有好几双眼睛在监视着这个贴满了单面可见玻璃的房间。我丈夫说,他虽然是个科学家、医学家,对政治这个肮脏的东西一点不感兴趣,但他还是了解一些的。当他知道这个人是谁以后,他差一点神经失常。那天,就是我打开门,看到他面如死灰的一天。”
黄医生的遗孀讲到这里,脸上充满了痛苦和悲哀,我看她停下来,生怕她就此后悔,不再说下去了,就旁敲侧击地问:“那个克隆人既然不是超人,又不是蜘蛛侠,怎么会把你丈夫吓成那个样子……呵呵,我倒也很好奇呢……对了,那个克隆人像谁?或者说,那个克隆人是谁?”
医生的遗孀抬起头,眼睛里闪过浓浓的迷茫,摇摇头。我一看就急了,开口问:是谁?你不敢说?还是医生没有告诉你?
“那天我们在卧室时,我丈夫的精神都快崩溃了,所以他本来是想告诉我的,他还让我把中央电视台打开——我们家装有卫星电视,可是正在这时,有人按门铃,我丈夫哆哆嗦嗦下楼去应门。原来是和他在一起工作的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医生,那医生笑呵呵地说,正好访问朋友,经过这里,顺便来问个好。他们两位随便聊了一会,那人就告辞了。那人的到来,打断了我们夫妻的交谈,那人走后,我本来是想听丈夫说出他克隆的到底是谁的,可是,他显然改变主意了,他说,还是不要告诉我为好,让他再想想……”
我没有等她说完,就赶紧打断她问道:“后来呢,你丈夫告诉你没有?或者透露出一些什么没有?”
她摇摇头,过了一会,眼里含着泪水说:“没有后来了,我讲的就是那伙暴徒冲进我们家的前一天的事,第二天,我丈夫就被杀害了,我也……”
我已经听出名堂了,很简单,他们家一直被窃听,当那丈夫要透露真相时,那人及时敲门,假装是经过这里顺便拜访。实际上,那人的及时出现倒是客观上救了妻子一命,如果那天丈夫告诉了妻子克隆的人是谁,妻子第二天肯定也会被杀害灭口。
想到这里,我悚然一惊,这才知道,自己可能卷入到一场空前的阴谋和危机之中。同时,我敏锐地感觉到,自己刚才进来时已经被注意到,而离开的一群人中没有我,一切都太晚了。
说实话,这件事如果不是有命案卷入,可能还一时无法让我相信真有此事。我知道眼前医生的遗孀精神有问题,但我是心理学家,自然当场就判断出她没有撒谎。知道卷进去的我,遇到了一大难题。那就是,如果我只是一名普通人,一名普通的美国华人,就是说,如果我不是在白宫工作,又为北京充当间谍,那么这件事很容易处理,我只要打个电话给CNN或者BBC,这些媒体会马上过来接我们,然后把我们保护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就此安全了。而他们将会得到这个世纪最大的新闻,并且会穷追不舍,就像多年前那些华盛顿的记者穷追水门事件最终把美国总统赶下台一样。当然,其实我也想到,至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位遗孀的指控,而且这时,我才知道了那些杀害她丈夫的人为什么布置了一个种族仇杀的现场。
在美国,总是有公民指责政府搞阴谋,有些确有其事,有些则是无中生有。然而,这之中,种族歧视引起的凶杀最常被民众指责为政府阴谋。所以,这次他们枪杀医生后干脆就布置成种族仇杀现场。这反而让那些理智的民众特别是媒体有一种逆反心理,认为又是公民在受到种族歧视后的无中生有。
过了一会,等到天已经黑下来,我才告别医生的遗孀,走时,我向她保证,等我想出办法,我会立即联系她。
我走出这栋充满悲伤的小房子,走进黑暗中,在我打开车门准备进去时,我感觉到在四周黑暗之中,有好几个红外线夜视镜的镜头泛出鬼火般的幽光……
八
厚厚的米黄色的天鹅绒窗帘,粉红色的高级羊毛地毯,墙上挂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