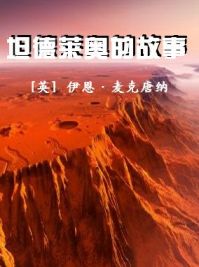坦德莱奥的故事-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上。
我像疯了一样,手里举着枪,朝着街上的人尖叫,敞开的外衣随着我的奔跑飘向身后。我竭尽全力地飞奔。
我跑向家,跑向乔古路,跑向我丢在那儿的亲人。没什么能阻止我,没什么敢阻止我,我手里还握着枪。
我要回家,我要摆脱这些疯狂。我要告诉家人——联合国要为我们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带我们飞离这里。我们要飞到不需要枪,不需要难民营,不需要救济的地方,飞到能再次找回自我的地方。
我就这么穿着我的外衣和笨重的靴子一路跑着,路过废弃的乡村巴士终点站边的棚屋,绕过兰德海路上的金属路障,穿过垃圾场,跨过了卢萨卡路——那儿有两辆公共汽车在燃烧。我跑到了乔古路。
有人堵在路上——许多许多人;有汽车——白色的联合国汽车;还有士兵——很多士兵。我看不到教会成员中心。我冲进人群,用枪托朝他们击打,推开挡我路的人。
“别挡我的路,我要回家!”
有人用手抓住了我,一个肯尼亚士兵抓住了我的肩膀,把我拽开。
“你不能进去。”
“我的家人住在这里,在教会成员中心,我需要见他们。”
“任何人不得人内。这里没有教会成员中心了。”
“你什么意思?你在说什么?”
“一个‘滑翔机’落下来了。”
我挣脱开他的手,奋力穿过人群一直走到士兵组成的警戒线。一排悍马越野车和装甲人员运输车沿着路一字排开100米。在它们后面100码处就是感染外星生物的地方。
“滑翔机”冲进了住宿大楼。我仍能够在灰泥墙上蔓延的菌团和海绵的外壳里看出蝙蝠翅膀的大致形状。
恰卡珊瑚礁的骨架已经顶开了教学大厅的锡皮屋顶,小棚屋成了一摊正在融化的塑料和在褐色烂泥里膨胀起的半透明泡泡。那烂泥碰到哪儿,哪儿就有新的泡泡长出。
礼拜堂已经在一个网状的红色脉络下消失了。就连乔古路上也长满了黄色的花和蓝色的桶状物质。恰卡六角形苔藓的触角正向路边房屋伸展。就在这时,中心外的一株荆棘树坍塌消失,腾起一股银色的微小粒子进了下水道。
“人都在哪儿?”我问一个士兵。
“接受净化。”他说。
“可我的家人还在那里!”我朝他尖叫。
他转过了头。
我朝人群叫嚷。我大声喊着爸爸的名字、妈妈的名字、小蛋的名字和我自己的名字。我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想找到他们。
太多的人,太多的脸。士兵都在看我。他们正在用电台报告,我打扰了他们。任何时候他们都可以逮捕我。更可能的是,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僻静处,朝我的后脑勺来一枪。太多的人,太多的脸。
我放下枪,伏下身在人群的腿间穿行。
净化,一个联合国用语,联合国东非总部可能已经得到了被污染的记录,去那儿也许能得到家人的消息。
奇罗莫路。我需要交通工具。我冲出人群又开始奔跑。我离开乔古路,穿过体育馆,绕过兰德海路的环形路口。街上还有几辆轿车在行驶。我跑到路中央,朝每一辆向我驶来的汽车举起枪。
“带我去奇罗奠路!”我叫道。驾驶员要么掉头就跑,要么按喇叭,要么咒骂。有人还朝我直冲过来,我一个闪身躲开了,对他们来说,我的动作非常敏捷。“带我去奇罗莫路,否则我杀了你!”武装分子坐在他们的“小家伙”里大笑着叫喊着冲过我身边。没人停下来。大家都见过太多的枪了。
有一队肯尼亚军队驻扎在普瓦尼路上,所以我穿过密密麻麻的棚屋直接上了卡里奥考路。只要我沿着左边的内罗毕河走——它现在已经成了一条堆满垃圾的臭水沟,我将直接到达恩加拉路。贫民窟的人面对我这个拿着枪穿着条纹衣服的魔鬼纷纷躲避。
“别挡我的路!”我叫道。但几乎同时,小巷里所有的人全都直愣愣站着抬头向上望,没人理会我的话。
第十章
在我看见它之前我就感觉到了它。我的皮肤感到了它的阴影带来的凉气。我也停下来抬眼望去。它向我猛扑下来,当时我只觉得——这东西从恰卡的腹地被派来就是专门来对付我的。
“滑翔机”比我想像的还要大,还要阴暗得多。它朝我俯冲过来,我愣了一下,但很快意识到自己手里拿着的家伙。我迅速举起枪朝着黑暗的翼状物射击。我不停地开枪,直到子弹全部打光我还在机械地扣扳机。我站着,颤栗着。
“滑翔机”在我头顶擦身而过,消失在塑料棚屋屋顶的后面。我伫立在那儿,看着手里握着的枪。
刹那间手枪弹膛的边缘长出许多细小的黄色花苞。花苞绽开露出晶体,晶体像鱼鳞一样遍布在油亮的黑色金属枪壳上。更多的花苞从枪口长出并从枪筒向下蔓延。晶体逐渐膨胀隆起盖住了扳机。
我像是见了蛇一样立刻惶恐地扔掉枪。我揪扯着头发、衣服,搓揉着皮肤。我的衣服已经在开始变化——斑马条纹外衣正在起泡。
我掏出里面的注射枪,它已经成了一捧黄色的晶体和花。我现在没指望救家人了。我把注射枪扔掉。
纳特森和孩子的照片掉在地上,它们先变成泡泡又化成烂泥。
我撕扯着衣服,塑料碎片和孢子从我的手指缝掉落。
我奔跑着,一只长筒靴的鞋跟掉了,我摔倒在地打了个滚又爬起来,我索性脱掉了笨重的靴子。
在我周围,卡里奥考的人都在边逃边用手撕扯着他们的衣服并搓着皮肤。我跟着他们,和他们一样惊慌失措地尖叫着奔逃。
我把衣服都扯光了,根本无暇顾及自己已经赤身裸体了。现在我一无所有了。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扔了,除了我胳膊里的芯片。两边的塑料和木头的棚屋上都抽出了恰卡的茎和芽。
我们全奔向卡里奥考市场的联合国紧急警戒线。柳条盾把我们挡回去;警棍举起来向我们砸下来,人潮冲上去又被打退回来。一些人抱着打破的脑袋栽倒在地。我奋力挤到警戒线前。
“让我过去!”
我把胳膊从两面防暴盾牌间伸过去。“我植过芯片!我植过芯片!”
警棍在我面前举起来了。
“联合国通行证!我植过芯片!”
警棍朝我砸下来,但被什么东西挡回去了。一个白人的声音叫起来。
“见鬼,她是的!让她从那儿过来!快!”
盾牌分开了,几只手抓住我,把我拽过去了。
“拿点东西给她穿上!”
一件军队夹克披在了我的肩上。我被迅即带离士兵组成的警戒线,来到一部有红十字标记的白色吉普车上。
一个穿着印有红十字背心的白人男子让我坐在车后门的踏板上,用一个扫描仪在我前臂上扫描。注射处的伤口呈青紫色,一抽一抽地痛。
“坦德莱奥·柏。美国大使馆情报联络处。好的,坦德莱奥·柏,我不知道你在那干什么,但你必须接受净化处理。”
一个助理——我猜也是个长官——回到吉普车。
“没时间这样处理了。还有2300个平民等在外面呢。”
军医抬起脸颊:“这不符合程序……”
“程序?”军官说,“让整个该死的城市在我们周围崩溃吗?不过我敢担保,如果美国人知道我们和他们间谍中的一个掺和在一起,那些人准会他妈的发火。一个表面的冲洗就可以……”
他们把我带到一辆有生物危害标记的厢式卡车上。它停在远离其他车辆的地方。我还在因为震惊和恐惧而颤抖。我任由他们剃光我所有的头发,没说一句话。有人温和地脱掉我的军用夹克并指点我站的地方。三个男人打开在卡车一边的高压水管从头到脚地冲我。水很冷,强力的水压让我感到很疼,皮肤像火烧一样。我蜷缩转动身体想避免水柱冲到乳房和身体其他的柔软部分。在冲洗第三遍时,我这才意识到他们在做什么,想起了自己为什么会到这儿。
“带我去净化!”我叫道,“我要去净化!我的家人在那,你不明白吗?”
那些人根本不听我说。我认为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正在冲刷的是个年轻女人的身体。没人听我说。
我被热风机吹干,得到几件宽松的工作服穿上,然后上了一辆大使馆吉普车的后座,它快速地穿过街道到达机场。
我们没有去机场大楼——如果去那里,我还可以挣脱开他们逃跑。我们穿过铁丝门,笔直前往一架尾舱门已经打开的大型俄国运输机。
一队人正沿着坡道进入机腹硕大的空舱中。他们大多是白人,许多人带着孩子,所有人都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大家都是难民,就……像我一样。
“我的家人还在后面,我要去接他们。”我对站在坡道前拿着安全扫描仪的人说。
“我们会找到他们的。”他边说边在官方资料库中核对我的芯片(这是我背叛家人的标志),“好了。祝好运。”
我走上金属的活动舷梯,进了飞机。一个穿着制服的俄国女人给我安排了一个中间的座位,远离任何窗户。
我被安全带固定在座位上,浑身打着颤,直到我听见活动舷梯收起来,引擎发动了——我明白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我停止了战栗。
飞机在水泥地上滑行上了跑道。
我心里有个可怕的念头:希望什么东西会坏掉,飞机坠毁让我死掉。因为我想死——我毁掉了拼命想保护的东西,却留下了毫无价值的东西。
引擎的声音更响了,我们一路前进,虽然我只能看到后座和机舱巨大的灰色弧形金属板,但我很清楚我们是什么时候离开地面的,因为我感觉到自己和肯尼亚的纽带扯断了。飞机带着我背井离乡,我的家园在下面渐渐远去。
好了,我要暂停一下,现在开始的地方最好还是让另一个声音来述说吧。
第十一章
我的名字叫肖恩。这是个爱尔兰名字。你可能看出来了,我不是爱尔兰人,我身体里没一点爱尔兰血统,就因为我妈妈喜欢这个名字——三十年前,爱尔兰的东西是很流行的。我可能没法客观地讲述坦德莱奥的故事,对此我很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