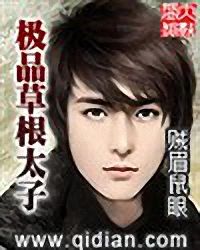哥本草根-第7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走近窗台,凑着东升的橘黄色近满的月亮,就发现呜咽之声并非来自域外,而是发自屋内。在临近窗沿的地方,那台按装位置极其愚蠢的空调内挂上面。刚刚在梦中所见的那串由贝壳构成的精美项链,在烟纱一样迷朦的月色掩映下,那些贝壳一颗颗就象宝石一般,放射出梦幻般莹莹的光泽,组成一个大大的心字图案摆在空调的上面板上。呜咽之声,正是窗外吹来的海风,刮在上面,经由它们发出来的交响。
提着的心放了下来,后脑勺那一小撮警惕的头发也息数卧倒。
双手小心翼翼的把那串象夜明珠一样,闪烁光芒的项链拿起来,尽量保持着它原有的“心”形图案。一边是惊奇一边是敬畏。
在抓到手里的一瞬,呜咽声再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以贝壳相搏之声,如燕雀叽喳如小儿的欢呼。
而当我把它们贴在胸口,就好象它们就是贝儿,拥佳人入怀。如是不是本人的臆想所形成的心中乱像,那么一定就是真的了——突然之间,贝壳们象经过了两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后,疲惫不堪,倒在久违了的牙床之上,便齐刷刷地发出甜美至极的酣声呢喃。
一股又一股的暖流在身体里涌动,感受那天簌一般,无比澄澈而又透明的温馨。一动也不敢动,“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就算是空气的流动都嫌是多余的,仿佛稍微一动,就会将那些宝贝的梦境打碎,再也修补不起。
我呆呆地静穆着,十分钟,二十分钟?也许是三十分钟以后,酣声渐落。一只又一只的贝壳,仿佛次第通通进入了最悠远的背景里,一时半会返回不了桌面上来了。
这时,我才敢把项链挂到了脖子上来。当我把项链的下半部分掖进衣服里面,紧贴着肌肤时,贝壳们再次发出声响——“咯咯咯咯”,让我顿时想起笑脸如花的李贝儿此前,经常在我面前所笑的声音。
此时此刻,就算是再铁杆的唯物主义者,也禁不住动摇。这个世界上是真的有幽灵存在呢!
这串蕴含着李贝儿姓名的项链,完全象活的一样,因为我的一举一动,亲近还是疏离,象人一样,用它所特有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哀乐喜怒。
人们常说鸡血石、和田玉、水晶是最最通灵的物质,而今,我的脖子上所挂的这些大海的精灵,贝壳又何尝不是汇聚了大自然精华的通灵宝物呢?
只是梦中女子,也就是静远庵还俗的尼姑小姐,所提到的贝儿的那封信却找不到了。按理说,它与项链没道理不放在一块儿的。可是借着越来越亮,宛如白昼的月光,找遍了整个房间,也没有发现信的影子。
我就怀疑信在我起来之前,是否就已经被风吹出去了。弯着腰弓着背仔仔细细朝屋外寻去。蓦地在背后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头皮就是一麻。扭过头去看。却又什么都没有。除了愈发皎洁的月光,还有,丝丝缕缕,风在粘稠的空气中流动过的轨迹。心里定了定,转过身来继续弯下腰去找去搜寻,杂沓的脚步声又起。这次头皮麻的面积更大了,连膝盖头,都开始发木发沉。又扭回头去看。还是什么都没有。背后面,除了风声,就是我那有节制的喘息在撞到南墙之后,折射回来的声音。我默默地把头调了回来,又猛然地返回去,就象要吓谁一大跳,结果脑后“嚓”地一声乍起。吓得脖颈子发凉,“蹭”地一声兔子一样窜了出去,冷汗都来不及流,一口气跑下楼跑出大门,上坡,一直跑到两里外的海军码头,遥遥地就见海军码头大门口两个持枪的岗哨,才松了一口气,停下来。
一路上项链上的贝壳不住地跳起来,亲吻我的嘴巴还有脸,半边脸都给亲麻了,或者说是打麻了,有好几只贝壳都是象钉子一样,尾巴尖尖的戳人。
再就是发现那种杂沓的脚步声,依然如影随形地跟着我,阴魂不散。又想跑。却发现,那两个哨兵中一个已经在看我了。胆子壮了些,同时,也不再好意思露怯。哪怕是装,也要装做坚强。
尽管只是假装坚强,可是缓慢下来的脚步还是增强了我的判断力。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就发现,响声并非来自身后,而是自己的脚下。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张长方形的纸就牢牢地占居了我右脚掌的四分之三,粘在了我的脚下不得脱。扯下来发现,原来是一封信,被一大坨不知被谁玩味过的口香糖粘在了我的鞋底下。那种令人抓狂神经错乱的杂沓的脚步声,就是由它们组合之后,摩擦地面发出来的。心说,怪不得我找不到信呢,原来是骑马找马,戴着眼镜找眼镜。瞎忙了一通。
就着海军码头的路灯,打开那封信看。起首是,“帅哥,你好!”很正式。“未曾想到的是,车站一别,就成了永诀。如果不是芳芳来说,我还真的不知道,我早已经告别人间,身处地狱。在去牢里看过我妈妈出来之后,就遭遇到了车祸横尸街头死掉了。我与你的爱情只是存在于地下。我真的是难以置信。
可是不管怎么样,我都想对你说,我爱你!
你也爱我是吧?尽管,我极少听你对我说那三个字。不过我一直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道理。你就算是颗石头我也会把你焐热的。何况你并非是颗顽石。而是一个感情内敛不善言辞,却情感极其丰富的男孩子。我说的没错吧!
“爱”是一个神圣的字眼,在你心中,以及在我心中。我其实欣赏你这一点,爱的深沉。
可惜的是,吝啬的老天,就算你们是躲在地狱里,也不忘施展它的淫威。给予我们的时间太过短暂了。片刻的欢娱之后,就是痛苦的分离,阴阳相隔。
不过,高兴的是,我就要转世了。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在此相见。
我也许会化作一棵树,站在你必经的道旁,默默地为你祈福。而我的身上,可能被人刻上了“到此一游”,亦或被系上绞索,当作晾衣绳,勒得我皮肉皆翻,喘不过气来。
我也会化作一只翅膀受了伤的小鸟,歌哭在你的窗台。期待柔软的抚摸,小心的呵护。
我还会化作一只断了翅的蝴蝶,翩跹在你的天空,舞姿不会优美,可是,请记住,那可是我的一片心啊!
我还会化作一只遍身疥痢的流浪狗,在众人唾弃的口水中鼠窜!请不要理会我凄厉的叫声,更不用你挺身而出去保护我,你只需用悲悯的眼神看我一眼,而不是嫌弃的目光,贝儿我的心就已经醉了!
--------。
二十年后。当一名风姿卓越的女孩子,站在你的面前,叫你一声“哥”或者“叔”时,请你不要责怪她的莽撞!那可不是别人,那正是寻求再续前缘的我啊!
77。…第七十七章狂乱
多少天,我已经不记得了。上了下,下了上,我就象得了坐车强近症的偏执狂,把旁人用来捞钱的时间用在坐车上。
我只坐2路车。
从起初的讶异,嫌弃,对待精神病患者才有的避之唯恐不及的仓皇闪躲,到习以为常,直至后来成为所有司乘人员的调味品。无论是司机还是售票员,慢慢地,潜移默化当中把我当成了2路车的一部分。半天见不到我,就会有人打听,“那个神经病怎么没有看见了!是不是死了?”然后象空气纯净了许多似的,深吸一口气。
当然他们在提到我时,用的绝非是象对待轮胎,发动机那样不可或缺重视的口吻,而总是一副轻佻侮慢居高临下的口气,就象我是车上的垃圾桶或者是呕吐袋拖把之类的。我就是他们无聊行车路上的一粒开心果。
对他们我也是耳熟能详。2路公交共有十八辆车组成。二十名司机,三十六名售票员。司机中四名是女的,其余,性别不详——因为都穿着裤子。有三名姓李的四名姓张的六名姓王的,其余的皆姓猪——因为不是售票员就是乘客,全都叫他们猪师傅。
售票员当中,五名是男的,八名是女的,其余,性别也不详——因为也都穿着裤子。
他们大都叫我“傻子”只有少数的几个人,文绉绉地叫我的大名——“神经病”。他们叫我“傻子”,我喜欢。因为,我们家乡有一种瓜子的牌子就叫做“傻子”。“神经病”听起来,则有点怪怪的。太官方了。我又没有住过精神病院,没有官方发的证书,这样叫不好。就象没有领结婚证的男女象夫妻一样住在一起,同样是无证上岗,公家会有意见的。
他们中有的态度不是很好,挤眉弄眼,冲着我就象狗叫,尤其是那些不男不女的售票员,象阉人歌手维塔斯那样用比常人高出几个八度的G音,摇晃着脑袋尖叫着,“不要上了!不要上了!臭死了!”
我好怕怕。只好眼睁睁地望着车子绝尘而去。我好伤心,我是个文明人,我忍受不了别人受刺激。我喜欢每一个人都笑口常开。
用官方的话说,绝大部分人还是不错的,有的甚至还可以用和霭可亲来形容,象一个一个精心雕琢过的大骗子。
因为我没有什么东西好骗的,所以,我认定了,他们对我的好,是发自真心,而不是欺骗。
尤其是那位又矮又瘦,长得象受尽委屈,勉强存活于世的朝鲜苦菜花,眼珠子一分钟要转三千六百八十一下,所有的人都叫他猪师傅的司机,待我特别地亲。一见到我,就象见到失散多年的亲人一样,亲热地不停地抚摸我的头顶,啪啪作响,于是,我就眼冒金星,晕晕乎乎感动半天。没有比他再亲切的人了。
“傻子,你在干什么?上车又下车的。”许许多多的好心人都这么问我。我就把食指放在嘴唇边,轻轻地对他们说,“嘘——这是秘密!”
“秘密?秘密你能告诉我们吗?”他们哄笑道,故意大着声问。我生气了,既然我已经说过了是秘密,你们怎么还这么大声呢,这些愚蠢的聪明人。
我在寻找回到地狱的路。除了我,我再没有告诉任何人。有人问,“傻子!你也要打票啊?”
好稀奇的话。我又不是狗,我为什么不打票。
“傻子!你打票的钱,哪里来的?”还有人问。就好象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