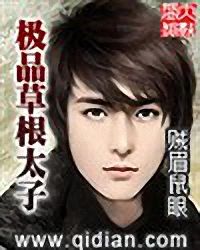哥本草根-第4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急得是汗雨如注。不晓得有多少人家,被人这一下搞得断了电。还不敢轻易走开。万一有哪个找死的鬼,在我不在的时候过来,送掉小命。
但我也不能老是这样守着。问题总是要解决的。我看了又看。这一段高压线,似乎并不像我担心的那样重要。它们位于码头高压线的最末端。所有的用电设备,都与它们无关。这一下,我心里定了许多。至少,一时半会,不会被别人发现,我干的这件好事。
从而也让我加大了消尸灭迹的决心。让现场变得跟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看看四周没人。赶紧撒腿往宿舍跑。我的所有家伙都放在宿舍里。过来接电时,我就带着两把螺丝刀,一把尖嘴钳子,我得赶紧把电笔还有万用表拿过来。
太阳毒也感觉不到了。我疯了一样,跑去又跑回。一颗始终揪紧的心,远远地看见吊机旁边没有躺着一具尸体,才松开来。
总共断了两根线,一边两个头。乍看之下,以为断了三四根呢。用电笔量了量,很奇怪没有电。
我怀疑是不是电笔坏了。本地生产的电笔,关键的时候,你真不要指望它。我曾在一天内碰到三支坏电笔。你试它的时候,它是好好的。等你用的时候,它是不灵了,时好时坏。害得我有一次把火线当成了零线抓在手里,结果,自然是被狠狠地咬了口。
想想,我还真应该是一个做电工的料,怎么打,都打不死。
我找来了一根水管当地线,又用万用表的电压档量了量,结果还是没有反应。我还是不放心,又用指尖的背部在线头上弹了弹,确实没有电。
两根断掉的全都是零线?不可能的。那么大的火花,表明其中必有一根是火线。可是,我为什么没有被打死呢?搞不懂,是保险动作够快?只有这一种解释了。
我不得不感谢老天爷的眷顾与垂怜。
既然,线头上都没有电,那么处理起来,就方便多了。根本就不必爬高上低的。把垂下来的部分,剪掉。不让人轻易碰到就行。
把剪下来的部分,扔到河里。高压线风吹日晒的,本身就无需掩饰,就象是断了八百年。挂在那里几个世纪似的。
事情处理完了。脆弱也就跟着来了。
可是我不敢对人说,我差点被电打死。不敢说。只能一个人悄悄地把秘密埋在心底。,装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
可是我的心里一个劲地打着冷颤。第一次感到,生命是如此脆弱,不堪一击。什么理想,未来啊。在脆弱的生命面前,都成了狗屎。谁也难保今晚闭上眼睛睡去,明天就一定能够睁着眼睛醒来。
我再也无法做到心如止水。因为,我刚刚死里逃生。我强烈地需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哪怕对方是个陌生的人,只能象征性地对我说声,太可怕了。对于我来说,就已经足够。
那种无可名状的凄凉淤积在胸口。也并不是说,同情你的人找不到。比如说于满舱。我只要愿意倾诉,他还是愿意听的。但以后怎么办呢?那就成了一个把柄落在他手上。我已经不复像刚来时,那样,对他抱以信任了。他并不是象表面所看到的那样胸无城府。我担心,有一天,他会把我的这番话,当成笑柄传出去。
我突然间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如此孤独。连一个倾诉的对像都没有。如果,我有一个女朋友,甚至于一个妻子,那该有多好。在心情如此糟糕的时候,跟她们倾诉一下。吐一下肺腑之言,至少不必担心,她们马上把我出卖掉。
什么我还太年轻?什么我等到三十四十再结婚?谁又能保证,你一定就能活到那个三十四十。“世上的黄土,不只是埋老人”,也埋年轻人啊!
45。…第四十五章因爱知味
“当我想到“爱人”这个词时,眼睛就湿润了。我的爱在哪里,我所爱的人又在何方?
这时,在我脑海里浮现出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妹妹,另外一个,就是她。借了金鱼”的手机,给她打电话。我的眼里含满泪水,就象一个受尽委屈的孩子,在寻求母亲的抚慰。
“谁呀?”听上去,应该在睡觉。我能想像得到她眯缝着眼睛,迷迷糊糊接电话,随时准备又扔下电话昏睡百年的样子。
“听不出来?”本来是想哭的,却笑着说。
“你倒底是谁呀?”有点儿失望,心里说,我在她心目当中,难道一点位置也没有了?如此看来,她也不会有兴趣知道,不一会前,我差一点就和她说白白了!心里面顿时酸溜溜的。
这要是以前,我会啪地把电话撂掉。可是今天,哪怕她不理我,我也要说上几句。直到此时我才发现,那些以前为自己所不耻的,男人的无赖劲,原来,自己也有。
“我是电俞啊!”我失望的近乎于敷衍。
“你啊!”声音一下变得清澈起来,好像这时才清醒过来,“你也会打电话吗?”这话说的好希奇,好像我是亚马逊丛林里的印第安土著,“你从来没有打电话给过我哎。真的不好意思,刚才没有听出来。”这么一说,我心里晕凉晕凉舒服多了。
“懒猪,是在睡觉吧?”
“唔——!听出来啦!”我猜她正在用手背擦眼睛。
“还没睡好么?没睡好,你就继续睡吧,我就不打扰你了。我挂了?”我恋恋不舍地抓着电话,听那边的反应。
“喂,俞大头,”她在那头突然间大叫起来,“你也太不负责任了吧!把人家吵醒,你就开溜,有没有公德心?”
“你不是还没睡好么?”心里面一阵狂喜。
“谁说我没有睡好!谁说的,头都快睡扁了,还没有睡好?都无聊死了!姑妈和表姐都去上班,就留我一个人在家里,电视又不好看,”
“你倒底在哪里啊?”
“市里啊!”
“你家在市里吗?他们说,你家不是不是在市里的!”
“是啊!我家是不在市里,我是在我的表姐家里。”
“既然无聊,那你为什么不来上班呢?”
“上班?上班还不是一样!你也不理我!上班干嘛,我还怕没有的吃啊!饿死?”
“过来吧?”
“为什么?”
“不为什么,”
半天没有声音,“喂!你挂了吗?”
“你才挂了呢!”
“那你干吗不说话?”
“我是在想,你是不是想我了?所以才给我打电话,”电话那头的她扑哧一声笑了起来,“不要跟我说,你想的倒美,”马上又补充道。
我没有吭声。“真的是想我了啊?”笑声没有了,“莫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笑声又起,“让我看看,”我听到嘭的一声,应该是赤脚蹦到地板上发出的声音,“是唉,今天的太阳是打西边出来的,”笑的嘎嘎的。
“下巴掉了吗?”我有点被作弄的感觉,忍不住呛了她一句,“你过不过来?”有点凶巴巴。
“你的下巴才掉了呢!”她不高兴地回敬了一句,“不过去。你要我过去就过去啊!你当我是什么!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不过来拉倒!”我气得一下子把电话掐了。
把电话还给“金鱼”,一个人顶着烈日跑到码头上,缩在吊机底下,看着大海,发呆。
生刚才那个家伙的气。可是,并不是严重。能听到她的声音,说上两句,说心里话,比吃什么治疗抑郁的药,都要管用。心情好多了。
也许已经放到了回收站,可至少没有象我所害怕的那样,把我扔到垃圾筒里。虽然口气上,疯疯颠颠的不太正经,对我还是不错的。
在吊机下面,先是坐着,一会儿感觉眼皮有点儿沉重,慢慢就倒下去,睡着了。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突然间就听到机车的轰鸣声。蓦地惊醒,还以为停了十几二十天的“好望角之鹰“的马达让谁给弄响了。
甫一睁开眼睛,就见一辆黑色的影子离弦的箭一样,风驰电掣冲我就冲了过来,眼看着就要撞上我了,停下来。
“你什么意思,要我过来,你却躲到了这里,害得我好一通找。”不等我说话,她一边手掸着凉风往身上扇,一边向我抱怨道,“热死我了!”她说。
我没有说话,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她。戴一副黑色反光墨镜,穿一件黑色的小背心和一条牛仔短裤。
背心下面紧紧包裹着一对结实坚挺的青苹果,不大不小盈盈可握,也许是运动员出身,那一对尤物,显得特别磁实。下身的灰色牛仔短裤,也是紧紧地包裹着身子。不知什么时候在右臂的三角肌的位置上,还纹了个不知什么东西的东西。
“看什么看!老俞?”顺着我的目光,她扭着头去看自己的右肩头。用左手往上面摸到了摸。
“什么东西啊?张牙舞爪的。”我用那种老派的口吻,接下来就要教育下一带似的。
“你啊!还能是什么,”她从车子上下来,把大张脚打起,走到荫凉处,双手推了我一把。
灼热的太阳下面,世界上的其他人,似乎都被晒焦入了土,就只剩下了我和她。在她的撩拨下,我的激情一下子就点燃了。粗重地喘起气来,不等她把手缩回去,双手一把逮住,顺势一拉,把她的整个人就带到了怀里。
紧紧地抱住了她。登鼻子上脸,嘴巴就吻了上去,从脸颊,到耳朵,之后,又是嘴巴。在嘴巴上费了一些周折,费了不小的力气,才用舌头把她的牙齿撬开,早知道,我应该备一把撬棍的。
舌头钻进去,她就显得魂不守舍起来,与她的两根舌头象两条上下飞舞的蛟龙,厮杀着纠缠在了一起,。
我的手贪婪地在她的背间臀部游弋。女孩气息咻咻,身体上的热浪透过薄薄的一层衣物阵阵袭来。
我的右手,像沙漠里的蝰蛇,悄无声息地潜入了她的背心里,倏地登上峰巅。她的身子为之一颤,死死地搂紧了我。
在那细腻如绸的质地上流连往返,揉捏辗转。那细小的蓓蕾花骨朵儿指捏不住,只得用指尖弹拨,轻轻的,柔柔的,就像是对待一场美丽绮俪而又易碎的梦。
她也象琴键之下的音箱,随着我的弹拨,不住地发出低低的动听的呻吟。伴着轻轻的海浪,如梦如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