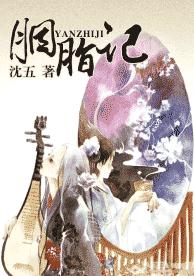胭脂-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陶陶讶异地问:“为什么不用立顿茶包?顶香。”
我说:“你懂什么。”
“至少我懂得碧螺春是一种带毛的茶叶,以前土名叫‘吓煞人’。”
“咦,”母亲问,“你怎么晓得?”
“儿童乐园说的:采茶女把嫩叶放在怀中,热气一薰,茶叶蒸出来,闻了便晕,所以吓煞人。”
我说:“以前你还肯阅读,现在你看些什么?”
“前一阵子床头有一本慈禧传。”母亲说。
“那是五年前的事了。”我瞪着陶陶,“就知道跳舞。”
“跳舞有趣嘛!”陶陶不服气。
是的,跳舞是有趣,也许不应板着面孔教训她,我自己何尝不是跳舞来。
“而且我有看读者文摘及新闻周刊。”
“是吗,那两伊战争到底是怎么一会事?说来听听。”
“妈妈怎么老不放过我!”她急了。
“暑假你同我看熟宋词一百首,我有奖。”
妈妈冷笑,“之俊你真糊涂了,你以为她十二岁?看熟水浒传奖洋娃娃,看熟封神榜又奖糖果,她今年毕业了,况且又会赚钱,还稀罕你那鸡毛蒜皮?”
我闻言怔住。
一口饭嚼许久也吞不下肚。
陶陶乖巧地笑说:“妈妈还有许多好东酉,奖别的也一样。”
她外婆笑问陶陶:“你又看中什么?”
“外婆,我看中你那两只水晶香水瓶。”
“给你做嫁妆。”
“我十年也不嫁人,要给现在给。”
“那是外婆的纪念品,陶陶,你识相点。”
“你妈今天立意跟你过不去,你当心点。”
陶陶索然无味,“那我出去玩。”
她又要找乔其奥去了。
我问:“为什么天天要往外跑?”
母亲笑,“脚痒,从十七岁到二十七这一段日子,人的脚会痒,不是她的错。”
陶陶露着“知我者外婆也”的神色开门走了。
是不是我逼着她往外跑?家里没有温暖,她得不到母亲的谅解,因此要急急在异性身上寻找寄托。
我用手掩着面孔,做人女儿难,做人母亲也难。
“之俊,你又多心想什么?”母亲说,“最近这几年,我看你精神紧张得不得了。”
“是的,像网球拍子上的牛筋。”
“松一松吧,或者你应该找一个人。”
我不响。
“你生活这样枯燥,会提早更年期。”
我问:“叫我到什么地方去找?以前看到女同事夜夜出去约会,穿戴整齐去点缀别人的派对,就纳罕不已,深觉她们笨,后来才懂得原来她们是出去找对象,但是我做不到。”
“那你现在尽对牢些木匠泥水匠也不是办法。”
“我无所适从。”
“你才三十多岁,几时挨得到七老八十?不一定是要潘金莲才急需异性朋友,这是正常的需要。”
陶陶说得真对,母亲真的开通。
我用手撑着头。
“老是学这个学那个干什么?”母亲说。
母亲说:“你打算读夜校读到博士?我最怕心灵空虚的女人药石乱投什么都学,本来学习是好的,但是这股歪风越吹越劲,我看了觉得大大的不妥。”
我抬起头,“然则你叫我晚上做什么?”
“我也托过你叶伯伯,看有什么适合的人。”
我说:“妈,这就不必了,益发显得我似月下货。”
“所以呀,不结婚不生孩子最好,永远是冰清玉洁的小姐,永远有资格从头再来。”
“我是豁达的,我并没有非分之想。”
“叶成秋都说他不认识什么好人,连他自己的儿子都不像话,每年换一个情妇,不肯结婚,就爱玩。”
我说:“我得认命。”
“言之过早,”母亲冷笑,“我都没认命呢,我都五十岁了,还想去做健康运动把小腹收一收呢。”
我把笔记翻来覆去地折腾,纸张都快变霉菜了。
“读完今年你替我休息吧。”
我不出声。
“公司生意不好就关了门去旅行,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压力不过是你自己搁自己头上的,打日本鬼子的时候咱们还不是得照样过日子?”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你父亲带着我走的时候,我也只有十九岁,手抱着你,来到这个南蛮之地,一句话听不懂,广东人之凶之倔,嘿,不经历过你不知道,还不是挨下来,有苦找谁诉去?举目无亲。”
“你爹夜夜笙歌,多少金子美钞也不够,才两年就露了底,怎么办?分手呀,我不能把你外公的钱也贴下无底洞,这还不算,还天天回来同我吵。
“最惨是你外公去世,我是隔了三个月才知道的,那一回我想我是真受够了。但天无绝人之路,又与叶成秋重逢。所以你怕什么?柳暗花明又一村,前面一定有好去处。”
我握紧母亲的手,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不重要,我们这三个女人必需互爱互助。
“我回去了。”妈妈说。
“我送你。”我站起来。
“不用,我叫了你叶伯伯来接我。”
我说:“看样子,叶太太是不行的了。”
母亲不响。
我自管自说下去,“也许情况会得急转直下。”
“如何直下?你以为他会向我求婚?”没想到母亲会问得这么直。
我嗫懦地低下头。
“他看上去比时下的小生明星还年轻,要再娶,恐怕连你这样年纪的人都嫌老,他叶某放个声气出来,要什么样的填房没有?到时恐怕连旧情都维系不住。”
我连忙说:“朋友是不一样的,叶成秋不是这样的人。”
“女人最怕男伴从前的朋友,怕你们老提着从前的人,从前的事,非得想办法来隔绝了你们不可,除非你懂得做人,以她为主,我可做不到,办不到。”
这话里有许多感慨,有许多醋意,我不敢多言。
“我送你下楼。”我说。
叶成秋站在车子外。
现在肯等女人下楼来的,也只有叶成秋这样的男人。
他说:“我初初认识你母亲的时候,之俊,她就跟你一样。”
我温和地说:“其实不是,叶伯伯,那时候母亲应与陶陶差不多大。”
“但陶陶还是个孩子。”
“她们这一代特别小样。”
“会不会是因为你特别成熟?”他笑问。
“不,我不行。”我把手乱摇。
叶成秋说:“之俊,你有很大的自卑感。”
“我不应该有吗?我有什么可以自骄?”
叶成秋笑,“总之不应自卑。”
今夜不知怎地,我的眼泪就在眼眶中打滚,稍不当心用力一挤就会掉下来。
最受不了有人关注垂询。
受伤的野兽找个隐蔽处用舌头舔伤口,过一阵子也就挨过去了,倘有个真心人来殷勤关注,硬是要看你有救没救,心一酸一软,若一口真气提不上来,真的就此息劳归主也是有的。
他上车载了母亲走。
在电梯中,我觉得有一撮灰掉在眼中,还是滚下一串眼泪,炙热地烫着冰冻的面颊。
真肉麻,太过自爱的人叫人吃不消,女儿已随时可以嫁人,还有什么资格纵容自己,为小事落泪。
我温习至凌晨不寐,天露出鱼肚白时淋浴出门吃早餐去。
考完试步出试场,大太阳令我睁不开双目,睡眠不足的我恍惚要随吸血伯爵而去。
“之俊!”
我用手遮住额角看出去。看到罗伦斯给我一个大笑容。他坐在一辆豪华跑车里。
“唉,”他笑着下车,“之俊,原来你是杨之俊。”
我坐上他的车,冷气使我头脑清醒,簇新的真皮沙发发出一阵清香。
“是,我是杨之俊。你不是一早就晓得?”
“之俊,我是叶世球啊。”
这名字好热,他面孔根本就熟。
“唉,我是叶成秋的儿子。”他笑。
轮到我张大嘴,啊,怪不得,原来此花花公子即是彼花花公子。
“之俊,”他好不兴奋,“原来我们是世交,所以,有缘分的人怎么都避不过的,我总有法子见到你。”
我也觉得高兴,因对叶成秋实在太好感,爱屋及乌,但凡与他沾上边的人,都一并喜欢。
怪不得老觉得他面熟,他的一双眼睛,活泼精神,一如他父亲。
“你是怎么发觉的?”我问。他略为不好意思,“我派人去查你来。”
我白他一眼。就是这样,连同吃咖啡的普通朋友也要乱查。他大概什么都知道了。
“我们现在可以做朋友吧?”
“朋友没有世袭的,叶公子,我同令尊相熟,不一定要同你也熟。”
“咄!我信你才怪,女人都是这样子。”
“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叶世球。”
广东人喜欢把“球”字及“波”字嵌在名字中,取其圆滑之意。正如上海人那时最爱把孩子叫之什么之什么,之龙之杰之俊之类。
“世球,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
“你现在想做什么?”
我不假思索:“睡觉。”
他立刻把握这个机会,做一个害羞之状,“之俊,这……我们认识才数天,这不大好吧,人们会怎么说呢?”
我先是一呆,随即笑得眼泪都流出来。
这个人,我开始明白干嘛他会吸引到女人,不一定是为他的经济情形。
父亲不会明白,父亲老以为母亲同叶伯伯在一起是为他的钱。
“说真的,到什么地方去?”他问。
“带我去吃咖啡。”
“我同你去华之杰,那里顶楼的大班咖啡室比本市任何一家都精彩。”
“我去过,我们换个地方。”
他讶异地说:“爹说你长大后一直与他维持客气的距离,看来竟是真的了。”
“你与叶伯伯说起我?”
“是,他说你有一个孩子。”
我点点头。
“她已有十七岁?”叶世球很惊奇,找我求证。
“快十八岁。”
“这么大?我不相信,之俊,你有几岁?”
“问起最私隐的事来了。”我微笑。
“不可能?你几岁生下她?十五?十六?未成年妈妈?”
我仍然微笑,并不觉得他唐突,他声音中的热情与焦虑Jar电子书下载乐园+QiSuu。с○m都是真实的,我听得出来。
“世球,你三个问题便问尽了我一生的故事。”
“可不可以告诉我?”
“不可以。”
“之俊,不要吊我瘾。”他恳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