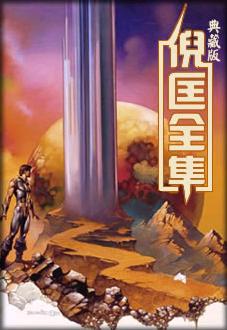孽海花-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还唱哩!”说着话,那船愈靠近来,就离这船不过一箭路了,却听一人唱道:莽乾坤,风云路遥;好江山,月明谁照?天涯携着个玉人娇小,畅好是镜波平,玉绳纸,金风细,扁舟何处了?雯青道:“好曲儿,是新谱的。你们再听!”那人又唱道:痴顽自怜,无分着宫袍;琼楼玉宇,一半雨潇潇!落拓江湖,着个青衫小!灯残酒醒,只有侬相靠,博得个白发红颜,一曲琵琶泪万条!
雯青道:“听这曲儿,倒是个愤世忧时的谪室。是谁呢?”说着,那船却慢慢地并上来。雯青看那船上黑洞洞没有点灯,月光里看去,仿佛是两个人,一男一女。雯青想听他们再唱什么,忽听那个男的道:“别唱了,怪腻烦的,你给我斟上酒吧!”雯青听这说话的是北京人,心里大疑,正委决不下,那人高吟道: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
只听那女的道:“什么麻不麻?你要作死哩!”那人哈哈笑道:“不借重尊容,哪得这付绝对呢?”雯青听到这里,就探头出去细望。那人也推窗出来,不觉正碰个着,就高声喊道:“那边船上是雯青兄吗?”雯青道:“咦,奇遇!奇遇!你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呢?”那人道:“一言难尽,我们过船细谈。”说罢,雯青就教停船,那人一脚就跳了过来。这一来,有分教:一朝解绶,心迷南国之花;
千里归装,泪洒北堂之草。
不知来者果系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宝玉明珠弹章成艳史 红牙檀板画舫识花魁
却说雯青正在浔阳江上,访白傅琵琶亭故址,虽然遇着一人,跳过船来,这人是谁呢?仔细一认,却的真是现任浙江学台宗室祝宝廷。宝廷好端端地做他浙江学台,为何无缘无故,跑到江西九江来?不是说梦话么!列位且休性急,听我慢慢说与你们听。原来宝廷的为人,是八面玲珑,却十分落拓,读了几句线装书,自道满洲名士,不肯人云亦云,在京里跟着庄仑樵一班人高谈气节,煞有锋芒。终究旗人本性是乖巧不过,他一眼看破庄仑樵风头不妙,冰山将倾,就怕自己葬在里头。不想那日忽得浙江学政之命,喜出望外,一来脱了清流党的羁绊;二来南国风光,西湖山水,是素来羡慕的,忙着出京。一到南边,果然山明川丽,如登福地洞天。你想他本是酪浆毡帐的遗传,怎禁得莼肥鲈香的供养!早则是眼也花了,心也迷了。可惜手持玉尺,身受文衡,不能寻苏小之香痕,踏青娘之艳迹罢了。
如今且说浙江杭州城,有个钱塘门,门外有个江,就叫做钱塘江。江里有一种船,叫做江山船,只在江内来往,从不到别处。如要渡江往江西,或到浙江一路,总要坐这种船。这船上都有船娘,都是十七八岁的妖娆女子,名为船户的眷属,实是客商的钩饵。老走道儿知道规矩的,高兴起来,也同苏州、无锡的花船一样,摆酒叫局,消遣客途寂寞,花下些缠头钱就完了。若碰着公子哥儿蒙懂货,那就整千整百的敲竹杠了。做这项生意的,都是江边人,只有九个姓,他姓不能去抢的,所以又叫“江山九姓船”。闲话休提。
话说宝廷这日正要到严州一路去开考,就叫了几只江山船,自己坐了一只最体面的头号大船。宝廷也不晓得这船上的故事,坐船的规例,糊糊涂涂上了船。看着那船很宽敞,一个中舱,方方一丈来大,两面短栏,一排六扇玻璃蕉叶窗,炕床桌椅,铺设得很为整齐洁净,里面三个房舱。宝廷的卧房,却做在中间一个舱,外面一个舱空着,里面一个舱,是船户的家眷住的。房舱两面都有小门,门外是两条廊,通着后艄。上首门都关着,只剩下首出入。宝廷周围看了一遍,心中很为适意,暗忖:怪道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一只船也与北边不同,所以天随子肯浮家泛宅。原来怎地快活!那船户载着个学台大人,自然格外巴结,一回茶,一回点心,川流不断。一把一把香喷喷热毛巾,接着递来,宝廷已是心满意足的了。开了船,走不上几十里,宝廷在卧房走出来,在下首围廊里,叫管家吊起蕉叶窗,端起椅子,靠在短栏上,看江中的野景。正在心旷神怡之际,忽地里扑的一声,有一样东西,端端正正打上脸来,回头一看,恰正掉下一块橘子皮在地上。正待发作,忽见那舱房门口,坐着个十七八岁很妖娆的女子,低着头,在那里剥橘子吃哩,好像不知道打了人,只顾一块块地剥,也不抬头儿。那时天色已暮,一片落日的光彩,反正照到那女子脸上。宝廷远远望着,越显得娇滴滴,光滟滟,耀花人眼睛。也是五百年风流冤业,把那一脸天加的精致密圈儿遮盖过了,只是越看越出神,只恨她怎不回过脸儿来。忽然心生一计,拾起那块橘皮,照着她身上打去,正打个着。宝廷想看她怎样,忽后艄有个老婆子,一迭连声叫珠儿。那女子答应着,站起身来,拍着身上,临走却回过头来,向宝廷嫣然地笑了一笑,飞也似地往后艄去了。宝廷从来眼界窄,没见过南朝佳丽,怎禁得这般挑逗,早已三魂去了两魂,只恨那婆子不得人心,劈手夺了他宝贝去,心不死,还是呆呆等着。那时正是初春时节,容易天黑,不一会,点上灯来,家人来请吃晚膳,方回中舱来,胡乱吃了些,就踅到卧房来,偷听间壁消息,却黑洞洞没有火光,也没些声儿,倒听得后艄男女笑语声,小孩啼哭声,抹骨牌声,夹着外面风声,水声;嘈嘈杂杂,闹得心烦意乱,不知怎样才好。在床上反复了一个更次,忽眼前一亮,见一道灯光,从间壁板缝里直射过来。宝廷心里一喜,直坐起来,忽听那婆子低低道:“那边学台大人安睡了?”那女子答着道:“早睡着哩,你看灯也灭了。”婆子道:“那大人好相貌,粉白脸儿,乌黑须儿,听说他还是当今皇帝的本家,真正的龙种哩。”那女子道:“妈呀,你不知那大人的脾气儿倒好,一点不拿皇帝势吓人。”婆子道:“怎么?你连大人脾气都知道了!”那女子笑道:“刚才我剥橘皮,不知怎的,丢在大人脸上。他不动气,倒笑了。”婆子道:“不好哩!大人看上了你了。”那女子不言语了,就听见两人屑屑索索,脱衣上床。那女子睡处,正靠着这一边,宝廷听得准了,暗忖:可惜隔层板,不然就算同床共枕。心里胡思乱想,听那女子也叹一口气,咳一回嗽,直闹个整夜。好容易巴到天亮,宝廷一人悄地起来,满船人都睡得寂静,只有两个水手,咿哑咿哑的在那里摇橹。宝廷借着要脸水,手里拿个脸盆,推门出来,走过那房舱门口,那小门也就轻轻开了,珠儿身穿一件紧身红棉袄,笑嘻嘻地立在门槛上。宝廷没防她出来,倒没了主意,待走不走。那珠儿笑道:“天好冷呀,大人怎不多睡一会儿?”宝廷笑道:“不知怎地,你们船上睡不稳。”说着,就走近女子身边,在她肩上捏一把道:“穿的好单薄,你怎禁得这般冷!我知道你也是一夜没睡。”珠儿脸一红,推开宝廷的手低声道:“大人放尊重些。”就挪嘴儿望着舱里道:“别给妈见了。”宝廷道:“你给我打盆脸水来。”珠儿道:“放着多少家人,倒使唤我。”嗤的一笑,抢着脸盆去了。宝廷回房,不一会,珠儿捧着盆脸水,冉冉地进房来。宝廷见她进来,趁她一个不防,抢上几步,把小门顺手关上。这门一关,那情形可想而知。却不道正当两人难解难分之际,忽听有人喊道:“做得好事!”宝廷回过头,见那老婆子圆睁着眼,把帐子揭起。宝廷吃一吓,赶着爬起来,却被婆子两手按住道:“且慢,看着你猪儿生象,乌鸦出凤凰,面儿光光嘴儿亮,像个人样儿,到底是包草儿的野胚,不识羞,倒要爬在上面,欺负你老娘的血肉来!老娘不怕你是皇帝本家,学台大人,只问你做官人强奸民女,该当何罪?拼着出乖露丑,捆着你们到官里去评个理!”宝廷见不是路,只得哀求释放道:“愿听妈妈处罚,只求留个体面。”珠儿也哭着,向他妈千求万求。那婆子顿了一回道:“我答应了,你爹爹也不饶你们。”珠儿道:舐枵诟窃蚋的硕,抱着琵琶弹哩。效亭走下船来,就哈哈大笑道:“雯兄可给我们拖下水了。”雯青正待说话,山芝忙道:“别听效亭胡说!这是船主人,我们不能香火赶出和尚,不叫别个局,还是清局一样。”胜芝道:“不叫局也太杀风景。雯青自己不叫,就是完名全节了,管甚别人。”雯青难却众意,想自己又不是真道学,不过为着官体,何苦弄得大家没趣,也就不言语了。于是大家高兴起来,各人都叫了一个局。等局齐,就要开船。那当儿里,忽然又来了一个客,走进舱来,就招呼雯青。雯青一看,却是认得的,姓匡,号次芳,名朝凤,是雯青同衙门的后辈,新近告假回籍的,今日也是山芝约来。过时见名花满坐,翠绕珠围,次芳就向众人道:“大家都有相好,如何老前辈一人向隅!”大家尚未回言,次芳点点头道:“喔,我晓得了,老前辈是金殿大魁,必须个蕊官榜首,方配得上。待我想一想。”说着,仰仰头,合合眼,忽怕手道:“有了,有了。”众人问:“是谁?”次芳道:“咦,怎么这个天造地设、门当户对的女貌郎才,你们倒想不到?”众人被他闹糊涂了,雯青倒也听得呆了。在坐的妓女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甚药,正要听他下文,次芳忽望着窗外一手指着道:“哪,哪,那岸上轿子里,不是坐着个新科花榜状元大郎桥巷的傅彩云走过吗?”雯青不知怎的听了“状元”二字,那头慢慢回了过去。谁知这头不回,万事全休,一回头时,却见那轿子里坐着个十四五岁的不长不短、不肥不瘦的女郎,面如瓜子,脸若桃花,两条欲蹙不蹙的蛾眉,一双似开非开的凤眼,似曾相识,莫道无情,正是说不尽的体态风流,丰姿绰约。雯青一双眼睛,好像被那顶轿子抓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