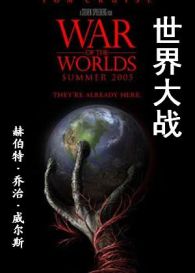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67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罗斯福再三使自己和所有的人都抱有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的希望这一点,就有助于改变公众对国际事务的态度,并在将来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在罗斯福自己的国家里尤其是如此。从1947年到1952年,国际关系中主要的新特征是美国所扮演的新角色。在这方面,美国的民族利益当然对外交政策发生影响,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美国人一般自认为已投入的那种道义上的十字军讨伐——即讨伐这次戴着共产主义面具的暴政与侵略的十字军运动。美国对国际事务的态度中这个理想主义的特色,产生了相当实际的效果。例如,我们难以相信,如果美国人民不是为了实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理想,他们竟会支持在朝鲜的一场战争,尽管从罗斯福逝世以后,这种理想已大为改变,比以前冷漠多了。
在一种多国保持均势的局面下,自以为正直并感到义愤的心情现在或许已不是制定国家政策的完全可靠的指南。实际上,这种心情基本上会破坏这种局面,因为它们总是促使人们设法树立某种最高权威,有权来宣布什么是正确的,并予以实行。而在联合国成立以后,正是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假如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将用自己的实力改变多国主权平等的制度,并且最终把它推翻,那末罗斯福及其前辈威尔逊将负很大的责任。
有识之士曾经说过,神话同事实一样,推动着人类并影响着历史向前发展。战时人们曾希望,一旦获得胜利后,便将出现全球的和平与繁荣,这肯定是一篇神话,无视历史和俄国同西方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现实。然而,如果神话是扣人心弦、符合人们心灵深处的愿望的,象这一篇这样,如果它最终能在人们心中唤起新的忠诚之感,象这一篇可能会唤起的那样,那末它们便能超越事实,排除失望的情绪,从而创立伟大的制度,在人类的事务中促成革命。当然,这种制度或革命的形式不一定完全合乎最初的意图或预见,也离不开自私、野心、憎恨和恐惧等其他的动机。
要说罗斯福写入大同盟历史中的这篇神话,最后是否能同促进人类演变的巨大推动力如基督教或马克思主义这些神话媲美,这在1952年也为时过早,但如果把它一笔抹杀而称之为愚蠢的幻想,那就会误解人们的心意,并对一种最有力的政治领导方式作出错误的判断。
甚至在1952年,人们就大可以这样说。那就是,自从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俄国国家权力在国内外的扩大与巩固,是从马克思主义中汲取力量和得到理论根据的。同样,美国权力的扩大与巩固,似乎是从这些同威尔逊和罗斯福的姓名联在一起的神话中得到了思想上的(或者可以说是文字上的)根据的。如果人们相信和平、正义、自由与富饶是可以实现的,那么它们就成为值得争取的强有力的积极目标,而这些目标是一项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的支柱,并促使人们在单靠民族利己主义决不敢冒险的地方大胆行动。
在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同盟保持团结的一切因素中,官方宣布的战争目标看来是最脆弱的。当战争尚未结束时,罗斯福本人为了波兰和满洲问题在同斯大林交涉中,就在很大程度上背弃了自己的原则。他为了保持各大盟国之间的合作而作出了这些让步,但在摧毁共同的敌人之后,这种合作还是没有持续下去。尽管如此,从长远来看,领导大同盟的政治家们向全世界声明和宣布的理想,到头来可能成为他们所有的行动中最富有意义的部分。
二十世纪人类信念中最大的变化之一,是逐渐产生了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社会与经济关系至少有可能加以合理的控制和有意识的安排。罗斯福对于通过发挥人的意志力可能创造一个美好世界的信心,就反映了这种信念。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幻想也是基于这一信念。超国家的行政机构的成长仅仅是一个例子,说明人们处心积虑地想通过切实的努力来管理人类的事务。同样,新兴的超级大国之所以能崛起,是因为散布在地球上广大地区内千百万人的社会力量得到成功的协调,这是通过政府的官僚机构而实现的,它企图运用人力物力来建立军事力量,或许还想达到其他种种目的。因此,由战时大同盟(及其敌人)所促成的一切持久的变革,可以看作人类思想与行动大变化的各个方面,这个大变化可以称为二十世纪的社会革命。
这种认为人类可以有意识地控制和操纵他们的社会关系与经济关系的信念,具有深远的思想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但直到二十世纪,这个信念才越出思想界扎根成长,不再是不切实际的白日梦,而是国内和国际政治活动的基础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有意识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社会与经济的传统格局。那次大战以后,布尔什维克便着手使社会与经济计划成为俄国的常规。经过几次冒失的开端后,这个新制度直到1928年才真正发挥作用。不久,从1933年起,希特勒在德国创立了基本上类似的制度。斯大林和希特勒的这种做法,都是根据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动员期间两国在控制社会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后来,他们为新的战争作准备时,又扩大了这一制度,使它臻于完善。相形之下,西方国家远远落在后面,但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类似的事情也发生了。英美两国政府作了重要的改革,并在一定程度内表现出富有意义的克制,从而建立了它们自己的有控制的社会。
因此,我们可以把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看成是为一种新型社会组织接生的两个助产士。在和平时期的发展中,这方面的先例与雏形很容易找到,而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的两次世界大战则大大加速了已经发生的变化。外来的威胁和对胜利的希望,迫使或敦促人们采取控制社会的新措施。当这些新措施产生巨大的成果,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时,人们的思想也改变了。通过或多或少受到合理控制的行政管理机器的运转,各种社会力量都被成功地调动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这时人们似乎突然可以掌握新的权力与新的财富了。
这次社会革命可以同近代欧洲史上两大革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相比。事实上,它同那两次是完全一样的。工业革命是科学应用于工程的结果。人们经过深思熟虑,能驱使自然界的物质力量为自己的目标服务,从而大大增加了他们可以运用的财富与权力。当然,这并非人类初次合理地操纵事物,但确实具有新的规模,并取得惊人的效果。
法国大革命有许多成果,其中之一是把理性运用或试图运用于政治制度。人们经过思考,认为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调整各种政治关系,使它们适合自己的需要和目的。当人类的这种理性用之于事物时,便产生新兴工厂的产品,而当这种理性施之于政治时,便可能产生(或许这是幻想吧?)自由、平等、博爱这类产品。
然而,两者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工业产品易于得到良好的评价,事实上几乎得到普遍的赞许,例如比过去便宜的布料、便宜而迅速的运输等等,都使人们获得物质上的舒适与便利,这是很少人能否认的。可是政治制度要达到什么目的,这个问题却含糊得多,会引起激烈的争辩,并涉及种种感情和利害关系,这些几乎是不能用合理的计算和调整来处理的。
对于二十世纪的社会革命来说,这一问题甚至更为尖锐。同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情况一样,目前也在人类活动的新领域内实行合理的控制与操纵。多少世纪来偶然组成的各种社会与经济的制度与机构,现在都经过改组与调整,使它们为一个目标服务,即争取胜利。在战争或备战的压力下,这个目标可能足够了。但在军事至上的国家中,一切社会力量及物质资源都被用来保持尽可能强大的军事实力,这种国家本身就不太吸引人,即使仅仅由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压制或漠视丰富多彩的人类经验与价值。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民主主义者都声称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福利国家。在这方面,人们只做过部分的试验,而且不能回避要达到什么具体目标这个问题,即在不同的社会集团、阶级、民族与种族之间时常相互矛盾的福利中,究竟为谁谋福利?而且是什么样的福利?
无论军事国家或福利国家都建立在一个原则上,即有计划地运用人力物力来达到一致同意的目标。这两种国家发展到极端必然会在国内形成两个集团:受役使的人和看管和使用这类人的管理者。在这种情况下,在管理人员之间就达到什么目标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就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这就可能需要独裁。事实上,到1952年时,俄国的社会已经接近这一极端了。
任何珍视个性的人必然会认识到这种演变的后果而感到害怕。幸而通过推理而假定的极端,即使曾经出现过,也极少在实践中成为现实。我们可以有信心地期望:不管上述社会革命有任何进一步的发展,古老的、不合理但具有奇特魅力的旧时代的残余将继续存在。恐惧和疑虑不大可能使已经建立的事物化为乌有。人们已经知道能够做到的事情,他们希望至少得到有意识的社会管理所产生的某些成果。只要世界上继续存在对抗的主权国家,对敌人的恐惧始终会鞭策落后者,使他们在有计划的协调与合作方面作出新的努力,以求获得更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永远虚幻的“安全”。
这里值得着重指出,大战期间在有意识地操纵社会行动方面获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即使所用的合理计算方式是临时的、粗糙的和现成的,例如在英美采用的那些方式,它们也相当突然地使过去不可能达到的生产指标、不可能进行的后勤工作与军事行动都变得可能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