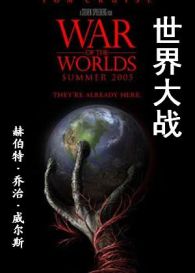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53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政府同报界之间的这种关系,可以看作不过是英国人在进行战争的各个方面所能取得的全面协调中的一个特殊的例子。报纸越能响应官方的意见,政府在同朋友和敌人的关系上就越能享有一种较为自由的活动余地。但是这种控制不是强制性的控制:只有在政府能够用内部情报和正确论据说服新闻记者的情况下,新闻记者才会遵照政府的愿望行事。因此,政府的活动自由远不象苏联那样广泛。在苏联,政策的任何变动肯定会受到报界的欢迎和辩护。说得恰当一些,英国记者同议员一起,是一般公众享有特权的代表,政府有时在实际方面,有时在法律方面,都不得不设法取得他们的赞同。
在现代政治中,个人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然而,正如罗斯福控制着美国政府并给予美国政府一种特殊的性质那样,丘吉尔从1940年5月成为首相的时候起到1945年7月他卸任的时候止,也对整个英国政府的领导起了深远的影响。
丘吉尔作为联合内阁的首相和国防大臣,法律上对他所处的地位的限制,比罗斯福受到的限制为大。根据美国宪法,总统对许多决定单独负责,而同样的决定在英国就得由全体内阁成员共同来作出。在罗斯福同丘吉尔的定期会议中,一个经常出现的特点就是,常常需要把会谈中的建议提交伦敦的内阁审查。诚然,丘吉尔通常能够说服内阁同意他所提出的建议,但内阁始终还是可以要求对那些提议表示拒绝或修改的。
因此,从内阁政治制度来看,丘吉尔个人对英国政府所有部门的控制,不可能达到罗斯福控制美国政府的那种程度。每一位大臣都有他自己特定的活动范围,而丘吉尔所选定的活动范围就是军事,他作为国防大臣,同海、陆、空三军的计划和主管人员经常保持着密切接触。我们只要粗略地检阅一下他亲手写的大量备忘录,就能为他的非常广泛的活动范围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了。
丘吉尔认为他本人完全有资格领导英国军事领袖拟订作战计划。他也积极地经常地同三军参谋长合作。但是,尽管丘吉尔不断地提出质问和下达命令去折磨他的军事助手们,尽管他感到可以通过军事部门传达下去,纠正他认为不得当的任何细小事项,但他是通过惯例和法律所明白规定的渠道去进行他的多种多样的活动的,这一点仍然是事实。他并没有象罗斯福经常所做的那样,越过各部大臣或者置正式的行政渠道于不顾。
总的说来,如果我们考虑一下美、俄、英三国政府的主要轮廓,那末,似乎很难否认,英国的官僚政治,在美国官僚政治的杂乱无章和俄国官僚政冶的前后紧密衔接、步调一致之间恰好是个中不溜儿。英国政府的中心目标和政策得到一种几乎是普遍赞同的支持。因而它只消象征性地使用暴力或强制的手段,便能够作出可以称之为“人的管理”的那种奇迹来。人口、财产、产品和价格全遭到空前未有的变动、控制和调节。一种接近于警察制度的极权主义政权,在没有割断把人民同政府联系在一起的那条自愿赞同的线索的情况下建立起来了。而通过自愿赞同完成了这样一次革命,这的确是英国政府战时的最大成就。在政府这方面当然需要果断与机智,但英国社会的异常团结以及英国在1940年面临的那种显而易见的致命危险,也是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要展望一下珍珠港事件发生时俄国的形势。就必然要遇到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首先是资料缺乏。在1952年,俄国并没有象英美最高统帅部一些成员所撰写的那种回忆录。在俄国,官方历史必然是令人可疑的,因为它是为了宣传的目的而随意重写的。俄国报纸以及斯大林和其他人在战时所作的官方声明,也同样值得怀疑。当然,俄国政府所采取的宣传方针本身,有时也可能是饶有趣味的,而它的宣传方针的改变就会反映出克里姆林宫内部人士的计划和意图的改变,这一点也是确实的。但人们不得不盲目地去猜测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假的或歪曲的,再不然,更慎重一点,干脆把问题搁起来不作定论。
就盟国之间的关系而言,根据英美方面的各种记载,可以约略知道斯大林与西方国家谈判时的举止态度。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如何解释的问题。斯大林所说的和所做的,究竟有多少是坦率地表达了他内心的思想和愿望?有多少是他为了打动外国客人而故意披上的伪装?斯大林简直不能被描绘成一个可信任的人,如果认为他在某个时候并没有故意哄骗他的来访者,那就未免过于轻率了。
的确,斯大林似乎可能是一个十足的两面派,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他显露出来的面目到底哪一面是“真的”,哪一面是“假的”。这种在两个角色之间踌躇不决的情况,在政冶家当中是很常见的,他们往往采用一种最适于吸引或打动当时听众的伪装。但在连续扮演两个角色之间,其矛盾程度则有变化,即有些政冶家比其他的人更接近于前后一致。但斯大林作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作为俄国统治者——且不提他可能扮演过的其他角色——是大不相同的,而且常常是互相矛盾的。要决定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那就会把个人与政治心理状态的神秘过于简单化了。在这些领域里,逻辑上的统一律既不适用也不应该用作为一项准则。
当我们致力于叙述俄国民众的态度时,也发生了类似的、同样不可克服的困难。俄国人自己只能利用官方的表达渠道,这些渠道是经过设计而且受到指导和控制的。普通人同外国人的接触都遭到警察有系统、有效的阻止。因此,外国记者的新闻报道价值是有限的,而且由于战时从俄国发出的电讯受到极其严厉的、有时好象毫无道理的新闻检查,所以价值更为有限。
当战时盟国之间的紧张和敌对情绪变得尖锐的时候,任何一个人要动笔写作就会遇到另一种困难。人们几乎不能不根据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战时的历史,探索1946年或1947年以后普遍存在的紧张局势的迹象,并忘掉或低估战争年代盟国之间“要什么给什么”的关系。但是在1941年和1942年,德国的失败还未成为定局,在1943年和1944年,大联盟的解体也还看不出是不可避免的,而在1945年和1946年,把世界划分为共产主义地区和非共产主义地区的分界线也还没有明确地划出。面临这些以及无数较小的捉摸不定的事实,盟国政府不得不尽力而为。如果设想在1952年为大家所知道的这种结果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认为这种结果是由盟国的一位领导人或一国政府“那样安排好的”,那肯定是大谬不然的。
概括地说,对于苏联政府的政策可以采取两种对立的看法。一方面,他们的行动可以解释为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应用,不论这种应用多么歪曲了原意。在国际事务中,这意味着,第一是保护社会主义祖国,第二是在全世界煽起无产阶级革命。根据对俄国政策的动机作出的这种解释,苏联与非共产主义国家之间唯一可能的关系就是一种敌对的关系,这种敌对关系有时是隐蔽的,有时则是公开的。一时的形势可能需要同其他国家结成联盟或进行表面的合作,但是这样的结盟是暂时的,是一种假象,而不是真相。
这可以称之为阴谋论: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来,资本主义正阴谋包围并推翻这个苏维埃国家,而反共产主义则看到一种威胁要发动世界革命的巧妙地伪装起来的红色阴谋。缩短成这样夸张的语言,这种理论当然过于简单化了。不过人们越是倾向于简单地生动地并用阴谋与反阴谋这种概念去看事物,这样一种理论就越可能呈现出相当大的真实性。在人类事务中,人们经常设想出他们最恐惧或最希望的事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好象他们的情感是以事实为根据的。由于他们自己的行为(以及别人的相反的行为),他们相信的事物,不久就变得至少有几分是真实的了。所以,我们不能不加思索就摒弃俄国所提出的阴谋论,也不能轻易就否认类似这种理论对俄国及俄国以外的官方决定已经起了作用,而且继续在起作用。
对俄国政府行动所作的第二种总的解释,则摒弃意识形态和阴谋论,认为它们是口头虚构,旨在哄骗天真无知的人们。相反,现实政治,即追求权力,以及安全地享有权力,这些都可以提出来作为对苏联迂回曲折的政策一种充分的解释。根据这种看法,苏联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和通常存在于民族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差别。俄国的统治阶级或集团愈觉得自己的政权不巩固,他们就愈变得不安,于是通过自我约束(即通过党),并辅之以宣传和警察,以争取获得国内的安全。与此同时,统治者则通过联盟、领土扩张以及军备来追求国外的安全。
根据这种看法,苏维埃政权的特点是来自困扰着统治集团的那种持续不断的不安全感。强烈的不安全感导致斯大林和他的顾问们对国内政冶及国际事务的政策作出剧烈而突然的改变。比较稳定的政权,如美国或英国存在的那种政权,对内对外都已在较长的时期内稳定下来,不致被迫在政策方面作出比较激烈的改变。但是,尽管有这种差别,我们仍然可以争辩讲,实质上到处都是同一个动机在起作用:民族的利己主义以及统治阶级或集团(如目前所理解的那样)的利己主义支配着一切掌握权力的团体;政府领导人所唱的高调和道德或政冶原则,事实上只不过是一种手法——在某些情况下,或许是不知不觉地使用的——凭着这种手法更容易使群众服从。
尽管在极端的形式下,这种理论事实上显然也过于简化,但是认为这种理论不屑一顾,那也是错误的。政府毕竟要尽力去维护自己的权力,而且只要有机会更要增强这种权力。同时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