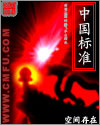中国现代文学史-第8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感觉是很难写得出好剧本的。”(注:《曹禺创作生活片断》,《剧本》1957年7月号)同时他又认为他自己的戏应该作到为普通的观众所了解,“只有他们才是‘剧场的生命’”。这也表现了曹禺对群众的重视,他和那种主张一个内行人的认识重于一戏院子groundlings的称赞的人完全不同(注:参阅《〈日出〉跋》groundlings指贱价买票、站着看戏的人们)。所以他的作品能够牢牢地抓住人心,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
曹禺的作品的出现,标志了“五四”以来话剧创作上的新成就,不只有当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推动了话剧创作水平的提高和发展,而且在长期的舞台考验中得到了人们普遍的爱好,一直保持着巨大的魅力,他的《雷雨》、《日出》等优秀作品为现代文学剧本创作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巴金、老舍、曹禺,一般被称为民主主义作家。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起点出发,经过各自不同的道路,摸索前进。革命形势的推动,中国共产党直接间接的领导和影响,使他们越来越密切地与人民革命的洪流结合在一起。他们的作品,以主要的篇幅暴露诅咒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黑暗和罪恶,同时也严肃地探索着人民解放的途径。这些作品以其在艺术上刻苦认真所获得的优秀成就,成为现代中国新文学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十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创作(一)
第一节:蒋光赤和早期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作家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迫切地要求大革命失败后处身于白色恐怖环境中的作家振作精神,鼓起斗志,从创作实践方面做出努力,及时反映工人农民的生活,反映革命人民的英勇斗争。适应着这种要求,太阳社、后期创造社等的刊物上相继出现了一批新的作者和作品。这些作者大多从实际斗争战线上撤退下来,程度不同地受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风暴的洗礼。借用蒋光赤《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一文里的话,他们是“在革命的浪潮里涌现出来”的,“富有革命情绪”(注:载《太阳月刊》1928年1月号),创作上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色。在这些作者中,写作最早、用力最勤、影响较大的,正是《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的作者自己。
蒋光赤(1901—1931)又名光慈,出身于小商人家庭,五四运动时在芜湖参加学生运动,一九二一年赴苏联学习,一九二四年回国。早在这个时期就开始写作新诗。他在自己的第一个诗集《新梦》的自序中说:“我生值革命怒潮浩荡之时,一点心灵早燃烧着无涯际的红火。我愿勉力为东亚革命的歌者!”集中的作品,有抒写诗人为探求革命真理而出国的情怀,有歌唱自己在新的生活中种种欢欣的感受,也有向“痛苦的劳动兄弟”倾诉激情的篇什。《新梦》是我国现代文学中第一部为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活放声歌唱的诗集。作者歌颂红军;歌颂苏联少年儿童;为列宁的逝世而感到最大的哀痛。在《临列宁墓》中,他赞美列宁“如经天的红日”,说列宁安卧“在克里母宫的城下”,“远观世界革命的浪潮,近听赤城中的风雨”。在《莫斯科吟》中,他为十月革命热情歌唱:
十月革命,
又如通天火柱一般,
后面燃烧着过去的残物,
前面照耀着将来的新途径。
哎!十月革命,
我将我的心灵贡献给你吧,
人类因你出世而重生。
作者意气风发、情绪高昂,诗歌格调宏朗奔放,即使怀念“沉沦”的祖国,也仍然号召以斗争夺取胜利。《新梦》出版于“五卅”前夜,对当时的知识青年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蒋光赤回国后,来到“黑暗萃聚的上海”,于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写成诗集《哀中国》。帝国主义、军阀蹂躏下人民的苦难和现实的黑暗,使他深感痛苦,而亭子间生活与群众革命斗争的一定程度的脱节,则使他不免在一些诗中流露出惆怅忧伤的情绪。“海上秋风起了,……满眼都是悲景呵,”“江河只流着很鸣咽的悲音,山岳的颜色更惨淡而寥落!”(注:分别见《海上秋风歌》和《哀中国》两诗)但诗人并未被这些压倒,面对着正在高涨的群众运动,逐渐地转为兴奋,转为顽强。在“五卅”惨案周年纪念日,他写出了充满愤怒情绪的诗章,要求以新的方式与敌人展开斗争:
顶好敌人以机关枪打来,我们也以机关枪打去!
我们的自由,解放,正义,在与敌人斗争里。
倘若我们还讲什么和平,守什么秩序,
可怜的弱者啊,我们将永远地——永远地做奴隶!
——《血祭》
而在稍后的《寄友》一诗里,他更意味深长地写道:“朋友,我觉悟了,我们要把枪柄拿到自己的手里!”这些质朴无华的诗句,反映了诗人对必须坚持武装斗争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的认识。《哀中国》总的说来比《新梦》深沉,有着更为踏实的现实的基础。
一九二五年以后,蒋光赤以较多的精力从事小说创作。中篇《少年飘泊者》,作者自称是在“花呀,月呀”声中“粗暴的叫喊”。它写农村佃户少年汪中,因父母被地主所害,流浪异乡,经历各种遭际,最后走向革命,牺牲在战场上,通过汪中的流浪历程,小说展现了“五四”到“五卅”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和斗争,洋溢着分明的爱憎,有较强烈的浪漫主义色采,在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流露了不健康的思想感情。一九二六年所作短篇集《鸭绿江上》,共收小说八篇,借不同社会生活的描写,反映了民族、阶级之间的不平,革命倾向相当鲜明,但有些部分(尤其是写爱情故事的部分)也具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调。其中《鸭绿江上》、《弟兄夜话》等篇较有特色。
一九二七年四月初,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不到半月,蒋光赤完成了中篇小说《短裤党》,及时地反映了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作品主要描写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经过和失败,最后勾勒出第三次起义成功后的胜利图景。写到的方面较广,包括党内活动、工人群众会议、武装斗争、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屠杀罪行等,这一切又都围绕着起义斗争的发展而进行,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的面貌和当时的社会气氛。作品着力描写斗争的领导者杨直夫、史兆炎的坚定、忘我的光辉品质。他们较早就指出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杨直夫出于对革命事业的责任感,身患重病而坚持工作,写得颇为感人。作品还写出了工人李金贵、邢翠英等勇往直前,不畏牺牲的英勇气概,歌颂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描写这样重大的题材,描写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形象,这在当时文学创作中是难得的尝试。作者写作时为“热情所鼓动着,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在做小说”,立意要使《短裤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证据”(注:《短裤党·写在本书的前面》),这里也表现了一个革命作家可贵的责任感。作品还存在一些缺点,例如个别人物身上表现了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肯定暗杀复仇的行动;由于作者写作时间过于匆促,而又企图较全面地反映起义斗争,来不及熔铸和精细琢磨,因此缺少比较完整丰满、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作者这时的一些小说具有共同的缺点:常常以热情的叙述代替对现实生活和人物性格的细致而具体的描画,结构不够谨严,语言也缺少锤炼。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作者辗转沪汉,较多地看到了现实生活中蜕化或没落的方面,对于工农群众力量估计不足,心情悲愤而又低沉,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消极影响。《野祭》中的青年有的在革命的浪潮中退却,有的在继续斗争中牺牲;《菊芬》中的人物的斗争失败后以暗杀作为反抗现实的手段;《最后的微笑》也只能以自杀来结束斗争。这些作品,虽然仍表现了作者对敌人的强烈憎恨,但气氛比较沉重;早先作品如《少年飘泊者》、《鸭绿江上》中还不算显著的所谓“革命与恋爱”的表现,此时也有了发展。作者思想上的消极倾向在《丽莎的哀怨》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这个作品描写一个白俄贵族妇女在十月革命后流浪到上海,最后沦为妓女的故事。小说过多地渲染了丽莎昔日的荣华富贵和眼前生活的沦落,它所采取的自叙形式,使人物的哀怨显得深切,作者对此又缺少必要的批判。因此,作品给予读者的并不是对于俄国贵族的厌弃和憎恨,反而是对于他们的怜惜。小说受到革命文艺界的批评。
作者这时对于革命发展虽怀有疑虑,但又始终关注着它,并不曾放弃自己的革命要求。即使如《野祭》、《菊芬》等作品,故事背景也仍是当时动荡的革命现实;同时期写的长诗《哭诉》(即《写给母亲》),感情虽嫌忧伤孤寂,但对反动派表示了极大的愤怒。作者这样剖露自己:“我的一颗心,……只是烧呀,……任冰山也不能将它冷透!”在序文里更为明确地表示了自己虽受创伤而决不屈服的心情:“我始终是在希望的路上走着。”正是这种坚定的革命感情保证了作者此后在思想上和创作上的新的发展。
这段时期内,作者实现了在一九二四年组成“春雷社”时就提出的以办刊物来“振作中国的文学界”的愿望(注:见通信集《纪念碑》(1924年11月3日信),亚东图书馆1927年11月出版),与钱杏村、孟超等人组织太阳社,主编《太阳月刊》,提倡革命文学,做着“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基础的工作”(注:《停刊宣言》,《太阳月刊》停刊号,1928年7月)。《太阳月刊》停刊后。蒋光赤又先后主编《新流月报》、《拓荒者》等,明确地“想对目前的如火如荼的新时代文艺运动,加上一点推进的力量”(注:《编后》,《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