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心的日子-第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挑滑竿的人
在我所去的地方,峨嵋山是给我印象颇好的。它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美,飘逸、俊秀、清朗。山上有泉水,整个美就灵动起来了。泉水清澈,清音阁里余音袅袅。满山的青翠,浓郁与淡雅错落有致。峨嵋山上的猴子恐怕是别处没有的景致了,那些猴子已不是精瘦灵活的样子了。由于每日都有大批的游客上山,猴子的食物是异常丰盛。它们根本不需要再去从游人手中抢夺食物,仅是游人抛向它们的各类食物就能让它们饱食终日了。见到的猴子都是胖胖的。很多小动物都可以胖胖的,很是一份鞠态可爱的样子,唯有猴子,一胖起来就有一种不伦不类的样子。
峨嵋山的那些生意是让人生厌的。住旅店的人漫天要价,他们也知道游客总是要住店的,总不能与猴子共憩,于是这种唯一的选择给了他们大发横财的机会。还有各种专门卖药材的人,打的都是山中奇珍贵宝的幌子,到处兜售或蒙骗旅客。更有各种神仙纷纷下山,说是得到峨嵋仙人的真传会占凶卜吉,常常莫名奇妙地胡说一通就算是为你算了一卦,然后强行索要高价。这也算是峨嵋山上的独特风景吧。难以忘怀的景致和人生百态的缩影固然是游峨嵋的收获,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却是那些挑滑竿的人,我回来以后,那些挑滑竿的人的一举一动还时常印入眼帘,我也不知道我为何会对此会如此诸多感触。
所谓挑滑竿,是指为了帮助那些爬不动山,或爬上去又因劳累走不下来的人准备的一种工具,是用竹子和麻布编织成的一种轿子。通常是四个人合作。从峨嵋半腰到山顶,坐一次滑竿大约要支付二百元。下来差不多只要一百元。我并不是体力极旺盛的人,可我毕竟年轻而且体健,我只带了一个小背包,爬到半腰时已经气喘吁吁。越往上越感到艰难,以至于后来腿就象踩在棉絮上。好在,处处有风景,让人驻足观望也不至于乏味,这样慢慢地爬边看边走还是可以的。我看到一对来自加拿大的老夫妇,携手相依地走了好久。我问他们为何不坐滑竿,他们说:“不忍心!”这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年轻人不坐滑竿是因为尚有余力,年老人因体力不支坐滑竿而上是很正常的事,滑竿本来就是为他们而准备的。再看一下那些挑滑竿的人,清一色的都是年青男子,皮肤晒得黑得发亮。上山时,汗水象雨一样一路淌过。而且还得保持一定的速度,太慢了反而受累也要遭客人的指责。后面的两个人更是辛苦,要把滑竿高高举过头顶以便和前面的两个人执成一个水平面。这样,坐滑竿的人才能平躺。我对他们的体力和吃苦的精神是绝对佩服的。我本来只是为了这些挑滑竿的人为了求生存的一种无奈中的选择而感悟,可是那对老夫妇,一对来自异域的加拿大老人提醒了我。再看看那些坐滑竿的人吧,极少有因体力不支爬不动的老人,相反都是一些年青人。他们有的根本没有爬,从山脚开始就请人抬上来,他们是来享受这份侍候的。彼此嬉笑着一路而过,也没有对峨嵋景致留恋忘返,全部的乐趣就在这坐滑竿的过程中享受尽了。看到一位特别健硕的男子,完全像个运动健将的样子,他坐在滑竿上的那一瞬间,挑滑竿的几个人起初的步子都有点打虚,渐渐地才稳实起来。那二个加拿大人问我What's wrong with him?我无以回答,他没有病,他很健康,他是在追寻一种快乐。
在那二个老人看来,健康的人却要让别人付出如此巨大的痛苦来抬上去,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理解他们为什么说“不忍心。”那些挑滑竿的人,一路上拿着滑竿几乎是央求游客来坐,价格一降再降。因为挑一次滑竿所挣得的钱对他们而言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平均挑一次每人能分到四十至六十元,运气特别好且体力旺盛的人一天可挑二三次。他们也只有趁着夏季是旅游旺季才可赚到一些钱。一年四季的指望也就在这三四个月里了。他们觉得自己的劳动能换来这样一笔钱是太合算了。想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有些自嘲,我简直是在杞人忧天,倘若没有人去坐滑竿,那些挑滑竿的人一定是愤怒的。我觉得我的想法近乎有些荒唐得可笑。本来嘛,坐滑竿的人为挑滑竿的人提供了生存机会,没有挑滑竿的人,坐滑竿的人可以靠步行上山,但若没有了坐滑竿的人,挑滑竿的人也许生存就要面临困境了。我没有办法向那对加拿大老夫妇阐明这一切,这也是他们无法理解的残忍。
从山顶往山下行进的时候,挑滑竿的真面目才让我领略到一份惊心动魄。先是前面有二个人开道,一路是大声吆喝:“让开——让开——,”既而后面挑滑竿的人急速而下。
由于下来时有一种惯性,况且肩上又抬着人,只能是一路横冲直撞下来。本不宽敞的山坡上到处是游客,开道的两个人就是为了让众人让开一条路。偶有躲闪不及的被撞着是常有的事,你还没转过神来,他们已经下山很远了。我真的是既为挑滑竿的人提心又为坐滑竿的人提心。坐滑竿的人被一根绑带拴住,一般是不会从滑竿上飞出去的。但那些挑滑竿的人万一脚下打滑,不仅自己会连滚带爬摔下去还会将坐滑竿的人连人带滑竿甩出去,到处都是山崖,后果不堪设想。我不知道有没有出过这样的事,可看看就发怵。原来坐滑竿的人多少也是要有点“不同寻常的勇气”的。
我爬山上去又从山顶下来,一路上不断有滑竿从身边走过。我看到的汗流浃背的挑滑竿的人和春风得意的坐滑竿的人。坐在山旁的石头上休息。看到有一个已经上了年纪的男子也在休息。他大约已近六十岁了。他的身旁有一堆半人高的砖,绑得好好的,显然他是要将这砖搬上去。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以此为营生的。山上有人要盖房子,需要有人把砖搬上来。这样一堆砖差不多近一百五十斤,搬一次可得二块钱。他一天只能搬二次——实在是太累了,一天可挣四块钱。我非常惊讶,怎么会只有那么少的钱。我不加思索道:“既然如此,你还不如去挑滑竿。”他沉默了片刻说:“挑滑竿的人都结成一派,只挑年青人做,况且我也老了,万一脚下打滑是要出人命的。挑滑竿的人赚得是游客的钱,游客反正也有钱,我赚得是山上人的钱,山上人本来就穷,二块钱一次已经很好了……”
凯恩斯说,“……人类的需要可能是没有边际的,但大体能分作两种——一种是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感到必不可缺的绝对需要,另一种是相对意义上的,能使我们超过他人,感到优越自尊的那一类需求。第二种需要,既满足人的优越感的需要,很可能永无止境,但绝对的需要不是这样。
挑滑竿的人和坐滑竿的人之间是一种绝对需要对相对需要的需要,这种需要的互补达成了一种平衡,诧异、忧郁担心、感叹都只不过是一阵夏风,对平衡的磐石不起任何作用。
——反正,就是这样的了。
永远的遗憾
经常会从杂志社的编辑手里接到一些由他们代为转交的读者来信。每一封我都仔细地看过,然后收起来,留在一个大匣子里。我把这些本不相识的人对我的尊重和关心好好地保存着。可我几乎从来不回信,每每想提笔写点什么可总也想不出该怎么写,于是就作罢了。
那一次,有份杂志在内页的第一页上登了我的照片和介绍我的一些文字并且留了我的学校地址。这一次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一下子涌了过来,仅寄到学校的就有几十封。我如往常般慢慢地读着我所收到的读者来信,有一封是最特殊的。这封信来自内地的一所监狱。信封上盖有一方宽整的蓝印,上面印着XX劳改局。来信的是一位年愈三十的男子。他是因盗窃罪而被判了六年徒刑。他在信上说,他原先是内地一所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毕业的,喜欢文字酷爱创作也曾经发表过作品。无奈大学毕业的第三年,因误入岐途,邪念缠身而参与团伙盗窃,因此而沦为阶下囚。他从那份杂志上看到了我的文章和介绍我的一些资料,他们狱中的图书馆订了那份杂志,我那时经常为那家杂志写点小文章,他因此而写信给我。信写得很长,有八页纸。写他的过去,写他的悔恨,写他在狱中的痛苦和反思,写他苦捱着盼出狱的那一天,写他对文学的执着,也写他对我文章的喜爱。我不知道他们的信寄出来是否需要经过审查,我也不知道审查的人读了这封声泪俱下的信会是怎样的感受。信写得酣畅淋漓,文笔流畅生动可见到他很不平常的文学功底,字写得尤其得好,挥洒自如又不失工整。在信的最后他说,今年他就要出狱了,恳请我能够给他回一封信。他一出狱后就到上海来见见我,希望我能把家庭地址给他,他要到家中来拜望我,和我好好谈谈文学。
我一口气读完他那长长的来信,没料到一个在那样的环境下生活了好几年的人,依旧是没有磨灭掉一份充满渴望的执着。他给我留下了他所在劳改局的地址以及他所在编队的号码。尽管我多少被他打动了,可我还是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尴尬,不知道该不该给他回信。晚饭的时候,我随意地向父母提了这件事。父母的反应较我强烈得多,劝我不要惹麻烦,至少家庭地址不要写。写一封回信给他问一声好是最妥当的做法。我应允下来,也就准备这么办了。
这期间,各种各样纷扰的事太多,我实在无暇顾及。写回信的事也就耽搁了下来。后来,一切都忙完之后,我几乎就要把此事给忘了。一次去杂志社,又从编辑的手中接过一些读者来信。他的来信比第一封更长,大意是怕我没有收到第一封信就再寄了一封请编辑部转交的,信的内容和第一封相差无几,只是又写了新近的一些情况,他的表现很好,受了表扬。随信还附了一篇散文,是写他如何思念父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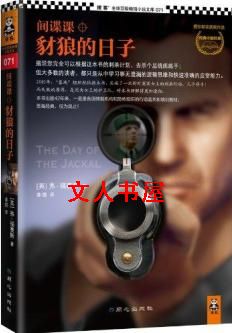
![[进击的巨人]和兵长比身高的日子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3/3827.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