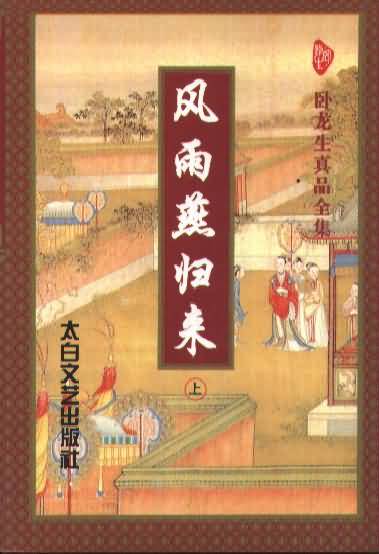风雨六载-第4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也真巧,打完松日后,我们下一轮的比赛就是到广州,客场打广东宏远队。
到了广州,利彪又来找我,说潘苏通要请吃饭。我说,这时候吃饭不太合适。他说,那么来拜访总可以吧?我说,要来就到我住的流花宾馆来吧。
这次潘苏通来流花宾馆,谈得比上一次深了。潘苏通问我:“徐教练,上次我对你谈的事你有没有考虑过?”
我当时已经很认真地考虑下一步该去哪里了,那时邀请我的不止松日一家。在打完与松日队的比赛后,北京国安俱乐部总经理张路也打来电话询问:“根宝,你有没有可能到国安?”我说:“什么意思?你们是不是准备换金志扬?”张路说:“上面有这个意思,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你到北京来后我们再谈。如果没有的话,就到此为止了。”1996年金志扬带领国安队在甲A比赛中的战绩很一般。我当时也没有给张路明确答复。
潘苏通这次与我的谈话比第一次更直接、更深入,讲到了我的待遇问题,讲到队伍的问题。我当时抱定的原则是,什么都可以谈,但什么都不能定,包括去北京国安队的事。
“广州会谈”结束后,10月27日,我到北京,与北京国安队进行1996年度甲A的最后一场比赛。到北京时,我已经基本定下了下一步的方向。我与张路正式会面并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我对他说:“谢谢看得起我。但是搞了三年甲A,确实比较累了,是不是我就不来了?”
到北京之前,我征求了很多朋友的意见。他们都告诉我,北京这座城市与别的地方不同,各方面的要求都非常高,北京的球队也不太好搞,压力太大。我听了触动很大:这三年来搞申花队,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么大压力,难道还要跑到压力更大的地方去吗?而南方的广州相对宽松些,压力也轻。再说,广州的足球不太景气,只要好好搞一下,是很容易出成绩的。经大家一说,我觉得非常有理。于是便决定,如果我离开申花的话就去广州。这时,我已经不看重甲A和甲B的名分上的差别了。脑子里只是想,如果能把甲B的球队带上甲A,不照样能显出我的本事吗?而且觉得这个目标并不是做不到。我对自己挺有信心,相信经过我的调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再说,这样的缓冲对我的事业也是有必要的。当然,这还只是想法,到底去不去还没有最后定。这段时间松日队与我的电话不断,我也很认真地与他们谈着各项条件。
3。签下台同,潘苏通鼻子突然出血不止
我正式决定离开上海去松日,是在不久后上海市体委主任金永昌和足协秘书长胡康健找我谈话后。他们找我谈话,“正式”透露了申花队明年可能请外籍教练,并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考虑了半天后说,如果让我当主教练,我干。如果不干主教练,我就离开。我不愿意对新上任的主教练和队员有什么影响,我的性格也决定了不可能干那种在别人手中讨饭吃的活,我害怕别人对我怜悯,这种施舍对我来说,是一种侮辱。我徐根宝再落魄,也还没到这个份上,请我的还大有人在。自此,我在申花的日子进入了倒计时。
11月11日,申花队在汉城打完与韩国LG队的友谊比赛后,郁知非告诉我,根宝你知道吗,你离开申花队要惊动多少人啊!
他还告诉我,申花惧乐部宣布我离开的新闻发布会的时间是11月14日,也就是我们回到上海以后。我听后没有说话,心里突然涌起一股难言的滋味。不管怎么样,我在申花这三年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申花队给了我重振旗鼓的机会,我也没有辜负俱乐部和家乡人民的希望。当真的要离开为之奋斗并取得一些成就的家乡时,那种心情是别人无法体昧的。我虽然一生在外漂泊,东奔西走早巳习以为常,但这一次不知怎么搞的,我忽然觉得自己像个软弱的孩子,有一种被别人抛弃的感觉。我甚至默默地对自己说,申花,我终将回来,以我的实力让你们再请我回来。
11月14日,在申花俱乐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俱乐部向新闻界正式宣布我离开申花队的消息。我记得参加那次发布会的记者很多,尽管大家在事先都已经知道了我要离开的消息。在新闻发布会上,大家对我的未来非常关心,都问我将去哪里?我没有正面回答,因为我知道这事还没有完全定下来。但我还是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我的去向在上海的南面;二,我去的队不会同申花队比赛。据此,他们已经猜出我的大致去向。那次新闻发布会给我的印象挺深的,当会议结束后,许多以前一直攻击我的抢逼围、对我好像也不够友好的记者,跑到我面前,和我握手,说一些道别的话。那时候,我甚至有这样一种感觉:是足球扭曲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而一旦当这种关系不存在时,我们之间竟可以变得那样轻松,像朋友一样愉快地交谈。
15日,潘苏通从广州飞来上海,一个人悄悄地住在新锦江大酒店。我们的这次谈话就更加直截了当。只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谈判,就达成了最终协议。由于在此之前,我与潘苏通和俱乐部人士的电话联系没有断过,话题早已牵涉到假若当教练,应该担负的责任和应该拥有的权利,以及我的待遇等问题。因此这次在新锦江的谈话,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需要解决了。那时,潘苏通还要让我当副总经理,他说,当时的总经理古广明的合同大约明年3月就要到期,到时候他要我担任总经理,把一切权力都交给我。
谈判很顺利地结束了。我们两个当即就在房间里摊开合同签字。没有什么仪式,也没有祝贺的人群和香摈酒,我们两个一人拿一枝笔,就在合同文本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签完字后,潘苏通的鼻子突然出血了,大量的血从鼻子里流出。他几次跑去洗手间用纸塞住鼻子,但仍然流血不止。我吓了一跳,问他:“你是不是上火?”
他说从来没有过的,他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心想,潘苏通是不是太兴奋了?
后来潘苏通到美国后,有一次与人谈起这事,说他不明白那天与根宝签字时鼻子为什么会突然出血,因为在生意场上签字时从来没有发生过。有一位先生对他说,那个人(指我)的命硬,压过了你。后来潘苏通告诉我说,我们两人的命都硬,但你压过我。我当时听了一笑了之,并没有放在心上。后来在松日冲击甲A成功后,有报纸写“根宝命硬,松日大难不死”,看来,我的命确实够硬的。
4。王后军突然“辞职”,蔺新江紧急“补位”
自合同签字后的那一刻起,我便是“松日的人”了。我的目标是冲甲A,这是不容置疑的,否则人家不会花那么大力气请我。潘苏通给我的职务是惧乐部副总经理兼主教练。球队一切的一切,从队员到教练班子全由我组织。
尽管与松日惧乐部签字了,但我一时还不能离开申花俱乐部,因为还要带队去西班牙参加世界室内五人制足球赛。申花队是亚洲区唯一获得进人世界杯决赛圈的队,俱乐部要求我打完这个比赛后再离开。播苏通的意思,我先把班子搭好,队伍先去昆明冬训,等我西班牙比赛结束后再到昆明。我们还就班子的组建进行了一番探讨。我问他,你们广东有没有合适的教练?他听了忙摇头说:“广东的教练你一个也不要用。”我问为什么?他说:“这一点你只管听我的,弥来之后工作上我大力支持你,但是只有这一条,广东教练你一个也不要用。”
他这么一说,我只能放弃用广东教练的念头。但是,谁跟我搭档去松日呢?我干了几十年足球,深知一个教练班子对球队建设的重要性。尤其是我先去西班牙时,必须有称职的人带一段时间。选谁呢?我在苦苦思索。
忽然,我想到了过去的同窗战友王后军。他由于带领福豹足球队冲甲B没有成功,现正在家闲着。能不能用他呢?
王后军1965年与我一起调入国家队,我们一直踢到七十年代。各自当教练后,相互间也一直有书信联系。我搞国二队、国奥队时,在选队员上他对我一直很支持。我两次竞选国家队主教练,一次北京西山的预备会,一次在昆明竟选会上,他都投了我的赞成票。我和王后军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外界所说的那样“不行”。王后军自己也说,“我与根宝的关系是不错的。”我们关系出现紧张是我到上海担任了申花队的主教练以后。别人感觉是我把王后军的饭碗给抢了。
王后军那三年的教练生涯确实不顺利,他先后执教过浦东队和福豹队,但由于种种原因,成绩一直不理想。1996年时,他正赋闲在家。王后军的能力也是众所局知的,他担任上海队主教练多年,在足坛有“小诸葛”的美名。我非常需要一个我不在的时候能够拿得起的助手,王后军有这个能力。考虑再三后,我决定请老王出山。我曾为此征求许多人的意见,他们的第一个反映是“想不到”。当我与王后军通了电话,告诉他我的意思后,他一口答应了,并说他的身体没有问题,甚至“可以带身体训练”。他同时答应按我的训练计划去做。老王这么爽快的答应我,倒让我有点“想不到”。
我决定让王后军担任领队兼教练,同时还找了李红兵担任助手。另外,我还准备把高洪波和胡志军挖过来,他们都是我在国二队和国奥队时的队员。高洪波跟随我多年,他痛快地答应了。经过俱乐部出面工作,国安俱乐部也同意放人。当时定下的转会费是150万。胡志军答应要来,但是太阳神队硬是不肯放,结果转会没有成功。
我定完班子后,便与王后军联系,让他先到广州来带队。我把松日的计划大致安排妥当后,王后军这时赶到了广州。在我准备率申花队出征西班牙之前,王后军从广州绘我打来电话。他说:“这支队伍怎么这么差?”我说:“松日要我们去,就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