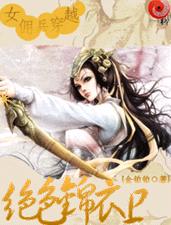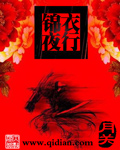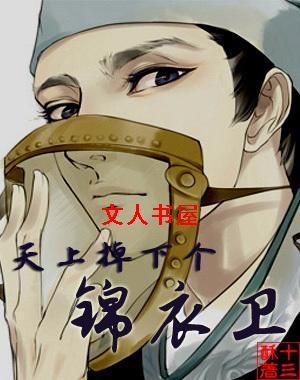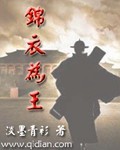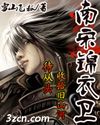锦衣王侯-第65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比霍韬更远,如果他真的是把这当成一次前程的赌博,那只能说,他一次就押上了自己全部的筹码。
“大哥,方献夫这个人,官职权柄都很一般,但他是王守仁的弟子,这次上本到底是他的意思还是王守仁的意思?会不会是那些信奉心学的,这次准备投机,要为朕出力?”
“陛下,这种可能虽然有,但是并不太大,也不必把希望寄托在这上。根据臣这里得到的情报,王守仁一直以来,都在广西那里抚夷,最近一段时间,他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上本,建议朝廷不要改土归流。至于和他京中弟子之间,并没有什么往来。方献夫虽然是心学子弟,但是心学这个学派不是江湖组织,约束力很差,所以他读过心学,向王守仁学过什么,都不能代表什么东西。就拿王守仁自己来说,他的态度,实际也是说不好的。说不定,在这件事里,他可能站在杨廷和一边。”
嘉靖现在还是想要扩充自己的力量,让自己的盟友多一些,与群臣的抗争中底气就能更充足。但是杨承祖希望通过这次礼议之争,让厂卫的力量达到顶点,自然不希望有不相干者入场分功,更何况王学的思想,与他将来要推广的帝王思想,也完全不在一个轨道上。
信奉心外无理的心学,并不尊奉皇权,或者说,心学更偏于一个哲学方向,在他们的思想领域,帝王并没有什么值得尊敬之处。杨承祖的历史知识平庸,但是穿越之前,剧团曾试图编排一出新编历史剧张居正,里面作为反派人物登场的何心隐,就是心学弟子。他可是推广过无君无父非弑君弑父这样的理念,在江南讲学,宣传蔑视天子权威之类的观点。有了这个印象在,他更不可能让心学通过礼议之争,走上朝堂成为显学。
他随后又道:“陛下,现在的局势,就是一个字,乱。我们可以尽快将大礼辨做好,配合这几份奏折,一起发放下去,交群臣议。如果议成之后,就可以尊奉先主为皇考,将孝宗改为皇伯考,慈庆宫里那位,可以改称皇伯母,然后赶到其他宫里去住了。”
“大哥是准备跟他们现在就摊牌了?”
“臣确实有此想法,如果再拖延一阵,就离秋天越来越近了,一入了秋,大臣们会拿出防秋的事出来说话,到那个时候,我们要顾全大局,他们未必需要,这个江山是您的,不是他们的。到那个时候,为了保证运转,做事反倒要被他们捆住手脚。所以事不宜迟,还不如现在就开始议,等到秋天,我们的人也都放到了位子上,不会影响太大的。至于抄录的事,就交给翰林院去做,杨慎就在翰林院里,既然杨廷和早晚都要知道这个消息,就不如让他儿子给他报信。”
嘉靖也明白,这是杨承祖建议公开下战书,向杨廷和发起挑战。整起冲突中,杨廷和还藏在幕后,但是根据厂卫那边反馈来的情报,所有反对自己建议的大臣,都奉杨廷和为盟主。这些天里,杨家宾客往来不断,全都是反对重修帝陵之人。再想到朝议那天,杨廷和一言不发,那些大臣就纷纷上前与自己打对台的情景,嘉靖咬咬牙“就依大哥之见,朕这就让黄伴将奏折拿到翰林院,让他们去誊抄。”
由于家里最近宾客太多,杨慎回到家里也要应酬这些人,并不能与妻子待在一处,这种迎来送往的接待,也让他觉得很没意思,索性就在翰林院没有早退。
作为国朝第一清贵阶层,翰林们的工作相当清闲,主要就是抄抄写写,再不然就是给天子做侍读,侍讲,值经筵等等。像杨慎这种大才子,抄写的活也轮不到他做,侍读类的事,嘉靖又不大喜欢找他,在翰林院里,他就属于闲人,四下走走,与人谈谈文章或是诗文,一天过的很是惬意。
朝廷里的局势已经明明白白,彼此的矛盾摊在桌上,这种矛盾不可调和,大家都有自己不能退让的理由。朝廷里的气氛,已经变的越发凝重,除非是那些敏感度低到一定程度的蠢人,大多数人都已经明白,现在争的根本不是皇陵该不该重修,也不是王府有没有必要再扩。甚至于承天府是否改成国都,都没那么重要,现在真正重要的只有一条,天子到底继承谁的血统,再说深一点,这个国家到底是天子与士大夫共天下,还是天子乾纲独断,一切就看这一朝。
翰林们在这种时候,基本都放弃了工作,读书人本来就崇尚清谈,身为翰林储相,这时就更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柯亭里,十几个宽袍大袖,气度雍容的翰林围坐一处,品茗谈心,个个壮怀激烈,满腔热血。杨慎身为大明第一才子,在这个圈子里,就是最受欢迎的那一部分,大家围着他,听着他的见解。
就在杨慎侃侃而谈,说的正起劲时,他的妹夫金承勋忽然从外面挤进来,将几份奏折放在众人面前。片刻之后,柯亭内一片哗然,群情汹汹。
第一千零一十二章逼宫
明朝此时还不像另一个时空里万历后期那样,读书人动辄结社,又通过这种结社方式彼此约为兄弟,共进同退,左右清议。但是这个雏形,已经初步出现。
像是翰林院这种地方,就曾经出现过翰林四谏这样的敢谏之士。可以说,每一名翰林心中,都藏着一个可以左右朝廷,指点江山的梦想,想要在权力的盛宴中分一杯羹。
看到霍韬和方献夫的奏折后,不管是出于对孝宗的爱戴,还是出于对离经叛道的不能容忍,又或者是看到了这里面蕴涵的巨大危机,在短时间内,柯亭内的十几名翰林,几乎同时都站在了杨慎一边。
“奸党,这绝对是奸党!方献夫人就在翰林院,我们把他找出来,问个究竟。我们读书人的风骨,就是被这样的人,全都给丢光了,如果我们不做一点什么,将来还有什么面目立于天地之间。”
十几名愤怒的翰林,在这时摆出的姿态,是要将方献夫撕成碎片,食肉寝皮的。金承勋与杨慎是同科进士,又是郎舅之亲,关系最厚。与一向率性的杨慎不同,他为人比较谨慎,急忙张开双臂,拦在众人之前
“大家不能莽撞,这里是翰林院,如果动粗的话,传出去丢的是所有人的面子。大家又不是街上的泼皮,不能遇到事就动拳脚,方前辈的意见,我是不赞成的,但是你们这样去讲道理,我也是不赞成的。咱们的武器是手中的笔,不是握笔的拳头,大家不能本末倒置。再者说,谁又知道,这件事会不会有什么阴谋,现在厂卫猖獗,大家不要中了他们的计策,被这帮鹰犬拿住什么把柄。”
冲动的翰林们,也渐渐冷静下来,作为天之骄子的他们,未必真的怕厂卫,但是在翰林院里动粗,也确实是有点丢人。所有人的目光转而看向杨慎,杨慎思忖一阵,也点点头“承勋言之有理,大家不可莽撞,这本章是陛下要咱们誊抄交百官议的,这事不能不做。不但我们要做,整个翰林院的人都要做,咱们要让所有的同僚知道,这些东西是谁写的。我现在去内阁,让父亲看看这些东西。”
内阁值房里,梁储、毛纪、蒋冕三人,本来去意已决,但是在杨廷和的反复劝告下,决定勉强再支持一阵,但是也已经不大管事。费宏的班辈本来不在杨廷和之下,但是两人的合作并不太愉快,杨廷和的行事思路和费宏并不相和,现在费宏已经很少来这里办公,在家中长期告病不出,很可能辞官辞的比另外三人还早。
顾鼎臣的科分辈分、名望还是手段,都不能和杨廷和相提并论,在内阁里,存在感极低。加上他是第一个在杨记入股的阁臣,弄的内阁里没人喜欢他,每天只是混日子。
最近百官议政,让内阁的工作量在原有基础上大为增加,杨廷和大权独揽的同时,也要承担远超常人的工作。除了这些朝政议论,地方上反应的问题,也从来没有中断过。南方的海贸,漕运,大户们对于杨记破坏市场的控诉,乃至于因为杨记买田、征地、造船等事,引发的一系列冲突,堆满了首辅的案头。
就在这种纷乱中,杨慎将那两份奏折的抄本递到了父亲面前,“父亲请看,这是万岁刚刚交到翰林院的,请父亲过目。”
杨廷和将两份奏折看了看,随手放在一边,“请你几位世伯看看吧,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天子想要什么,下面的人就给什么,大明朝最不缺少的,就是这种聪明人。霍韬、方献夫,他们只是开始,接下来,这样的人恐怕会越来越多。”
案头上的奏折里,原来有一部分会提到杨记害民,在地方为非作歹,乃至抢男霸女的事也时有发生。还有些地方民风剽悍,杨记在那里做生意,经常闹出人命。地方官由于受到限制不能处置,就把官司打到御前,请首辅做主。可是现在的奏折,这种内容已经大幅度减少,相反,倒是有不少地方,开始称赞起杨记为国出力,于国有功。
这些软骨头!杨廷和心里暗自骂了一声,顺带把霍、方两人,也都归入软骨头的范畴。这种奏折,其实也在他的意料之中。自科道互查以来,言官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同僚,查究不法的正事,没有太多人去做,还有人开始想着攀附权贵,保住自己的位置。曾经以节操风骨自夸的科道体系,正在逐渐走向崩塌。
随着事态的发展,早晚会走到这一步,如果不为了这个,也不会闹出这么大的事。现在天子的态度,是认为有了必胜把握,可以走到下一步了?
他冷笑了一声,难道下面一些人的声音大,就给了天子错觉,让他以为自己已经稳操胜券?那些六七品的小官,手上无权,品阶也低,一群蝼蚁般的东西,就算再怎么多,也没有实际意义。看来天子还是太年轻了,没弄明白什么叫胜负,自己有必要给他把这堂课补上。
蒋冕将奏折一放“这两份奏折,没有可议之处,如果连这样的东西都要议,那大家的时间,就都会浪费在商量这种荒诞言语上,国事又有谁去做呢?老夫的意见很明确,天子必须继承孝庙的血脉,不管他本人愿意或者不愿意,这一点都没有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