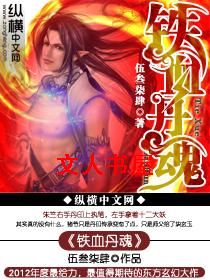集结号·铁血-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怯怯地看了我一眼,又飞快地把目光投向了旁边,但他还是伸出了一只手,让我把他拉了起来。他低着头看着脚下,他不敢看我了。他的脸上的表情有点奇怪,好像还有点懊悔和生气。他可能生气自己怎么能把手送给一个国军军官,让他把自己拉起来呢?我摇了摇头,我知道在解放军的宣传中,我们国军军官都是喝兵血的贪官,是无恶不作的恶棍。这听上去很带劲,但实际上它错了。我们和他们一样,血都是热的,头发都是黑的。
我当然不喜欢解放军,我最反感的是他们总把我们当作土匪来对待。
是的,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中,我们是“蒋匪”,在我们的宣传中,他们是“共匪”。我觉得这两种宣传都很愚蠢,实际上都没有把我们当作真正的军人来看待。在他们眼里,军人算什么呢,就是一群厮杀的蚂蚁而已。
整个战场都沉寂下来了,静得出奇,连地上的雪花融化嗞嗞地渗入地下的声音都能听见了。我突然觉得,整个双堆集,整个战场,就像一个巨大的坟墓,我们这些没死的人,其实都是一群活着的鬼魂。我已经厌倦战争了。我想起了远在确山那个偏僻县城的罗小姐,她红润的嘴唇,圆圆的脸颊,羞涩而胆怯地微笑着,她用目光抚摸着我,吮吸着我……
如果有可能,我更愿意死在她的怀中……
五
前黄埔军校生在绝望中迎来了十二月。天气更冷了。整个兵团已经彻底没有希望了。他作为一名基层军官已经知道了徐州的杜聿明、邱清泉等四个兵团也好不到哪里,他们准备南下援救十二兵团,但他们赶到河南永城陈官庄时,就陷进了另一支解放军的包围之中了。蚌埠的李延年等兵团也被解放军死死地阻击住了,无法北上一步。十二兵团别说突围,即使想攻占一个村庄,也是一件艰难的事情。
要命的是,粮食越来越少了,有些部队带的给养较少,已经全部用光了,只得宰杀战马。双堆集充满了越来越难闻的气味,除了死尸和硝烟味,又多了被煮熟的战马的骚骚的味道。没有盐,没有任何调料,就用雪水清煮马肉,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吃的肉了。第一次吃的时候,连队百分之九十多的人都呕吐了。前黄埔军校生作为一个地主的儿子,他的胃也消化不了这些食物,他回忆说,他吃完一块马肉后,蹲在战壕里,呕吐得鼻涕眼泪都一齐出来了,最后甚至还呕吐出来了黄色的胃液。但不吃这个又能吃什么呢?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什么都不吃,那只能饿死。本能战胜了恶心,几天以后,前黄埔军校生和他手下的士兵都习惯了大嚼大啃那些难闻的马肉,它们现在成了世界上最香的食物。
让黄埔军校生更加绝望的是,他引以自豪的军纪越来越坏了,凡是老百姓家能吃能用的东西,甚至屋顶上的茅草也被搬得精光了。为了寻找粮食,到处乱挖,把每家的房前屋后地皮都翻转过来,就连老鼠洞里残存的谷子也成了宝贝。本来就很少的树木也被剥光了皮,树干惨白地立在那里。让前黄埔军校生更难受的是,为了粮食,国军开始向老百姓开枪了。
前黄埔军校生回忆说,那天我正蹲在掩体里无聊地擦着枪,营里通知我们,准备把阵地移交给八十五军二十三师,我们连整顿好,全部拉到空投场,负责收集保护空投下来的给养,给养由兵团物资站统一下发。这是个好差事。
刚开始时秩序还可以,那些大饼和馒头装在麻袋和木箱子里,系着小降落伞落下来,虽然所有的士兵都抬着头眼巴巴地看着,但没有人上来哄抢。被围在双堆集里的老百姓也没吃的了,他们跟着降落伞跑,给养掉下来后,他们抱着就跑。士兵们大呼小叫地追着,但他们地形熟,像兔子一样窜到村里,一会儿就不见了。有些老太太背不动那些麻袋,就趴在上面,你去拉她时,她还死死抱着不放:“这是我的,这是我的!”我亲眼看到,一个老太太追着降落伞跑,结果被降落伞活活砸死了。
营长生气了,他把我叫过去,气呼呼地问我:“你怎么搞的,怎么能让他们来抢东西?”
我挠了挠头,说:“他们的粮食都被军队征用了,他们也没吃的。我能怎么办呢?”
营长很奇怪地看着我,他皱起了眉头:“你手中的枪是什么,是烧火棍吗?”
我愣了一下,呆呆地看着他:“长官,他们可是老百姓啊,我们总不能打老百姓吧。”
营长的眼睛里充满了杀气:“兵团来了命令,胆敢抢夺空投物资的,一律就地正法,不分老百姓和士兵,全部击毙!你执行去吧。”
我回头看了看那些村庄,村庄里住满了面黄肌瘦的乡亲。十一师从前不是这样的,即使在最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部队在常德作战,宁愿露宿山林也不去打扰老百姓,报纸上曾报道十一师“遵守爱民纪律,军民相处,融洽无间”。都是这可恶的战争,让人恶心的战争,把带枪的和没带枪的都推到了悬崖上,没有退路,只有看不到底的深渊,你明明知道,但你还得跳下去……
我们只得无可奈何地执行了这个命令,就连伍排长也没说什么,这些天里,他更加沉默,总是阴沉着脸看着同样阴沉沉的天空,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想可能他是在想念那些死去的二排的兄弟吧。八十五军的一些士兵被补充过来,二排已经满员了,但他们怎么能和那些朝夕相处的兄弟相比呢?
枪声响了,但我命令士兵向天空中开枪警告。那些老百姓惊惧地站在那里,犹豫不决地看着我们手中那些冒着青烟的卡宾枪,当他们看到那些枪口是对着天空时,他们又活过来了,继续追着那些空投物资奔跑着。我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挥了一下手臂,枪声大作,震得我的耳朵发麻。枪声停下来时,我睁开了眼睛,有七八个老百姓躺在了血泊中,甚至还有一个是十几岁的小孩,其他的老百姓退到了一边,他们看着我们,目光里充满了怨恨。我盯着他们,目光同样充满了怨恨:你们这是在逼我,我一个小小的连长,我能怎么办呢?我是一个军人,我必须执行兵团的命令!
是的,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件事。当时我还没意识到,这是我向人民犯下的一桩罪恶,我的双手也因此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当我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后,我更加清楚地知道了这一点,有段时间我常常做噩梦,总是梦见双堆集的那些乡亲向我伸着血淋淋的双手,仿佛向我控诉着什么。我心里一直压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现在把它写出来,心里轻松多了,如果人民因此要惩办我,无论如何处理,我都毫无怨言,这是我欠下的,我应该偿还。
枪杀老百姓以后,再也没人敢抢夺空投物资了。
但事情还是越来越糟糕,十多万大军人挨人堆在小小的双堆集,每天空投下来的物资根本就不够分配。天气不好的时候,飞机还来不了。士兵们开始挖草根来吃。大便里如果有没有消化掉的豆子什么的,也被人捡出来用雪水擦一下就吃了。我这时才明白兵团让十一师来管理空投场的用意了。十一师是兵团里最能打的一支部队,也是一支很有威信的部队,只有我们才能镇住那些被饥饿折磨得像无头苍蝇一样的士兵们。换了任何一支部队,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但这也没有能坚持几天,被饥饿驱使的士兵们受本能引导,丧失了理智,只要飞机一来,他们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一样,都爬出来了,站在那里,眼巴巴地看着那些空投下来的物资,然后慢慢地移动过来。我们面对他们,打开了枪刺,紧张地和他们对峙,阳光照着枪刺,发出冰凉的光芒,但他们仍旧缓慢而固执地一点点地逼近。我的额头上渗出了密密麻麻的汗水,我挥舞着手枪吆喝着让他们退回去,但没有人听,他们终于冲破了二连的警戒线,像一群狗一样扑过去,见到一个麻袋,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人都扑了上去,抢到一块大饼或馒头的,刚挤出来,又被别人抢去了。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有些士兵开枪了。被击中的士兵摇摇晃晃地倒下了,另一个士兵刚扑上去抓住了那块大饼,但他还没有送到嘴里,就又被别人打倒了。有时一块大饼跟前,会倒下三四个士兵。
团长十分生气,他命令我们在空投场上架起了机枪。刚开始那些士兵还真害怕了,瞪着血红的眼睛看着那些装满了大饼和馒头的麻袋,没人敢上来抢。但大饼比死亡更有诱惑,他们最后还是冒险冲了过来,推开正在抬着麻袋的士兵,发疯般地撕扯着麻袋。我愣愣地看着团长,团长脸色铁青,他恶狠狠地吼了一声:“开枪!”机枪立刻突突地叫了起来,那些士兵连哼一声都没来得及,纷纷地倒在了血泊中。我站在那里,脑袋一阵眩晕,痛苦地闭上了眼睛,这也是和我们站在同一个战壕里作战的士兵兄弟啊。
第二连下不了手了,伍排长就坚决没有执行向哄抢物资的兄弟部队士兵开枪的命令,三排长赵国忠也是这样,如果上司不在,他一般也不会向自己的兄弟开火。只有莫少尉的一排还在向抢夺物资的士兵开枪,但士兵们也拿着枪向他们还击,在一排一名士兵被打死以后,莫少尉也开始犹豫了。物资被抢得越来越多,兵团十分恼火,决定把宪兵连调上来。宪兵连很冷血,没有人会喜欢他们的,他们的武器精良,从来不参加战斗,但伙食却很好,个个养得身高体壮,专门用来对付我们这些在前沿流血拼命的军人。
第二连被重新拉上了前沿。
我们踏着冰冻的土地赶到了前沿,整个前沿已经变得陌生了,很少听到枪声了,出奇地安静,你要是仔细听听,甚至还能听到对面解放军士兵唱歌的声音。他们改变了战术,用坑道把我们层层地箍住,但却不急着进攻,就像猫玩老鼠一样,把你盘软了,然后再上来猛地咬你一口。他们在阵地上竖起了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