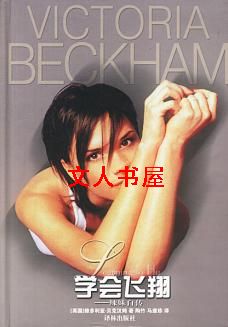学会飞翔-第3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件事一定不能泄露。戒指可以等等再说——重要的是我们对彼此的了解和感觉。我们试着交换戒指——但是我的蒂芬尼戒指甚至都无法套到大卫的小手指上。
因此我们只是把自己的戒指从右手移到了左手。我们就像孩子一样,我们太激动了。
8月30日,星期六。再过两天我就得走了,我感到非常烦恼。但是为了大卫我得高兴。上个赛季一开始——在我遇到他之前——在对阵温布尔登时他进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球,他从半场线处起脚,57码远——这是英超比赛中踢出的最远的进球。
我们曾经一起看过录像带,即使是我都能看出这个进球太漂亮了。不管怎么说这个球为他赢得了“年度马特·巴斯比爵士(1945—1968年间任曼联队主帅)年青球员奖”。我们都坐在那里,我的妈妈和爸爸、他的妈妈和爸爸,看他领奖。人群欢声雷动,大卫把奖杯高举到空中,转过身让每个人都能看见,我确实感到非常自豪。
我想大声喊出来,这就是那个我爱的男人,就是那个我要嫁的男人。我使劲地鼓掌,手都拍疼了,好像我想让他在体育馆67,000人的欢呼之外听到我的鼓掌声。
颁奖仪式过后接着是比赛:曼联对考文垂。在中场休息期间,我们像往常一样回到球员休息室,正喝着饮料,这时我爸爸的手机响了。他做了个手势让我过去。
“是露易丝,”他说,怪怪地看了我一眼。“她说媒体正在门口说你和大卫订婚了或结婚了还是其他什么事。那地方被包围了,她说,一束一束的花送过来,电话像发了疯一样。发生什么事了?”
我简直无法相信。他们是怎么发现的呢?因为没有人知道。没有人,除了我妈妈。我的意思是,你梦中的那个男人要你嫁给他——你不可能不告诉你妈妈。
每个人都要回到他们的座位上看下半场比赛了。
“求你了,爸爸,现在不行。我以后和你谈这事,”我说。
像往常一样,比赛结束的时候,大卫的爸爸向球场外正在售卖“粉红报”的人买了一份。这是一份比赛一结束就出版的体育报。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这么快就做出来了。不管怎么说,大卫的妈妈和爸爸上了他们自己的车,而我也只是回到沃斯利的房子后才看到大卫的那张照片。
它就在那儿,在头版:大卫举着奖杯,左手上套着一个戒指,标题是“贝克汉姆要结婚了”。我们都站在厨房里——桑德拉刚把水壶放上——他们(我妈妈、我爸爸、桑德拉、泰德)都看着我,或者不如说是朝下看着我左手上的蒂芬尼戒指。
接下来,我的手机响了。是为西蒙工作的一个律师,那时负责媒体方面的事务。
他绝对是个忠实的律师——我们经常称他为“死神”。
这正是我需要的。他的声音听起来比冰柜还冷。媒体登了照片,大卫把戒指戴在订婚手指上,还有我的一幅,戒指也戴在订婚手指上,他说。订婚的事情当然要否认。他将要发表的声明是大卫通常戴戒指的手指有轻度炎症,这就是他把戒指戴在另一只手上的原因。而我通常都把戒指戴在左手上。他会让媒体相信这没有任何意义。
“瞧,”我和他通完话以后,我妈妈说,“要想消除这条头版新闻的影响,得需要点有相当分量的东西。”
第二天清晨,在巴黎的一段隧道里,戴安娜王妃在一起车祸中丧生。我们直到第二天早晨离开大卫的家准备开往。伦敦时才知道。那么多摄影记者等候在外面——以前我们也遇到过这种奇怪的场景,但是都不像这一次。我已经照“死神”所说把戒指换回到我的右手上。但是他们并没有喊“把你的手给我们瞧瞧”,或者类似的话。他们说:“关于戴安娜你是否想说点什么?”
戴安娜?我记得当时想了一下。他们在说些什么?看到我一脸的茫然,另外有个人说:“你没听说吗?戴安娜王妃昨天夜里在一起车祸中丧生。”我看着大卫。
我们谁也没有说什么。突然我感到害怕起来。
我们上了车——这是我们一起买的第一个大件,一辆蓝色“保时捷”——我打了个电话给我妈妈。关于戴安娜他们说的话是真的。我们向伦敦开去,感觉好像完全失去了知觉。
前一天晚上——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我们到贝里一家很不错的而我们又熟悉的意大利餐馆吃了晚餐。回来以后,我们在沙发上坐了几个小时,只是哭。
为了过好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大卫做了很大的努力,他穿着我在纽约为他买的“普拉达”衬衫,看上去非常漂亮。
回到戈夫橡树,整个下午我都在收拾行李,而大卫踱来踱去,努力想鼓起勇气请求我爸爸把我嫁给他。他决心每件事都要做得很得体。他太紧张了。
“你不会吓着他的,大卫,”我向他指出了这一点。“我爸爸不会得心脏病或者什么的。”
他们在一起呆了大约十分钟,说着话。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我从来没问。
大卫上楼来以后,他的笑容和给我的吻就足以说明一切了。
那天晚上我们安排了一次告别晚餐。告别总是那么困难,但是戴安娜的死讯让它变得更为糟糕。每个人都知道威廉王子是爱玛的歌迷,我确信有一天我们会接到邀请到肯幸顿王宫去喝茶,然后我就能见到她了——不只是站成一排,握手或是什么的,而是一次真正的聊天。我是一个真正的崇拜者,忘了玛格丽特·撒切尔,戴安娜王妃向世界表明只要你一心一意你就能成就什么。她摆脱了一个不幸福的婚姻,开始过上她想要的生活。假如那不是女性力量,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称得上女性力量。
我们去了史密斯,翁戛的一家饭店,家庭聚会我们经常去那儿——离我妈妈、爸爸家只有大约二十分钟路。我们大家都到了,两家人,亚当斯一家和贝克汉姆一家:桑德拉和泰德,大卫的妹妹乔安妮和姐姐林娜,还有林娜的丈夫科林;杰基和托尼,露易丝和史蒂文,她那时的男友,克里斯琴,我和大卫。每个人都感觉非常沮丧和不舒服。环视桌边所有那些对我都很重要的人,我比以往更加强烈地感觉到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活着、和家人在一起。而我却就要离开我的家人长达一年,为什么呢?为了钱。
那天夜里,我收拾好了行李。卡米拉已经为我们买好了大箱子。我们只允许带这么多行李:一只箱子。我们每个人箱子的颜色不一样。我的箱子——恰好可以表达我的心情——蓝色的。这种箱子你也许会在海底发现,里面还装着财宝。大卫真的在上面画了一面“海盗旗”。一切都那么令人感动。
当这一切正在发生的时候,姑娘们打来了电话。我和大卫戒指戴在左手上的照片也许没有上头版,但却上了第三版。除了对戴安娜的死感到震惊外,她们都好像非常兴奋。
对她们来说出国的感觉和我是不一样的。梅兰妮·C没有男朋友,而且她离家生活好多年了。洁芮也一样,那时她也没有一个对她来讲很重要的男朋友。爱玛和我的心情是一样的——虽说她也没有撇下一个特别的男朋友。
梅兰妮·B倒是有一个男朋友,但是见面的机会本来就不多,因为他生活在冰岛。午夜的时候她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收拾好了。我说,还没有。你呢?她甚至还没有开始收拾。她不想去。
而且,不管怎么说,一年的行李你怎么收拾?
“不要想着一年,”我妈妈说。“你两个星期后就会回来,所以只准备两个星期的行李。”
我们访问的第一站是纽约,拍摄歌曲《难以忍受》的影像带,也为MTV的颁奖典礼做准备——《想要》摘取了最佳影像奖,这让我们大家都感到意外。为悼念戴安娜王妃我们都戴着黑色臂章。不幸的是,詹妮和凯琳没和我们一起来,自从《想要》开始,她们俩就一直为我们做头发、化妆,结果,我们看上去都像一群身着女装的大老爷儿们,尤其是洁芮。
我记得我们的座位紧靠莱尼·克拉维茨(美国著名男歌手)和他的女儿佐伊,佐伊打扮得活像一个跳摇摆舞的少女,虽然她当时大概6岁都不到。她穿着一条短小的皮裙子,白色T恤衫,皮茄克,还戴着一副和她爸爸一模一样的太阳镜。
正如我妈妈所说,两个星期以后我们又回到英国,但只呆了一个晚上。西蒙在法国南部租了一间大别墅,在那儿,我们将为10月初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一次大型音乐会进行排练。至少,尼斯离伦敦乘飞机大概只要一个小时左右。
结果是,这根本没什么两样。我们就好像远在西伯利亚。
那幢别墅在一个名叫比奥的村子外面,但我们却没去过比奥村或者到其他什么地方看过。在那儿的一个月中,我们只有一次出去到饭店吃饭。每个人都生活在那所房子里。
除了我们,还有厨师克雷西达,以及卡米拉。负责安全的有凡尔纳、JP,再加上艾伦·安德伍德,他这个“安全”的含义与其说是负责姑娘们不受伤害,还不如说是“军情5处”(英国负责国内安全和反间谍活动的政府机构)里“安全”的含义。西蒙不在时(这并不经常发生),艾伦·安德伍德就是他的耳目。他看起来就像一条哈巴狗——甚至走路都像,因为他是罗圈腿。他总是穿西服,经常穿一件长外套——即使天气比较热——事实上,他的脸总是不停地流汗。他拎着一个银色金属盒子到处走,我肯定那里面装着监视设备。
小的时候,我总是自寻烦恼,总是担心,因此我经常做这样一件事:闭上双眼,想像把任何烦恼都放在一艘船上,站在码头上向它挥手道别。那是一艘老式船,有船帆,它会带着我的焦虑驶向天边。对艾伦·安德伍德和他那个可怕的盒子我也试着这么做,希望他们能走远一点,但是,这一次不灵了。
我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