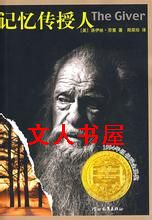战争与回忆-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虽然总的说来他更喜欢同女人鬼混。等他回来后,她大发脾气,闹得天翻地覆,他把她揍得直挺挺趴在地上;于是。她又羞又火,几乎发疯,喝了一瓶碘,痛得又打滚又呕吐,他在早晨三点钟开车送她进医院。这一件事情终于使他们断绝了关系。鲁尔继续过他的这种生活。象是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而从他的观点看,实在也不算一回事。
他象斯鲁特一样,在巴黎学俄语;这就是他们同住在一间房子的原因。他被派到苏联当记者以后,碰到“大剧院”剧团里的一个姑娘。那姑娘非常漂亮,于是他就和她结了婚——他是这么写信告诉帕米拉的——一仅仅为了占有那姑娘的身子,因为她非常一本正经,什么事都听不进去。他把共产主义的“婚礼宫殿”里的仪式描写成一场笑柄:瓦伦泰娜的父母、亲戚和“大剧院”里好朋友站在四周傻笑,一位神情严厉的胖女士,穿着一套裁剪考究的衣服,简短地给他们上了一段共产主义婚姻课,而新娘子呢,脸臊得通红,一只手紧紧地攥住她漂亮的英国心上人,还有一只手拿着一束蔫了的黄玫瑰。就这样,鲁尔有了一个俄国妻子。他一离开俄国,就把这件事丢在脑后了。
帕米拉避开他亲呢的凝视,哑着嗓子说:“你相信新加坡真是那样吗?”
“干嘛不相信呢?我们的垄断资本家通过几个和平主义的部,就在我们鼻子底下,在这儿英国老家建立了刮刮叫的强大空军和防御体系。不但德国佬,连我们自己的人民也感到惊奇哩!大英帝国是以新加坡为枢轴的,帕姆。要是我们要继续压迫和榨取五亿亚洲人,并且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愚昧的土著居民手中盗窃他们的财富,就一定要使新加坡坚不可摧。因此,这是毫无疑义的。”
“唉呀,不管怎么样,帝国已经完蛋了!”斯鲁特说。
“别说得太肯定,莱斯。温尼毕竟又建立起一个联盟,使它能苟延残喘。俄国人会为我们打败德国人的。你那些在打瞌睡的同胞迟早会参战并战胜日本人。整个垄断资本制度和它的殖民地都是腐朽的,注定要灭亡,只是还不到时候。 白人剥削者是顽强的世界主人。要消灭他们,就得发动一场全球性革命。 估计那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事了。”
“到底是什么让你认为俄国人会打败德国人的呢?”帕米拉插嘴说。“你没听见傍晚的新闻广播吗?”
又是那歪嘴一笑,那庞大的身躯在椅子里懒洋洋地挪动,那毛茸茸的双手大幅度地挥动一下。“亲爱的,你不了解苏联埃”
“我了解,”斯鲁特说。“我在莫斯科一直呆到上星期四。我还从来没看到过这样的精神崩溃哩。凡是能弄到车子或一匹马的人都溜走了。”
“他们不过是凡人呀。他们会恢复过来的。”鲁尔压低了嗓子,流畅低吟地说。“老弟,希特勒的主力部队从五十英里外朝你冲来,难道不叫人心慌吗?”
“我经历过两次了。这的确可怕。不过我自己是个该死的胆小鬼。我原来认为俄国人比较勇敢。”
帕米拉和鲁尔都笑了。帕米拉比较喜欢斯鲁特,因为他老实,虽然他再怎么看上去也没有一点吸引力。这个骨瘦如柴、脸色苍白的前罗兹奖学金获得者戴着无边眼镜,时常叼着烟斗,一副神经质的样子,总是让她想起象是个生理上发育不全的人。在莫斯科时,他曾向她大献殷勤,都被她厌烦地拒绝了。她始终不理解娜塔丽。杰斯特罗过去对他的那阵激情。
一阵冷颤使她很难受。“莱斯里,亨利上校在莫斯科呆了多久?”她不顾自己生病,赶到萨沃伊来,就是为了提出这个问题。
“让我们想想看。你和他是十六日走的,是吗?正是最人心惶惶的时候吧?”
“是的”
“他又呆了一个星期,设法弄到比古比雪夫更远的火车票。我原以为在那样慌乱的时候,这是办不到的事儿,可是最后他弄到了,于是他朝东去,穿过西伯利亚去夏威夷。”
“那么,他现在已经到那儿了?”
“应该是这样。”
“太好了。”
鲁尔用最最愉快的口吻对帕米拉说:“你们是情人吗?”
她的声调也同样愉快。“这跟你一点儿也不相干嘛。”
“莱斯里说,”鲁尔听到这冷冰冰的答复眨了眨眼睛,钉着这个话题谈下去,“杰斯特罗就是和这个人的儿子结婚的,是个潜艇军官,比她年轻得多。他还极秘密地透露,他自己内心里还在为娜塔而感到痛苦。她干嘛要做出这么荒唐的事来呢?那小伙子让她怀孕了吗?”
帕米拉耸耸肩。“你去问莱斯里。”
“他们与世隔绝,呆在锡耶纳郊外的别墅里,”斯鲁特阴郁地说。“我告诉过你。一个月又一个月地呆在一起,这是在他参加海军之前。当时他正为埃伦。杰斯特罗做研究工作。我想留在托斯卡纳的美国人当中只有他们两个年龄在六十岁以下。毫无疑问,事情就按照自然发展的规律发生了。我在华盛顿花了整整一个晚上和她就这个不相配的结合辩论。她很不理智,变得和顽石一般。”
“你的意思是她爱上了他,啪米拉说,”而不再爱你了。“
“事实上,我就是这个意思,”斯鲁特突然伤心地咧开嘴笑笑,回答道。这使帕米拉感到他的可爱。“她过去一向都理智得要命,现在却变得轻率了:嫁给这么个青年;和杰斯特罗呆在意大利;而且我最近听说,她还在那里,还带着个娃娃。”
鲁尔发出轻微的咯咯的笑声。“你们不应该把华盛顿那个夜晚都用在辩论上。”
“我要是想于其他什么事情,会给打得鼻青眼肿的。”
“得了,这也许对你有些安慰吧。亨利上校曾设法拆散过他们,可是没成功。帅B米拉说,”他们俩感情非常热烈呢。“
“这个人我倒很想见见呢,”鲁尔说,“亨利上校。”。“再容易也没有了。你自己安排一下,去采访在夏威夷的美国伽利福尼亚号‘舰长好啦,啪米拉厉声说。
“你喜欢他什么呢,帕姆?”
“他正派极了。”
“我明白了。新奇的魅力埃”
晚餐吃完了。他们的甜食——淡而无味、黏糊糊的粉红色胶冻状布了——留着没吃。钱已经付给侍者。斯鲁特巴不得鲁尔走掉。他有意要再在帕米拉身上试一试,不管她发不发烧;他已经有几个月没碰过女人了,而且他不象鲁尔,不玩妓女。鲁尔自称是个浪荡子;斯鲁特认为他简直是个畜生。他自己也曾经待娜塔丽不好,可是决不会使出把帕米拉逼得寻死觅活的那样粗暴手段。斯鲁特在莫斯科没勾引帕米拉,他相信那是因为有亨利上校在常现在亨利离得很远。帕姆又漂亮又可爱,而且又随和又开通,或者说,斯鲁特指望她是这样的。
“好吧!莱斯今天才从斯德哥尔摩来,帕姆,”鲁尔说。明摆着他怀有同样的意图。“也许我们不该让他熬夜。让我开车送你到你的公寓去吧。”
“说实在的,我听见有音乐呢。”帕姆说。“我真想跳舞。”
“最亲爱的,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啊?自从我认得你以来,你可是从来不跳舞的。”
“我的美国朋友们教会了我。可惜你不跳舞。怎么样,莱斯里?”
“乐于奉陪。”
鲁尔站了起来,在惨败中,咧嘴笑着。“那么,代我向韬基问好。我星期一去新加坡。没问题,那儿见吧。”
帕米拉注视着他离去的背影,红晕泛上了她的灰白色脸颊。
斯鲁特说:“你真的想跳舞吗?”
“什么?当然不想跳。我感到讨厌死了,我只是想打发那个爱搞同性恋的家伙滚蛋。”
“到我房间去喝一杯吧。”这邀请的用意显而易见,不过说得并不轻佻。
她脸上顿时流露出微笑——会意、觉得有趣、微微有点得意。即使在病中,她的脸也显得很可爱。她把一只汗津津的手放到他的脸颊上。“我的天哪!莱斯里,你还在对我打坏主意,是吗?你多么有意思埃对不起,我可是病得不行了,我在发高烧,不管怎么样,不行。”
斯鲁特说:“好吧,”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
“你真该在巴黎跟娜塔丽结婚的。她当时的要求可强烈呢!”
“唉!帕米拉,去你的吧。”
她大笑起来,抓起他的手放在自己潮湿、滚烫的额头上。“摸摸看。老实说,我最好找辆出租汽车送我回家,你说对不对?祝你在瑞士顺利。谢谢你带来了亨利上校的消息。”
一回到她自己的寓所,就写了那封热情洋溢的信。
在新加坡上空绕圈的飞船里,埃里斯特。塔茨伯利拉掉了自己的领带,敞开了紧贴大肚皮的白亚麻布外衣,用一顶草帽扇他汗湿的脸颊上的肥肉。“这儿比锡兰还糟啊,帕姆c我们正掉进一个该死的地狱呢。”
“安宁的小地狱,”帕米拉说,透过倾斜的窗户朝下看着。“庞大的壁垒、多得数不清的大炮、密密麻麻的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斗机都在哪儿呢?”
“自然,什么也看不见的。可是下面那个小小的绿蝎子可螫得死人呢。‘威尔士亲王号’就在那儿!舰上的那些炮塔一眼就看得出来。”
从空中看窄长的堤道使它和大陆相连,新加坡象是从峻峭的马来亚山脉切断下来一个尖端,波浪起伏的公海上一片绿色的三角形土地。两个灰色的“瘤子”破坏了它那丛林的美景:东南面是一座现代化城市,这里那里点缀着红屋顶,北面靠近堤道的是一大片小棚屋、起重机、营房、街道、房屋以及宽阔的绿色场地:新加坡海军基地。基地显得特别安静,在码头和广阔的抛锚地上看不见一只船。岛的另一边,战舰和商船都聚集在城市的海 滨。
“喂!”
在移民棚里,菲利普。鲁尔推开人群,穿过本栏杆走来。他穿着短军裤和衬衫,他的脸和双臂都晒成了红褐色,肿起来的、缠着绷带的手里拿


![[兄弟战争]喃喃爱语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0/49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