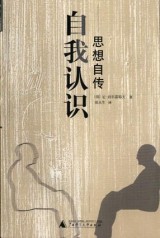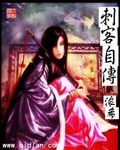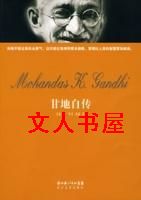巴金自传-第4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下一天我刚起床就得到从医院来的电话,值夜班的朋友说:“三哥完了。”
我赶到医院,揭开面纱,看死者的面容。他是那么黄瘦,两颊深陷,眼睛紧闭,嘴微微张开,好像有什么话,来不及说出来。我轻轻地唤一声“三哥”,我没有流一滴眼泪,却觉得有许多根针在刺我的心。我为什么不让他把心里话全讲出来呢?
下午两点他的遗体在上海殡仪馆中入殓。晚上我一个人睡在霞飞坊五十九号的三层楼上,仿佛他仍然睡在旁边,拉着我要说尽心里的话。他说谈两个星期就可以谈完,我却劝他好好休息不要讲话。是我封了他的嘴,让他把一切带进了永恒。我抱怨自己怎么想不到他像一支残烛,烛油流尽烛光灭,我没有安排一个机会同他讲话,而他确实等待着这样的机会。因此他没有留下一个字的遗嘱。只是对朋友太太讲过要把“金钥匙”送给我。我知道“金钥匙”是他在燕京大学毕业时因为成绩优良而颁发给他的。他一生清贫,用他有限的收入养过“老家”,帮助过别人,这刻着他的名字的小小的“金钥匙”是他唯一珍贵的纪念品,再没有比它更可贵的了。
它使我永远忘不了他那些年勤苦、清贫的生活,它使我今天还接触到那颗发热、发光的善良的心。
九天以后我们把他安葬在虹桥公墓,让他的遗体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里得到安息。他生前曾在智仁勇女子中学兼课,五个女生在他墓前种了两株柏树。
他翻译的《悬崖》和别的书出版了,我们用稿费为他两次修了墓,请钱君匋同志写了碑文。墓上用大理石刻了一本摊开的书,书中有字:“别了,永远别了。我的心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家。”它们是我从他的译文中选出来的。我相信,他这个只想别人、不想自己的四十三岁的穷教师在这里总可以得到永久的安息了。第二次修墓时,我们在墓前添置了一个石头花瓶,每年清明和他的忌日我们一家人都要带来鲜花插在瓶内。有时我们发现瓶中已经插满鲜花,别人在我们之前来扫过墓,一连几年都是这样。有一次有人远远地看见一位年纪不大的妇女的背影,也不曾看清楚。后来花瓶给人偷走了。我打算第三次为他修墓,仍然用他自己的稿费,我总想把他的“真正的家”装饰得更美好些。但是已经没有时间了。
不久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靠了边,成了斗争的对象。严寒的冬天在“牛棚”里我听人说虹桥公墓给砸毁了,石头搬光,尸骨遍地。我一身冷汗,只希望这是谣言,当时我连打听消息的时间和权利都没有。
后来我终于离开了“牛棚”。我要去给三哥扫墓,才发现连虹桥公墓也不存在了。那么我到哪里去找他的“真正的家”?我到哪里去找这个从未伤害过任何人的好教师的遗骨呢?得不到回答,我将不停地追问自己。
第八辑:达摩克利斯剑下的声音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
一、“到啦。到啦。”
接连的敲门声把我惊醒了。那个招待我们的波兰朋友阿来克斯在廊上大声叫着:“到啦。到啦。”我推开房门到廊上去,才看见火车停在一个冷清清的小站上。有两个铁路工人模样的中年人在月台上谈话。此外便是一片静寂。没有什么异常的景象。
“这就是奥斯威辛么?”我看见阿来克斯还站在走廊的另一头,便提高声音向他问道。
“奥斯威辛。”他短短地回答,一面在点头。他不会错。这个地方他太熟悉了。他在这里住了五年。他的父母都死在这里。他的左膀上还留着一个永远洗不掉的蓝色号码。
我忽然打了一个冷噤,好像有一股寒风迎面吹来似的。
“这个荒凉的欧洲小镇,就是德国纳粹屠杀过五百万人的地方吗?”我惊疑地问我自己。
没有人下车。也不见有什么动静。阿来克斯的声音传过来:“先去餐厅吃早饭。八点钟下车。”我看表,刚刚过七点钟。从华沙到这里,我们只坐了七个钟头的火车。
到八点钟,我们全下车了:除了中国代表团以外,还有罗马尼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阿根廷的代表们。苏联代表团中的尼古拉大主教也在这里,他的高帽,他的长须,他的黑袍,他的手杖在我们的眼里显得十分亲切,这几天来连他的声音我们也听惯了。
空气寒冷,我们的头上盖着一个阴沉的灰天,当地的居民到车站来欢迎我们,讲了话。好几部大汽车把我们送到集中营去。在路的两旁我们看见不少的红旗,旗上现着白色的大字:和平。每一面旗有一种文字,我看到了用八国文字写出的和平。
车子停在集中营的大门前。我远远地就看见了作为门方高高地横挂在门口的那一行德国字:“劳动使人自由”。怎么。
这个“自由”是什么意思?我要笑了。但是在这时候我觉得脸上的肌肉在搐动。我笑不出来。
我们下了车,脱了帽,在纪念碑前献了花。然后大家默默地走进集中营去了。我们都不想说话,好像在殡仪馆中哀悼死去的朋友一样。阿来克斯给我们带路。我们一共是三十八个中国人。别的国家的代表们已经跟我们分开了。
二、模范营
“我们现在走进奥斯威辛集中营了,”阿来克斯对我们解释道。“这一部分就是所谓模范营,是准备给人参观的。单从外表看,这里囚人的生活也许还要胜过希特勒德国的工人的生活呢。劳动使人自由,这是德国纳粹的一个大谎话。”阿来克斯的声音似乎是平静的,可是我觉得那里面含着强烈的憎恨。他是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一个打红领带的青年团团员,他给德国人关进这里的时候还只有十四岁的光景。五年的地狱生活应该给他留下不少的痛苦的记忆,这里的土地就搀和了他的父母的血和骨灰。他现在还能够用平静的声音说话,这个勇敢的孩子,他的心太坚强了。
的确,从外表上看,这里好像是机关职员的宿舍,或者中产阶级的舒适的住宅。在宽敞的路的两旁立着二十八所红砖砌的两层的楼房。每一所房屋都带着同样的和平的外貌。墙头挂着牌子,写明房间的号码。门开着,它们泄露了纳粹的屠户们尽力想掩饰的秘密。这些房屋现在已经成为纳粹暴行的博物馆了。
“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件东西也是他们没法隐藏的,这就是那双层的电网,网上通着高度的电流,谁触到它们,就会得着死亡,倘使劳动使人自由,那么这些电网装来做什么用呢?”阿来克斯继续说,这一次他的脸上现出愤怒的表情,他的眼睛射出憎恨的光。
我也看到了那些电网,柱子有四公尺高,两道网中间有一公尺的距离。电网的里外两边都有一道简单的铁丝栏杆,在这道铁栏的一些矮木柱上,钉了长方形的木牌,牌上绘着一个骷髅,骷髅下交叉着两根人骨,画旁边用德文和波兰文写着“站妆。这就是所谓”安全栏“了。沿着电网,像鬼影似地耸立着一些了望塔,据说阿来克斯住在这里的时候,塔里面不分日夜都有纳粹党卫军在看守,他们准备着随时开起机关枪射杀那些企图逃走的囚人。
其实囚人是没有逃走的机会的。一个党卫军的头目费立哥(Fritsch)上尉就对一批一批的新来的囚人说过这样的话:“我警告你们说,你们不是到一个疗养院来,你们是到一个德国的集中营来,你们除了从烟囱里出去外,就没有别的路走出这儿。谁要是不喜欢这个地方,他可以马上走到电网那儿。
倘使这里头有犹太人,他们没有权利活过两个星期;倘使这里头有教士,他们还可以活一个月;别的人可以活三个月。“
他没有骗人。从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五年一月这五年中间有五百万人到过这个地方。可是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二日苏联军队解放奥斯威辛的时候,集中营里就只剩了五六千个病重的囚人。德国的屠户们逃走时带去了五万八千个不幸者,其中有许多在中途就被枪杀了。的确有五百万人是在焚尸炉中烧成灰从烟囱里出去的。
三、博物馆
阿来克斯把我们引进一所房屋去。博物馆的负责人出来招待我们。年轻的说明员领我们去参观每一间陈列室。说明员讲波兰话,由阿来克斯给我们译成英语,我们中间也有人用中国话解说给一些同志听。
参观开始了,我们由一个陈列室走到另一个陈列室,由一所房屋走到另一所房屋。房间有大有小,陈列品有图片,有模型,有实物,有文字,有图表。每一所房屋有它的说明员。
说明员不只一个,参观的人也不只我们这一组,跟我们同火车来的各国代表全到了。在一个大的陈列室里面,人可以听到各国语言:俄语、西班牙语、法语、匈牙利语。不同的语言解说着一个同样的故事:五百万无辜的人怎样在这里死亡。
这不是故事,这不是空话。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对它表示怀疑,可是所有的人都带着惊疑和痛苦在问自己:怎么能让这种事继续进行了五年?怎么能够束手让那五百万无辜的人白白地死去?
我们的脚步变得沉重了。每个人的脸上都现出痛苦的表情。我不断地听见人在叹息、吐气。我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在刺着、绞着。我真愿意有一只大手来蒙住我的眼睛,可是我仍旧睁大它们,似乎要把眼前的一切刻印在我的脑子里面。
我们在注意地看什么呢?是人类的艺术的成就么?是近代科学的发明么?是大自然的美景么?是生命的奇迹么?我们是在参观?我们是在“学习”?
不,我们在看人类的受难。
这里是毒气房的模型,那里是焚尸炉的照片。堆在这里的两吨头发使人想到那三万二千个欧洲女人的青春时期的美梦;放在那个玻璃橱里的用女人头发织成的床毯在向人控诉纳粹的暴行。这个房间有成堆的梳子,那个房间有成堆的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