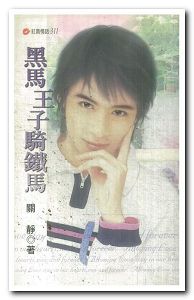金戈铁马-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这个以仁义道德教化的天下,现在杀了太仪还太早,那只会使人心反抗他仲骸,所以留着她。
暂时。
“朕不会到死都是你的棋子!”她不挣扎,反而用剩下的那只手不停的打他。
仲骸也不阻止,只是看着。
战场上,偶尔会遇到这种人,即使缺手缺脚剩一口气,也会勇往直前,或许最后会将生命燃烧殆尽,死无全尸,也有足够能咬下对方主将脑袋的气势,玉石俱焚的决心。
这样的人特别蠢,他却特别欣赏。
“你也可以选择当孤的女人。”仲骸游刃有余的将她拉进怀中,眼底漾着没有感情的笑意,提供另一个选择。
一手被他强劲的力道反剪在身后,倔强的她没有呼痛,另一手紧紧抵上他的胸膛,两人暗自凝聚相反的作用力,一个抗拒,一个强硬,相互勉强着彼此。
“这就是你和朕同寝殿的原因?你要天下,还想要朕?”熊熊火焰在黑眸中狂烧,一如她以往发怒时的眼神。
仲骸犹存余力,厚实的手掌隔着薄薄的睡袍贴上她的背,徐缓的摩擦着。
纵然端着一张脸,王室一族纤细灵动的外貌难以掩盖,太仪是个天姿绝色的倾城美人,而包裹这层美的是她傲视天下的王者霸气。
于是当她的威仪在他面前卸下时,最美。
“谁人不想稳固江山?”而她,是他稳固眼前的江山的基础。
“即使拥有朕,江山也不会是你的!”她的眼里盈满愤慨,全身辐射出紧绷的拒绝。
天下是她家的,天子是她!
仲骸优雅的挑起一边眉峰,看似温和的眸子隐含着足以冻结大地的冰冷。
“那么江山是谁的?你的?”他极为讽刺的反问。
太仪感觉自己被那深邃的黑眸吸进其中,那夜下不停的雨,狂奔的战火,马匹和宫女们的嘶吼哀鸣,每一张惊恐的脸,逐一浮现脑海。
仲骸,一个不属于原始七大家的异姓诸侯,是在这个充满了战争恶斗,下克上的时代洪流中崛起的一名猛将。
在他举兵入宫前,仲骸之名已然响彻天下,世人称他为枭雄,当时他的名气和实力已与她的祖先,天朝的初代帝王鸾皇所分封传承下来的异姓诸侯并驾齐驱。无法招抚日渐坐大的他,被九侍控制,逐渐养成软弱怕事性格的父皇只得听从官臣的建议,下诏分封他诸侯的地位。
那便是祸根的开始。
天朝气数将尽,是从父皇在位时,九侍把持朝政,混乱纲纪开始的。
当时,宫里日日笙歌作乐,臣不臣,朝不朝,只有深得父皇宠幸的九侍逾越了本分,在朝堂宫中呼风唤雨,提高赋税,欺压百姓,放任奸臣贼子大行其道,举国上下,苦不堪言。
国之根本一动,诸侯们遂拥兵自重,开始侵略并吞领地周围的大小城郭,巩固自己的势力,在仲骸被分封为异姓诸侯时,天下已然被瓜分成六块。
势力坐大,又互相制衡的诸侯们,于是虎视眈眈至尊之位。
仲骸的一把火,烧毁了三分之一的极阳宫,也烧醒了在皇宫中醉生梦死的上位者,她的父皇终于了解事态严重。
可父皇清醒不出三日,仲家兵入宫,血洗皇宫。
然后,天下迎接了她这个新主,仲骸迎接了手到擒来的江山。
“你何不直接杀了朕?”太仪问,语气是故意的酸讽刺人。
何故留下她这根肉中刺?
“名不正则言不顺,杀了你,苍生将不归顺于孤。”仲骸的回答明白,口吻却高深莫测。
“你连先帝都敢……”话说到一半,太仪同时感觉到两股痛楚,一是被他禁锢的手腕,一是被扯住的头发。
螓首高高后仰,撕裂般的疼痛让她几乎忍不住哀号。
“先帝是在睡梦中安享天年的。”仲骸没有怜香惜玉,拧断了纤细的手腕骨。
毫无温度的嗓音、冷冽的空气,使太仪泛起疙瘩。
她的视线在他与天井间震颤来回,疼痛已然麻痹了头皮。
“……谁会相信这番鬼话?”她咬着牙,即使痛得藏不住泪,也不要向他示弱。
好个刚柔并济的女人。
女人之于仲骸,一直是可有可无的。大部分的女人,即使有特别之处,他也没兴趣深究,太仪的特别,则是他所欲拥有的,于是他放了心思在她身上——很多心思。
俯下脑袋,仲骸用唇膜拜她紧绷的优美颈子,间或嗓音浑厚的说:“只要史班信,天下尽信。”
润黑的双眸倏地圆瞠,她再一次被迫认清事实,连史班都已在他麾下。
仲骸入宫不过半年,原本在她身边的亲信全被汰换掉,换上一批仲骸挑选的手下,宫女仆人不得擅自和她有过多非必要的交谈,左右史必须每日向他呈报,一整日她做了什么,和什么人说话,说了什么,全都被谨慎的记录下来。
她活在一个被严密监视的世界。
可笑的是,竟还称为帝王。
“天道何在?”她喃喃自语,身躯逐渐放松,眼眸黯淡无光。
仲骸微微一顿,接着一语不发的抱起她,走向大床,再把她放下。
她冷眼以对。
“天道从来不在。”
“那么……苍天已死。”她别开眼。
是不是该放弃了?如果连天都死了,她该向谁祈求?
“而你我还活着。”仲骸挑起她的下颚。
“这世间怎么总是不该活着的留下?”她的眉宇间全是尖锐的讽刺。
“因为世道如此。”他仍温文尔雅,一个眼神示意。
仆人们小心翼翼,恭敬的呈上一副历尽沧桑仍不坏的金甲。
刻有家徽的头盔不在了。
太仪永远记得,父皇是披着这身金甲尸首异地的。
如今这身金甲从父皇身上被扒了下来,上头的血迹已经擦拭干净,头盔则在父皇的首级上,而父皇的首级……
思及此,她惊恐的瞪着一名仆人举着一个托盘,托盘上的东西被红布盖着,隐约能看出头颅大小的形状。
尽管她的父皇在世人口中是个只知享乐,不理朝政,放任诸侯,以遭致灭亡的昏君,但终究是她的父亲啊!
至少他给过她为人父该有的爱,她怎么忍心看父皇的首级?
过于害怕,太仪忘了一个人死去后,尸体是不可能保存半年还完好如初的。
仲骸的眼角余光观察到她骇然的脸色,未经知会便掀起红布。
太仪差点不敢去看,直到红色的布巾翻腾了视线范围,翩然落下,朱鸾家徽印入眼帘时,一口气还梗在喉头,不上不下。
只有头盔,没有头。
她不知道是不是该松口气。
仲骸双手负背,站在头盔之前,状似审视它。
“这是你父皇的金甲,他穿着,却连刀都握不稳。”
“你配不上它。”太仪半坐起身,拾起红布,握在手中,隐隐发抖。
仲骸背对着她,“孤不喜欢死人的东西。这副金甲上,依附多少历代帝王的亡魂?瞧它的亮度、色泽,都风光不在。”
“即使如此,你仍不比它。”
“或者是它配不上孤。”仲骸回头,眸光犀锐。
太仪一窒,被他看得心头发颤,动弹不得。
他行至她面前,拿回红布,然后盖回头盔上,对一旁的仆人说:“换掉它,孤要打一副新的。”
“仲骸大人要用黄金打造吗?”仆人问。
“黑铁,黑得看不见一切的黑铁。”他说,正对着她。
她以为自己够坚强,能抵抗这个男人,但是他所言所行,都在彰显他们实力的差距。
半年来,她头一次的反抗,认清了一件事——
这场诸侯与天子的角力,她依然处在劣势。
从仲骸入宫的第一天起,他们一直是同寝殿。
以黑檀木为建材打造的寝殿,是她诞生时,父皇为她大兴土木建造的,沉稳内敛的色调,陪伴了她到目前为止的生命,这里总能安她的心。
躲在这里,犹如最坚固的避风港。
如今,却教他入侵了。
同房不同床,偌大的寝殿从那天起被分成两半,一半归她,一半归他,原本安全的堡垒成了同时囚禁她与野兽的牢笼,皇宫内再也找不到能松懈的地方。
第1章(2)
她不记得自己有多久没喘口气了。
黑得看不见一切的黑铁……
他怎么不干脆说黑得看不见未来?她清楚那才是仲骸说那句话的真正意义。
她的未来好像这片熄了灯的黑暗,寂静无声,没有前进的方向。
身后的床垫有下沉的感觉,太仪一凛,胃紧缩,紧张的酸液在里头灼烧。
同房不同床……也要在今晚打破了吗?
仲骸矫健的臂膀绕过窄小的肩头,转眼,她身陷一片温暖。
一个踏在尸骸上还会笑的男人,怎么还会有体温?
太仪起了疑窦。
“不睡?”她一点点细微的动静,全逃不过他的眼睛。
“睡不着,已是习惯。”她原本也没有装睡的意思,只是不想主动开口和他说话。
“为见不到风曦饮泣?”
“朕的眼泪如果能唤回十五日,掉几滴也无妨。”
“你如何确定眼泪对孤无用武之地?”
“有用吗?”她脱口而出的话听不出喜怒。
“何不试试?”他的话也听不出真意。
“当那些死在你刀下的人哭着求你放他们一条生路的时候,有用吗?”她的话句句带刺。
不是不试,是试了也没用。
“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哭相不好看。”仲骸揶揄。
“朕的哭相更丑。”太仪的语气充满嫌恶。
如果他懂得“守信”这两个字的意思,她或许会考虑哀兵政策。
仲骸冷漠的眼觑着太仪的后脑勺。
看来这口气她和他呕定了。
对于如何处置太仪,他始终没有确切的方向,唯一确定的是等待时机成熟后,便能杀了她,君临天下。
可偶尔他会想,杀了她太可惜,这个女人拥有太多他欣赏的特质,尽管她是恨意十足说出来的话语,在他听来都觉得有趣。
如果她是个男人又非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