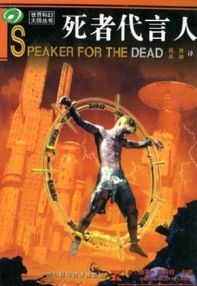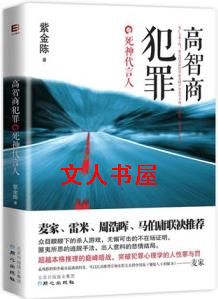姑妄言-第6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约起更时候,只得外边轻轻敲门,知是他来了。邬合拿着棒槌躲在厨房里去,那妇人出去开门,放那小子进来。忙把门插上,走进房来。那色鬼把妇人抱在床上,不暇言就替他褪裤子。妇人总不推辞,他自己脱得精光。也没工夫上床,就站在床前,扛起妇人的两条腿来,将屁股拉出床沿外,灯光下照得甚明,站着一攮到根。一个其大无外,一个其小无内,那小子如渴龙见水,命也不顾,下死力一阵乱抽,不多几下就完了事了。正在麻欢的时候,被妇人伸手将他的脖子搂过来,把舌头递在他的口内。这小子快活得了不得,咂了几下。那妇人也叫他伸过来,那小子忙把舌头伸出,恨不得连舌根都吐出来送入他口中。被妇人紧紧含住,猛的下力一口,格蹬一声,齐齐咬下。那小子疼得喊叫不出,一跤跌在地下。妇人忙把断舌头吐出,叫道:“有贼了,快些来。”只听得房门外喝道:“贼在那里?拿住了,不要放他走了。”那小子正疼得发昏,耳中忽听得这话,晓得是被他暗算。也顾不得衣服,爬起来,精光着就往外跑。那邬合嘴里吆喝,却不进来。他有心算计无心,在房门外等着。说时迟那时快,他才一只脚跨出房门槛,屋内有灯,外面黑,看不真切,被邬合下死力对准踝子骨一下打得哼的一声,一交跌倒。邬合上前按住,坐在脊背上。那妇人也将穿上裤子,拿出灯来。取过绳子来,同邬合将他紧紧的背绑起来。那小子舌头没了,疼得一声也无。腿又打伤,又跌得昏头晕脑,动也不能一动。况这小官只会屁眼中捱那挺硬的膫子,棒槌打踝子骨上,从不曾尝过这横量的木棒槌。他挣挫不得,任他夫妻二人舞弄。邬合把他绑得定定的,然后起来把他的头发打开,妇人已将日间预备的宝货都搬了出来,邬合用沥青将头发替他刷得直竖竖的,然后将油调的红黑蓝三样颜色,从头至脚,二人用笔一一阵混涂乱抹抹,彩画了个花花绿绿,将银锞纸钱替他浑身挂下。
妇人向小子道:“你奸了我几年,我那些儿亏了你?你还四处花败我。你今日又想来奸我,我且出出气着。”拾起棒槌来,拿那一头细些的把儿,对准他的粪门,尽力往里一插,竟进去了四五寸,疼得那小子把屁股只是扭。又拿着一根细绳,将棒槌扎紧,系在他腰间。一头在粪门内,一头托在外边。又找出几根旧头绳来,拿了些烂纸拴在棒槌上,像个大尾巴。才提将起来,开门放他。那小子得了命,一瘸一跛的才要走。他夫妻二人各拿了一把锥子,照屁股肉厚处戳了两下,那小子疼得又叫不出来,屁眼内又是棒槌塞着难走。戳得没奈何,只得瘸着腿一拐一拐的没命往外跑。邬合还恐他躲在僻静处,故意的大吆小喝,后面撵着。那小子怕锥子利害,直往前奔。邬合一直送他出了大街,见去远了,方才回家关门。夫妻笑了一场,上床而卧。他这条死巷内竟无一人得知。
再说那龙颺跑到街上,已有二更天气。人都尽了,静悄悄的。虽有微月,昏头昏脑,连路都认不清白。拐呀拐的乱跑,远远看见一簇人拿着灯笼,知是巡夜的官来了,转身往回里就跑。那官同众人已经看见,说道:“那是个什么东西,快快的赶上。”众人一轰赶来,那小子被赶急了,腿瘸着也跑不动,倒站住了脚,有个要人救他的意思,却说不出话了。众人离他不远,见他不动,反吃了惊。仔细定睛一看,从不曾见过这么个怪物。众人心里都是有些发毛,胆小的退在人背后躲着看。有几个胆子大的,高声喝问,又不见他答应。那小子分明是说甚么,因舌头全没,说不明白,只听嘴里呜噜呜噜的叫。那官儿仗着胆子,说道:“要是人必定会说话,他只会叫,不是鬼定是妖怪。我们人多,阳气盛,逼住了他脱不得形。你们快动手打,不要被他走了。”那小子也听见了,着了急,越发奔了人来,要人看看的意思,嘴里更叫得凶。众人见他扑了来,心中大慌。想是本官说的有理,到底是读书的人不同。又恐他先下手伤了人,仗着胆,一齐上前。一顿乱棍,打得脑浆直流,浑身骨折,方敢近前。将灯笼照着细看,方知不是鬼怪,倒是个人怪。吃了一惊,道:“这官儿因太通格物,格错了。”默无一言。次日报了察院,差人验看,唇外血污,口中无舌。肛门内有棒槌一根,备图了一个形状呈上官府。就知是这人定是因奸被人暗算,究无谋主,又无尸亲,吩付地方掩埋。这小子奸了人家闺女,这原是女子先去就他,还情有可恕,世上有几个鲁男子柳下惠?但只后来扬他的丑,无情负义。他已有了丈夫,今日又想来奸他。其情原自可恶,一死也不为屈。但这邬合夫妻也算下得毒手。这个小子的父母见儿子数日不归,四处寻觅了几日,杳无踪影。只疑他跟了好龙阳的大花子去了,再也想不到他这一首。这小子也只算个无主的孤魂罢了。
再说那邬合次日到街上,纷纷听得人说昨夜有一桩奇事。一个人不知作了甚么坏事,被谁人弄得如此如此形状,下此毒手,送了一条性命。听了,回家告诉嬴氏:“除了你病根了。”夫妻笑了一场。有一首词儿说这狱卒凶淫并龙颺的愚呆,道:恶毒从无过禁卒,逞凶那惧遭刑朴。叹嬴氏虽淫,坑他机阱,几乎就木。 堪笑龙颺愚满腹,想当年风流再续。似投火飞蛾,犹欣欣的,反被情仇戳。 《雨中花》此后这嬴氏同邬合过得好不和美,邬合也疼爱他至极。一日,邬合因有事到城外,忽然听得一个坟圈内有小孩子啼哭,忙走去大一看,却是个一岁来的男孩子,一脸的痘疮。原来这孩子出的是火症痘儿死了,他父母怕狗吃他,撂在人家坟圈内。这一夜得了露气,又沾了土气,复又活了,故此啼哭。邬合满心欢喜,抱了回来,叫嬴氏好生养着。过了几日,痘儿好了,好个白净的孩子。他夫妻二人知道自己不能生育的了,待这孩儿比亲生的儿还疼。虽才一岁,也会吃了,买那各样的糕点喂他。渐渐长大,起了个名字,叫作邬继祖。这孩子只知他夫妻二人是他的爹娘,并不知别有父母。连邬合还不知他是甚么家的,何况于那小孩子?后来抚养成人,承继了他的宗祀。这发人幼虽淫荡,到后来改过自新,竟做了一个贤妻慈母,寿考善终。那邬合真是:干妻反胜实妻,无子公然有子。
也受用了下半世。此系后话,不题。再说邬合那一日领了宦萼之命邀贾、童相会,回家歇宿。这话还在嬴氏被和尚拐去未曾拿获之时。因一枝笔写不得两处的事,此时方又续出。他次日大清晨起身要往他两家去,刚出门,遇见县里差来的捕快替他拿人。他送了个封儿,又同众邻居问了王酒鬼。众役去后,他方得脱身前去。正然走着,到了一个人家的大门口,看那个门长,若非仕宦门楣,定是富翁的华宅。只见有十来多岁的一个标致后生,身穿得十分华丽,打着一个小厮,也只有十来岁,打得哭喊连天,满地下乱滚,足足打了有百数,怒犹未息,气狠狠骂着,走了进去。邬合叹道:“一个下人就有过犯,将就打几下罢了。何苦打到这个地位?做主人的恩宽些也好。”傍边一个老儿笑道:“兄当是主子打奴才么?这是奴才打主子。真是天翻地覆,有冤没处诉的帐。”邬合惊问道:“请教老爹,这话是怎么说?我不明白。”那老儿笑道:“墙有风,壁有耳。这话对兄说不得,兄也不必问。”他说着,就走了开去。邬合听了,心中胡胡涂涂,猜测不出,也就去了。
你道这老儿说的是甚么缘故?原来这个体面的后生,姓牛名耕,字希冉。他父亲叫做牛质。这牛质是个堂兄,现做显官,名为牛解。这牛质家中有数万之富,他自幼酷好的是一个色字,除妻子苟氏之外,妾婢约有数十。他的房子最大而且富丽,卧房之后还有一处小园,内中有亭有塘,有楼有阁,曲曲折折,甚是幽致。各处俱铺设床榻,随处兴到,便同妻婢们高兴一番。他这园中果然收拾得好,但见那:潇洒旁轩,高明户牍。画贴春宫满壁,书堆淫艳连床。庭前院内,碧桃相间海棠红;廊下阶前,芍药并参玫瑰紫。夏月荷花映日,秋来桂蕊飘香。绕屋梅花三十树,垣墙翠竹几千竿。栏杆■字斜连,窗槅衢花掩映。楼阁俱铺床榻,庭轩尽设枕衾。淫情一动,不拘何处便行;骚兴旦浓,那管妾鬟混干。
园后还有个小便门通着外边,时常叫家人们打扫出那些污秽之物,就不从内室中走。这牛质虽有许多妻妾,总无儿女。他这个好淫,不但这些妾婢是他分中应乐之物,至于家中仆妇,不论精粗美恶,他总放不过一个,都要赏鉴赏鉴他们的光毛肥瘦。又好南风,龙阳戏子也养着许多,真是一个色精。然而以实论之,是登徒子的传流,只算得好淫,却算不得好色。他这妻子苟氏,生得风骚俊美,是个绵里针笑里刀的妇人。任凭丈夫娶妾纳婢,他谈笑自如,毫无愠色。心中虽然醋气薰蒸,面上从不露一丝形迹。他内中又别有一番心事,待这些妾婢们不但和和气气,而且都施些小惠。牛质夸他贤德,畏敬他是不消说了,这些婢妾也没一个不感他的恩私。牛质心爱的一个戏旦,叫个胡可,是苏州人,生得娇媚如妇人一般,有十七八岁。他不在戏班中算的,只自己家宴,偶然叫他唱几句,养在内书房中,竟作个妇人妆束,金簪珠坠,俨然一个女子。苟氏时常见他唱戏,恨不得搂到怀中,一口水吞他下肚。虽然爱到十分,碍着人多眼众,无可奈何,只好眼饱肚饥而已。苟氏有一个丫头叫做红梅,有二十岁了。生得红白麻子着实俏浪,那牛质自然是饶不过他的。但这丫长年长而骚,主人公的内宠多,雨露之恩不能常波及到他。时常牛质叫他往书房中取东西,他也看上了胡旦,反拿话儿勾他。他一个做戏子的人,这风月调情是他的拿手。况恃着主人公